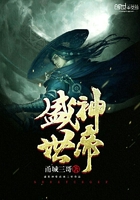“真的不用?”慕容钰清澈的瞬子此时蒙上了一层暗光,平静的瞳内似乎显现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将夏清歌的视线紧紧的吸了进去。
见到夏清歌小脸上那抹红晕,慕容钰心情极好的低垂下头,再次吻上了那近在咫尺,柔软到骨髓里的红唇。
“主子,修国公府到了。”马车内的气温逐渐加温,慕容钰双手搂着夏清歌的纤腰,正想加深此时的吻,却不想,车帘外一道极其不合时宜的声音打破了此时的画面。
夏清歌醒过神来,一把推开了他,随即抬起衣袖擦了擦嘴,在不看慕容钰一眼,脸颊烧红的揭开帘子跳下了马车。
“清歌小姐。”景天朝着夏清歌行礼,而对方却低垂着头,未曾看他一眼,急匆匆的朝着修国公府而去。
站在原地的景天朝着那远去的背影看去,清冷英气的面容上闪过一抹纳闷,随即转身朝着紧闭的车帘看去:“主子,可是要回府。”
坐在车窗前,一直目送那抹身影离开后,慕容钰方才含笑收回了视线。
不答反问:“景天,我记得曾经让你在一月之内找到喜欢的女子成家立业,如今可是有消息了?”
“主子?”景天的脸上立刻闪过一抹菜色,心里暗自纳闷,今日他难道又惹怒了主子?看来明日还要私下里去问一问景铭的看法,那小子是个滑头,定然能明白主子的深意。
“回府吧。”慕容钰安坐在软塌之上,不自觉的抬手抚摸上自己的唇,嘴角的笑意越发的深了。
“是!”景天眼见自家主子不再催促他娶妻这件事情,着实松了一口气,赶着马车转弯消失在了茫茫夜色当中!
德圣殿内
一身明黄色锦衣龙袍的秦武帝坐在案几前,桌面上摆放着一位年轻男子的画像,那名男子身穿一身锦衣华服,气质淡然清贵,嘴角含着一抹极其清浅淡然的笑意,瞬子更是温柔似水,男子的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画卷却已经有些泛黄陈旧,看来定然是经历过一些年月。
“皇上!”夏子恒缓步走入大殿内,朝着秦武帝躬身行礼。
“你来了,坐吧!”秦武帝从沉思中醒过神来,未曾抬头,沉声开口,声音有些干涩却不失浑厚之气。
“谢皇上!”夏子恒走至旁边的椅子端坐下来,这时秦武帝方才抬瞬淡淡扫了夏子恒一眼:“你知道今日朕宣召你来有何事吗?”
夏子恒低垂着头恭敬回道:“赎臣愚钝,不敢猜测圣意。”
秦武帝轻笑一声,嘴角却带着一抹清寒之气:“前几日红袖私下派遣杀手在凌霄山一代拦截夏清歌,想着以绝后患,丝毫未曾将朕的叮嘱放在心上,朕倒是想要当面问一问你,你那群属下究竟能不能配上用场!”
“微臣知罪,还请皇上息怒。”夏子恒身子猛地轻颤了一下,听出了秦武帝带着怒意的口气,他再不敢坐在位置上,即刻起身跪在了地上。
“回禀皇上,夏清歌如今在追查西郊庄子上的账目,臣只是怕她查出什么,所以才起了杀念,是臣的疏忽请皇上责罚!”
秦武帝盯着夏子恒看了片刻,眼神越发的暗沉下来:“如今夏清歌没有出事,你和红袖的罪朕先姑且饶恕,若下次在这般为所欲为,朕绝对不会在姑息养奸。”
“是,臣谨记皇上教诲。”
“好了,起来吧。”
“谢皇上。”夏子恒颤颤巍巍的站立起来,低垂着头并未坐下,秦武帝低头朝着桌面上的画像看了一眼:“你可还记得这个人?”
“回禀皇上,微臣记得。”他寻着秦武帝书桌上看了一眼,随即低下头低声回答。
这个人在二十年前可谓是轰动一时,可是结局也甚至悲惨。
“是啊,二十年过去了,朕几乎都快记不清他的面容了。”秦武帝有些感叹的缓声说道。
夏子恒眉宇微微一闪,似乎不太明白秦武帝此时的感叹。
“既然是故人,皇上就莫要如此感伤了。”
秦武帝脸上的冷意越发的深了起来:“对啊,他的确是已逝多年的故人,可如今朕却从另外一个人的脸上看到了他的影子。”
“皇上?”夏子恒也十分震惊,抬头带着询问的眼神看向秦武帝。
“很意外?”秦武帝冷笑一声:“这个人可是你们夏府的人,这么关键的事情,你怎么就未曾注意?”
“皇上所指的究竟是何人?老臣府上可从未见过长相和那位一样的人啊?”夏子恒彻底被秦武帝说懵了,脑海里仔细回忆,最后一张不算熟悉的面孔进入了他的脑海,可想起她的音容相貌,夏子恒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极其暗沉。
夏清歌自从落水醒来后性情大变,连相貌都彻底改变了不少,加上今日的宫宴,他只见过她两次,若不是秦武帝提醒,他断然不会将夏清歌的容貌和那个人联想到一起。
“皇上说的可是夏清歌?”
“你也觉察出了对不对?你和夏子清是亲兄弟,当年的事情你也有参与在内,自然清楚,自从杨紫鸢嫁入夏府之后,朕曾多次派你去查探,你报给朕的消息均是夏清歌是夏子清之女无疑,可如今夏清歌这张脸却像极了那个人,你要如何解释?”
看出了秦武帝审视怀疑的眼神,夏子恒心里猛地一冷,心里猜测,皇上定然是怀疑他当年禀报的事情不实起了猜忌之心。
“皇上,那人是二十年前就坠崖而死的,可杨紫鸢却是在十五年前嫁进了修国公府,这中间相差整整五年时间,按道理说,那人和夏清歌绝对不会有任何关系的,而且当年臣的大哥和杨紫鸢情比金坚,世人皆是看在眼里,夏清歌定然是他的亲生女儿无疑啊!”
听了夏子恒一番解释,秦武帝泛起的疑心丝毫未曾减退:“坠崖身亡?当年他的确是当着朕的面跳下万丈悬崖,可朕派遣了五千锦衣卫前去搜查他的尸体,可最终无果,朕要如何相信他是真的死了?”这件事情在他的心里深埋了二十多年,已经成了他每晚的魔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