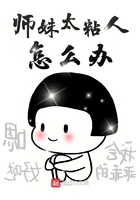从系安全带的那刻起,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行者,我的每个动作都牵动着队友们的神经。地面上的队友躁动了,他们担心高处的我停留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完成动作,于是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号子声在空旷的训练场上回荡。
我轻松地爬上十余米高的铁管,双脚却怎么都站不到平台上。那平台也就比我的脚掌长上五公分的样子,圆形的。下面的队友开始提醒我先上自己认为有力的一只脚,于是我吃力地把灌了铅一样沉重的左脚“搬”上平台。之所以在这里我用了个“搬”字,完全是因为那脚好像不是我的,而是大象或其他身体庞大的动物的。我清楚我的右脚还滞留在下面,可我很怕,怕右脚上不来,身体失去平衡,一头朝左边栽下去,尽管我系着安全带。
现在想来,我的担忧简直就是多余,可很多时候人都这样,就如很多人担心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事实上这一天和以往任何一天没多大区别。我半蹲在那里,尽可能放松身躯,以使自己得到片刻的体力调整。时间在一秒一秒地飞逝,我犹如一只蹲在栏杆上的石猴——没有一丝要站起来活动四肢的迹象。
不是我不想站立过来,我确实想不出半点法子使我的右脚能够“抬”到平台上,直到队友中爆发出有节奏的掌声,我的右脚才肯扬起头,跟着我的小腿向上、再向上,然后探出一点小脸,羞怯地向我的左脚打了声招呼。终于,右脚它战胜了羞怯和不安,向左脚靠拢了,地面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了队友的理解和支持,我的胆量迅速膨胀,我想站直双腿,岂料,铁管再次鬼使神差地摇晃起来,就像小时候我爬到高高的枣树上摘枣吃,大一点的孩子使劲摇晃树身搞恶作剧一样,不同的是那时我可以用力抓牢足以承受我体重的树枝,可眼前没有我所希冀的任何东西。
队友中有人提醒我调整呼吸。这在平常是我很怀疑的一个动作,到了关键时刻,我不得不说它实在神奇,神奇就神奇在经过我三次深呼吸调整后,脚下已风平浪静。我站在铁管上,伸出双手目测一米外的抓手,正准备身体跃起,去完成“尖峰时刻”时,铁管又一次触电般地抖动不止,我不得不继续停下来调整呼吸,看得出队员们内心比我还着急,他们担心我逗留时间过长,过度消耗体力。
从系安全带的那刻起,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行者,我的每个动作都牵动着队友们的神经。地面上的队友躁动了,他们担心高处的我停留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完成动作,于是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号子声在空旷的训练场上回荡。
“1、2、3”,“1、2、3”,“1、2、3”,一次,二次,三次,我呆立在那里,似乎无动于衷。其实不是我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身心,怕草率地一跃之后,再次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挑战。当四周一片寂静时,我突然伸出手臂,屈膝,像站在荷叶上的青蛙一样,轻轻一跃,便跳到了河岸上。我完成了“尖峰时刻”,之后我这个“神兵”从天而降。
掌声如潮水般响起,我胜利了。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失败和胜利取决于一跃之间。但这一跃,看似简单,实则是对心理极限的挑战。
曾在第一次挑战时我与成功失之交臂,主要是我给了自己失败的理由:我个子低。果然,在我做“尖峰时刻”时,“暗示”站出来替我说话了:“你失败没人笑话,且不说你身高不占优势,就是年龄你也属于偏大的了。”所以,我没有触摸到“抓手”,直接速降到地面,还感觉那是理所应当的。我想,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失败后,给自己寻找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直至我看到比自己低半头的一队友挑战成功时,才意识到自己的胆怯。于是,决定二次挑战。
没想到第二次挑战的压力比第一次要大得多。面对一声高过一声的助威,面对一双双期盼的眼神,我多希望自己像竞技运动员一样,一个漂亮的鱼跃,便宣告成功。然而我反复试验,却距离成功越来越远。“怎么别人行,我却不行?莫非我真比别人差?”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叩问自己,答案模棱两可。在我第一次挑战失败后,我眼见高大威猛的刑警队长,没有爬到铁管一半,就沮丧地打道回府,他说还不如让他去抓坏蛋简单,说着不好意思地抹去两行眼泪。那是我第一次见一个七尺男儿当众流泪。可我不同,我不恐高,别说这十来米的铁管,就是再高又有何惧?在我幼年时,爬高上低,无所畏惧,真可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与那些把根扎在地下的参天大树不同的是,光溜溜的铁管子像醉汉一样晃来晃去,这正是人把这种恐惧的力量传播到双脚的缘故,平地上你内心的恐惧无所察觉,到了半空,这种恐惧会借助铁管子放大,再放大。所幸,我最终说服自己战胜了恐惧。
这是我2010年夏天参加全省公安民警心理健康辅导员拓展训练的一个花絮。对我来说,完成“尖峰时刻”,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跳跃,它打破了我已往固定的思维模式,真正领会了“体验激发情绪,行为改变认知”的内涵。生活和工作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只要调整好自己的身心,完成纵身一跃,眼前便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快乐可遇而不可求,我们最明亮的欢乐之火往往是由意想不到的火所点燃的。
——约克兰逊
一人一物总关情
——由韩冬红散文说开去
郭连莹
散文是一种大众化文学艺术。散文写作没有门槛,然而,写好散文除了一个人的天分之外,还需要用心、用情、用汗水,需要贴近大地、贴近生活、贴近生命。
在一些作品的生活质感和生命体验明显弱化的今天,韩冬红用贴近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本真,努力用真情、激情乃至体温,构建切近生活原生态的反映市井百姓生活百态的散文艺术空间。在宏大叙事盛行的写作语境中,她注重打捞记忆深处的家族亲情以及与自己相关联的社会生活内容,敢于直面现实,坦露人性的弱点,以真诚复真实的姿态,敞开自己的生命历程与心灵世界,从而实现与读者的沟通,与时代的对话。从家乡、父母及亲朋、路人身上,她找到了散文的“故乡”——这是一种写作的原动力。
读韩冬红的散文,给人强烈的感应是蕴含于一人一物之中的真情。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至仁至爱,为艺术忘我而行者,皆真情真人也。
韩冬红不是专业作家,每天睁开眼就有忙不完的工作在等着。尽管这样,她的散文佳作不断、奖项不断。我曾多次忖度:春花秋月中,她在悄悄自我加压的吧?霓虹闪烁里,她是在把别人消遣娱乐的时间用来写作的吧!我感觉到,在文字的世界,她写作着,快乐着,如啜琼浆,甘之如饴。
韩冬红真正开始写散文不过十年时间,她开始动笔写作时,我刚好来到邯郸。其实,在不认识她的时候我已经认识她的文字了,从她的博客里,从一些报刊上。我听到了她铿锵前行的足音,我看到了她迅速成长的影子,我嗅到了她双手捧着的硕果的芳香。歌德说:“文学是经由语句组织起来,而成为一种扣动人类心弦的、和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而经由她用语句组织起来的散文,真的是扣人心弦。不止一次,我被她的散文感动得不能自已,在电脑前、在沙发上、在台灯下……不同的地点,一样的动容。我曾多次将眼睛从她的文章中移开,站起身踱来踱去,不忍卒读,任凭泪流。对我来说,这样的感动很少。
虽然和韩冬红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虽然经常看到她的文字,虽然和她的物理距离并不远(我家和她工作的单位仅仅一路之隔),但是,我们见面并不多,屈指可数。而今,当我再一次踏进她的文字丛林,才得以进一步认识其人和其文。
一、关于“宏大叙事”与“亲情记忆”
著名作家曹文轩曾几次重复自己下过的一个结论:“一个艺术家的本领不在于他对生活的强信号的接收,而在于他能接收到生活的微弱信号。”由此,我想到身边一些作家的薄弱之处,就正在于他们感觉的粗糙,而缺乏细微的感觉。他们热衷于宏大叙事,即:忙于对大事件、大波动、大人物、大场面、大文化的描述,而注意不到那些似乎平常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状态,注意不到那些似乎没有声响、没有运动的事物和人情,甚至对身边的亲情都会熟视无睹,不屑一顾。而事实上,往往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藏着大主题、大精神和深刻的人性以及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韩冬红写亲情、友情、世情的意识很执着。纵观她十年来的散文,选择的不是什么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没有厚重的历史感;选择的不是什么文明史上坐标式的伟大人物,没有悲壮的英雄感。韩冬红选择的是最生活化的人与事,特别是关于亲情记忆的书写,撼人心魄。在写这些人与事时,韩冬红写亲情中的那种微妙的意识一刻不肯松弛,紧紧盯住那些最容易被一般人忽视的微妙之处。她要的就是这些——“这些”是她散文的“魂儿”。
“四十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父亲狠心地一抬脚,就把六个孩子和无尽的苦难一股脑甩给了母亲。村里很多人觉得我们孤儿寡母可怜,洒下过不少同情的眼泪。”(《为了一句话》)也许,这是她心中永久的痛。在这样无尽的苦难中,母亲为了少不更事的“我”的一句阻止她再婚的话,一个人拉扯着六个孩子苦熬了四十年、不离不弃地跟随“我”四十年。所以,对于母亲,韩冬红着墨最多、用情最深,文字也写得最好、最感人。她写母亲风华正茂的岁月、不同寻常的“革命”经历以及牺牲自我、对子女无私的爱的付出。她写母亲的“那双脚”,她写母亲“不爱穿新衣”,她写母亲膝上的“黑”,她注重观察生活,捕捉母亲身上的闪光点,总能从细微之处入手,抓住母亲身上那些往往被人忽视的爱的“抓手”,书之写之,有细节、见性情。在《为了一句话》中,听说有人给母亲说媒,作者写道——
我心如刀绞。我没有像儿时那样央求母亲,我夸张地说:“您多大岁数了,还找婆家,不嫌丢人呀?”母亲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愣在那里,之后偷偷抹起眼泪。面对母亲的泪水,我不但不住口,反而变本加厉地大吼:“哭什么哭?嫁吧,嫁了这辈子我都不认你这个娘!”听此言,母亲一屁股坐在窗前,老半天没有说话,呆呆地仿佛一尊雕像。
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泪眼婆娑,甚至想哭,有一种心痛的感觉。第一次在《美文》上读到此文时已是深夜了,我还是忍不住给冬红发去短信:“……窝在沙发上一个人静静地品读《为了一句话》,从读进去之后,我的眼泪始终未干,甚至不能自控……为什么我们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们对母亲爱得深沉。通过您的文字,我触摸到了关于母爱的另一种表达。感动了,被您的文字,于是,马上想告诉制造这些文字的人……”她的《我娘膝上的黑》围绕母亲膝上的黑铺陈开来,千字文,精短、深情、巧妙。她从梦境开篇:“我说我娘,扶住墙别动,我给你搓搓膝盖上那块黑。我娘说别费劲,搓不掉。”结尾则是黑的延续、生命的延续、情感的延续、母爱的延续……“小庙上有个阿姨告诉我,你娘三天两头来小庙磕头,不是为这个儿子就是为那个闺女,还从没见过你娘为自己的事来给神灵磕头哩。”在这里,母亲的爱滔滔地淹没着儿女的世界,让人忍不住赞叹不已。
而对于父爱,冬红却是另一种表达。在《父亲印象》中,她虽然写的是“父亲的印象”,却因为父亲走得早,“我对父亲的印象是凭空想象的”,没有感官认识。全篇不叙父亲言行,然仅凭董叔、增叔等父亲好友的言行,父亲的品行已深透纸背。父亲的人格魅力从别人的细腻的言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妙。看其中的一段——
不想麻烦生活并不宽松的增叔一家,我和小哥去赵村买东西时,就会悄悄地从他家门口溜过去。那一次也不例外,却被增叔逮个正着。叔叔生气地抓住我的车把,泪水在眼眶里晃荡。“是不是嫌叔叔穷,不想跟叔叔亲了?”我和小哥被这久久没有靠近过的爱抚感动得泣不成声。
一个人的亲情记忆往往是和父母连结在一起的,而韩冬红的笔触却延伸开来,伸向自己的哥哥姐姐,伸向经历坎坷仁厚的奶奶,伸向有着曲折身世、渴望叶落归根的小姨,伸向革命情怀不灭、精灵古怪的五舅……可以说,韩冬红用自己的散文书写了难以泯灭的亲情记忆,书写了筚路蓝缕的家族成长史,书写了一个家族患难中情与爱的图谱……这,在我眼里很重要,也很有存在的价值;我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至此,再回望“宏大叙事”。我想,对于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而言,不妨从自己的亲人写起,把亲情记忆写好再言其他,不必好高骛远。我知道,世上,父母是最爱我的人,但他们从不言爱;我知道,如果需要,世上,父母是唯一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生命的人,但他们从来不会也没有对孩子唱过一句“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虽然,事实的的确确是这样。
我常想,比我更草根蚁族的我的父亲母亲、我的亲人们太渺小了,像小鸟一样,虽然从天空飞过,却不会留下一点痕迹。百年之后,谁能记起他们的名字,谁又能把他们付出的爱想起?名不见经传,爱却长存。父亲走了,我用怎样的行动再去爱他?母亲健在,她还在爱着我,又该怎样去爱她?蓦然间,我想对父母和亲人说:“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写作的意义!”如果我不记录下关于他们点点滴滴的爱,那么,百年之后,他们仅仅是家谱上的一个名字……想到此,我更感觉到韩冬红的亲情记忆的神圣意义。
那些政治事件,你写与不写它都会待在那里,等待后人的评判;那些名山大川,你写与不写它都会美在那里,等待文人的歌唱;那些历史文化,你写与不写它都会躺在书里,等待大家的钩沉……普通百姓的生活还得由自己去关注,亲情记忆还得由自己去留存——韩冬红的眼睛向内,深挖亲情的厚度、拓展亲情的广度,让我感动。
我想,关注社会还是从关爱自己开始,书写江山社稷还是从留存亲情记忆开始;诚如常话说的“百善孝为先”,我们欲行善事,那就先从孝敬父母开始。
二、关于“底层关怀”与“悲情元素”
社会是人的社会,文学即人学。人,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最为活跃的因子。毛姆说:“文学基本上就是借文学为媒介的人生表现。”茫茫人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弱势群体也是大众群体,更值得人们关注,也期待文学的底层关怀。韩冬红的散文在亲情记忆的书写之外,还常常把目光投向被人们忽视的底层小人物,以悲悯情怀写底层,把底层真实的生活状况与底层民众的情感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
诗文本来是很自我的用来抒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后来被人们渐渐赋予它很多重负,“文以载道”,要以文明道、达道、贯道等。但在古文运动中,韩柳二人的许多名篇,反而是以写小人物、小事物而得以流传,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如韩愈的《画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之类,贴近世俗日常生活,写出了社会百态,刻画世俗生活及小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韩冬红的笔,关注的就是底层小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多数以悲剧收场,读罢令人扼腕喟叹,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哲人说:“我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实际上每人都不过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在期待世人和天使评定优劣。而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属于他们的“戏”往往充满悲剧色彩,这似乎司空见惯。但我们撕开悲痛之后,展示给世人的是他们所渴望的温情与平静,而萦绕他们的却是苦痛、迷惘与无奈。
人物散文难写,难就难在写出一个人的精神,像小说一样刻画人的形象。韩冬红笔下的人物性格迥异,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老家那个小村子》里不事农事、不务正业、多次“作奸犯科”的二奎;从武汉归来,见过大世面的三凤;《秋风吹走了保柱哥》中上过战场、立过功,经常开导“我”上进的保柱哥;“清秀端庄,说话柔声细语,从来没给谁红过脸”的“被唾沫淹死的女人”……她笔下的人物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本来都有美好的开端,却或多或少渗透着悲情元素,读罢让人叹惋沉思,乃至唏嘘不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大千世界,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是世界最容易忽略不计的群体,韩冬红的笔触指向他们,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这不是一种小资情调,而是一种大爱情怀。他们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更与何人说?韩冬红敏锐地走近他们、感知他们、书写他们,以一个女人柔软的心肠和温情的目光把他们呈现于公众视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颜色。贵贱贫富,悲欢离合,都属于我们的生活。
从字里行间中看到冬红的善,不管是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还是生活中的过客、悲剧小人物,乃至那些花草、树木、麻雀,他们和它们都是生命,都来自这个世界的底层,都值得去尊重与关爱,都需要我们去付出自己的真情。大概她是从乡下走来的原因吧,所以感觉到她从骨子里保持着的那份淳朴和善良。
因此,她的作品弥漫着一位女子生命的真与人性的善,彰显着一种道德意蕴,自然完成了一种审美效果。我相信,善和美是统一的,丧失了善的作品,也就丧失了美。
韩冬红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记人叙事,而是置身于作品之中,把“我”和要刻画的人物血肉般地连接在一起,“我”的感情随着笔下人物的行为而发生变化。作品虽然没有情节上的大起大落的波澜,但不乏情感的涟漪。她通过文字在坚持自己的平民立场,以平民意识书写平民情感,坦陈生活中的艰辛与生命里的悲痛。她善于通过小人物故事的演绎,展示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状态,从最终的悲情元素里给人反思与警醒。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底层关怀”与“悲情元素”的有机结合,还原了生活的本真面目,彰显了生活的无奈与生命的尊严,拓宽了散文创作的情感体验与审美空间。
三、关于“从容叙述”与“间接抒情”
韩冬红的散文以写普通人物见长,且叙事、抒情有机结合,将“从容叙述”与“间接抒情”相糅合,氤氲出独特的艺术气息。宛如一位风韵女子,款步轻移,演绎出优雅的姿态。
韩冬红的叙事能力近年来日渐老到、稔熟,叙事语言流畅自然,如叙家常,既平平实实,又悠悠然然,在平实悠然之中讲述人物故事,同时也把叙事的目的性乃至意图不动声色地隐于其中,继而让读者在叙事中接受人物、接受叙述的目的,完成散文叙事的审美追求。就叙事的浅层结构而言,她把握其斤两、剪裁、位置、精神,诸要素合理得体,有一种结构美和顺序美。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指出:“叙事结构顺序之妙,在于它按照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重新安排了现实世界中的时空顺序,从而制造了叙事顺序和现实顺序的有意味的差异。”她的叙事或顺叙或倒叙,或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甚至第二人称,营造了属于自己笔下人物的时空顺序。《父亲印象》《古怪的五舅及其秘事》《老家那个小村子》等采用的是顺叙,《为了一句话》《母亲膝上的黑》等采用的是倒叙,一顺一倒,都是文本叙事的需要,让人感觉“顺”得自然,“倒”得得当,叙事的火候把握得很到位,从容不迫,读来舒服。《西屋》《城市·乡村》等篇章顺序和倒叙交叉进行,借鉴了诗歌的跳跃意象,彰显了散文叙事的立体、丰腴之美。她能够把主观感觉点染客观事物,将二者无间隔衔接;融合情、事、理,打乱时间、空间的界限,让思绪穿越现在与过去、城市与乡村、人间与天堂;抓住一点或一线延伸开来,营构出一个立体的空间……
叙事散文中的叙事不是目的,关键在于抒发情感、表达情思和寓意。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直接抒情即直抒胸臆,就是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不借助任何别的手段,直接地表白和倾吐自己的思想感情,以感染读者,引起共鸣。其特点是:不要任何“附着物”,而是思想感情直截了当地宣泄;不讲究含蓄委婉,而是思想感情毫无遮掩地袒露。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介绍志愿军战士的几个英雄事例后,写下了一段抒情文字。现在看来,这种直陈肺腑的抒情方式,虽然显得坦率真挚,但未免直白、简单,再这样写下去就给人一种“学生腔”、不成熟的感觉了。间接抒情则指作者不直接出面,或者不直接抒心中情,而是通过触景生情、咏物寓情、融情于事、融情于理等方式,通过特定的语调来抒发感情,语言比较冷静客观,给人以成熟、深刻、耐人寻味之感。韩冬红的散文属于后者:间接抒情。
韩冬红基于对生命现象的个人体悟和对人性的悲悯,皆体现在从容的叙事之中。或者说,正是这种从容的叙述和悲天悯人的情感意绪的两相融合,铸就了文字抒情的质感。从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老家”为她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也奠定了她抒情的基调。“老家那村子再小,也和我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它给我留下的不仅是记忆,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让我触摸起来,经络清晰,久久难以忘怀。”(《老家那个小村子》)寻常的日子,她不断在岁月的物与事里怀旧,追寻那些老物旧事里所特有的风情及韵致。旧地重游、旧事重忆、旧物重现,不由得会触景生情、叙事融情。这种情通过她的叙述向外散射,并附着于事物之上。她写亲情、友情、世情,自然情动于故事中;她写西屋、城内中街、老枣树、荷花瓶、猫、麻雀等,这些都成了她内心情感的外在物化,看似写物,其实,都是在写人。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察物情,物亦关情。在这里,物人合一,物我两忘,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外在的鲜明形象,所追怀的人和事也便多了感情色彩。读者会跟着她优雅的叙事脚步,潜移默化地被她的朴实无华的文字所打动。
有些作者在人物散文的结尾处喜欢直抒胸臆或来段议论,以增添思辨色彩及思想含量。我喜欢韩冬红文章结尾的随意及自然,既间接抒情又意味深长——
我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再次面对母亲生命中的十字路口,我绝不会再对娘说“您别走”……(《为了一句话》)
“男孩拽来了在地里忙着劳作的大哥。我放下了手中的屠刀,稠密的桃子笑了。”(《大哥》)
“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追寻老枣树。那年我父亲忽然就没了气息,而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追随他。”(《老枣树》)
“但绷了一冬天的脸还是在看到麻雀一家的那瞬间,像迎春花绽开了。恰好有几只马蜂出出进进,正在忙着修巢。”(《邻居》)
她的文章的结尾往往戛然而止,文断而意未断。结尾似乎很随意,但却令人浮想联翩。
文如其人一点不假。韩冬红的文字就像她本人一样简洁、明快、爽朗,不矫揉造作,且不世俗。看几个句子——
“那一年,奶奶和她的荷花瓷瓶一样肚子都是圆乎乎的。不同的是瓷瓶里装着奶奶娘家人对她的美好祝福,而奶奶肚里装的是对大伯和三叔无处诉说的苦水。”(《荷花瓶》)
“冰终于抵挡不住我们的决心,虽然没有融化,但松开了互相拉着的手。”(《魔鬼训练》)
她的文字叙事抒情,无不恻恻动人,阅其文者,会其意也。冬红的散文情真意切,无扭捏态,少雕琢痕。就像有人评价郑板桥的一些诗词:“唯其情真,固言之亲切有味,不着力而自胜。”冬红文字的长处正在这里:有真情实感,不需要如何粉饰,不需要做许多文字游戏,却能感人肺腑,使人历久难忘。清人袁枚说:“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文章要想打动读者,首先应该在情感上吸引读者,征服读者。
四、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去年深秋,得知韩冬红正在整理散文,准备今年出集子。她对我说:“在你不忙的时候麻烦给写篇散文评论吧!”我爽快地答应了,可是,直到今天才有了这篇文字。和她相比,我太懒散了。
总感觉公安战线的人浮躁,坐不住,可是韩冬红让我感觉到意外。她说:“我一不会唱歌,二不会跳舞,三不会打麻将,人笨到如此地步,更笨的是至今我都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做些名不副其实的事。”是一个“只留书香在心间”的人。“不论身处何地,内心总能保持一份宁静”。
她看似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实则是安静之人。在散文沙龙上见到她,总是静坐一隅,像一位小学生一样认真聆听别人读稿子、评稿子,她一言不发,很有淑女范儿。她说:“我喜欢安静,当认定要写散文时,就更安静了。但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单位事太多,有三个省级信息网需要审稿,一个市级网需要上稿,另外每半月一版报纸,累死……”在工作中,她绝对是一位拼命三郎。在她面前,我真的有些汗颜。
想起一副对子:何物羡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我知道,韩冬红能写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确勤奋。三更灯火五更鸡,读书不辍、写作不辍、进步不辍。人生总会有灾和难、痛与苦,韩冬红早就练就了面对苦难的淡定心态,并从中学会了在苦难中寻找幸福的存在。她曾说:“我个人觉得这种文风的形成是生活磨砺的结果。在乡下和城里,我受的苦是一般人所没有的,但是我还是很快乐地活着,它取决于母亲对我的影响。现在看来经历磨难不是件坏事。它让我成熟,也让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苦难之后的大彻大悟。拈花一笑,云淡风轻,这样一个人是何等的坚强啊。
我相信艺术都是相同的,虽然有天分高低的存在,但是必须勤于研习,这是不可或缺的一门功课。如习拳棒,当以研练之功不少简短;轻于试用,必致为害。大画家黄宾虹说:“所谓练习者,法有未备,则研究法;气有未知,则研究练气之法。法备气至,始为成功。而后出而问世。毁誉尤当不介于心。”
韩冬红的宁静与执著成就了她的文字。
韩冬红有个性,八小时之外,和人较上了劲,写家人、写友人、写身边的人乃至写路遇之人。她说:“每次我都会在不得不写的情况下动笔,那里是用我心血和泪构筑的,她有时是我的亲人,有时是我看到的一个路人,而有时候她又是我的朋友。”在我眼里,她的写作题材不宽泛,就在人物的小圈子里打转,乐此不疲,不像有些作者喜欢跟着潮流的风向标走。入迷了?我不知道,她说她的兜里和手机里储存的这样的资源还很多,够她写一阵子了。开了头,似乎没有驻足的迹象,散文艺术要把她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她不知道,她要做的就是跟着它走,无怨无悔。
她在真实记录着眼中见、心中想,用一字一句、一篇又一篇的文字记录着与她相关联的事物和人物的历史片段,让他们和它们在历史云烟、后人记忆中存在。
这里浸染着韩冬红的泪水、汗水和心血。我想,也许长留青史的,不是锱铢必较的物质利益,而是与艺术肝胆相照的真实记录。
我想,属于冬红散文创作之路,是她的师法造化时期;未来的路还长,通过她多年的从容汲取,一定会积健为雄,风光无限的。也愿冬红在经营好自己文字的同时,同样“经营”好自己的身体,陪伴在母亲身边,偷得这世上最幸福的浮生之闲;岁月静好,享受生命。
接到韩冬红的电子文档书稿快一个月了,我读来读去写来写去,始终不能尽快结稿。写着写着有时不敢轻易动笔,我怕自己拙劣的文字写轻了这份厚重的情感。虽然断断续续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文字,依然意犹未尽。
这样一个夜晚,独自一个安静的世界,电脑与茶陪我伴我,我们一起无语。我与冬红对话、我与冬红的文字对话、我与冬红笔下的人物对话、我与我自己对话……没有人能够让我品评这么长时间,没有一篇评论让我说这么多话。今晚,我必须为我的“发言”画下句号,不管圆满与否。
城市里,置身于高高的楼房,悬空生存,地气难接;只见三更灯火,不闻五更鸡鸣。敲下最后一个文字,不知东方之既白……
(作者系著名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