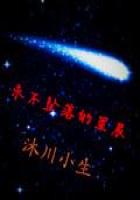却说翌日早上,因为担心穿越之旅而一夜没睡的风华,正扶着地牢的墙壁慢慢练习走动,忽而敏感的听到了脚步声,便赶忙趴回到草甸之上,装作昏睡的模样。果然,过了片刻,四个狱卒便打开了牢门,从一旁的泔水桶里舀出一瓢****,泼在了风华的身上。
“下、贱东西,起来!”狱卒扔下水瓢喝道,踢踢打打的拎着风华的镣铐把他从草甸上拖拽到地上,由两个狱卒摁着他,另外两个给他套上了一副枷锁。
“你们要干什么!”风华问,语气里透露出一股恐惧而紧张的神色,这是在接连几日的拷打中不曾有过的。甚至连这几个狱卒,见到风华难得的恐惧,都不禁流露出一丝惊讶。
“少废话,”狱卒凶狠的拽了一下枷锁前的铁链,强迫风华跟着她们朝牢门外走,同时鄙夷的唾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干什么不干什么,岂是你能过问的——快走!”
风华因身上原本有伤,身体又还处在虚弱中,即便不愿走,又怎能奈何四个狱卒的拉拉扯扯?他不由自主的随着铁链的拖拽离开了地牢,目光向身后望去,心头的恐惧感一点一点的增强。
今日,他应该待在地牢里等罗依相救的。可如今算是怎么回事?她们要带他去哪里,罗依要如何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风华甚至希望自己只不过是被带到别的刑房去用刑,或者是和那个被捕的女杀手对质供词,可他却万万不曾料到,他竟被带着离开了硕王府,并且很可能一去不返。
屋内,硕王爷站在窗前,明知此处绝对看不到被带走的风华,却还是在此固执的凝视着窗外,茶杯捧在她手中,她却一口未喝。
“云儿,”在一旁坐着的筠澈唤道,“那风华已经被带走了,你对此安排,还不满意么?”
“不,”硕王爷轻轻的摇了摇头,回过神来,对筠澈温柔的一笑,转而坐到了他身旁,“我很满意——把那风华锁在明国的军营里,的确比废掉他的腿,更能摧毁他——可我,我不止想要毁了他,我还想要毁了姐姐,我说过,要让她体验我当年的苦。”
“让她的正君落入敌国手中,让她有苦说不出,让她恨、让她疯,不是更好吗?”筠澈说着,握住了硕王爷的手,“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受我受过的酷刑,哪怕是我的敌人。我也不想让你动用那些酷刑,我不希望你与你姐姐用一样的手段,你不是她,我不愿你效仿她。”
硕王爷一时没有说话。
自从昨日她坦言要让风华承受筠澈所受过的所有苦,筠澈的心思便缠绕在了这个问题上无法释怀。前些日子,筠澈也如此纠结过这个问题,可从未像昨晚那么强烈、那么固执。想来,硕王爷也能理解,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记忆的人,筠澈被德王爷拷打逼供的经历,想必是他人生中最恐怖、最惨痛、最不堪回首的过去,而他肯定也不会希望历史重演。
可是,筠澈如今落得一个几乎和废人一样的结局,而她只把风华送到明军的军营里做俘虏军奴,这样的报复真的足够吗?她知道姐姐对风华的是动了真情的,否则不会在一个失宠正君身上反复留情——她爱的男人成了残疾,而姐姐爱的男人只去做做苦力粗活——这不公平,这不是报复,这不是她想施加的痛苦。
想到此处,硕王爷猛然站起来,走到门外,对侍官吩咐道:“你快马加鞭传令给明国的李将军,就说那犯人风华,是他那死对头德爷最宠爱的正君!倘若他还是个有血性的男人,就该尽其所能的羞辱,以偿还德王爷曾给他的耻辱……务必让此事闹得越大越好,让流言传回京城,让德王府知道。”
那边风华已经被带出硕王府,这边罗依也已早早动身,按昨日风华所说的地址寻找那件古玩店。
她正在街上边找边走着,忽而听到一声声的开锣喝道,她便与其他百姓一起自觉地站在了道路两旁。罗依原本以为这不过是某个官吏出行罢了,却不料,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一辆囚车,而囚车里的犯人,赫然就是风华!这真的是风华么?罗依觉得自己应该是眼花了,这怎么可能是风华呢?他不是还没画押吗,他不是应该待在地牢里等她救出去吗?
罗依满脑子都是解不开的疑惑,只能瞪着惊讶的眼睛,无意识的跟着囚车行走。
风华站在高高的囚车里,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罗依。作为唯一一个执着的跟着囚车走的人,她实在是太显眼了,风华很着急的想暗示她停下,她如果再这么没头没脑的跟下去,别人也会注意到的。他甚至想告诉她,他要被流放到明军的军营为奴,可他却一个字都无法说出来,更来不及再多看看罗依——囚车在路口拐了个弯,他的脖子被枷锁固定着,没办法扭头。
罗依看到囚车拐弯,心中愈加焦急,推开前面几个挡路的人,可她也只跟着囚车拐了弯,就再也没有往前追,终于,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反常行为。
她的脚步停止了,心跳仿佛也停止了。
注视着囚车渐行渐远,罗依将瘫软的身子靠在了墙上。无助、恐惧,潮水般的袭来……风华怎么会被带走,风华怎么能被带走!她怎么办,小远怎么办,谁来告诉她,谁来帮帮她,她到底该怎么做。罗依将头紧紧的贴在墙壁上,希望那坚硬的触碰能让她清醒,她像一个精神患者一样执拗的盯着蓝天,只有看着天,才能不让泪流下来,现在落泪,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不安全的。可她最后还是没抗争过泪水,眼泪还是火辣辣的流下来,让罗依不得不狼狈的逃窜到附近的巷子里。
她哭了好一阵子才渐渐平复下来,好容易略微冷静点的头脑,让她想清楚,当务之急还是要去古董店找白衣老妇。想到此处,罗依勉强支撑着快要瘫软的身子迈开步子,沿路来到了风华所言的那家古董店——然而——这又是什么情况?
罗依呆呆的站在店门口,觉得最后一丝力气也被抽光了,两个白衣白裤的姑娘正踩着梯子拆牌匾,几个白衣白裤的少年正往车上搬运大小不一的包裹,看此情景,大有停业搬家的打算。罗依跨进门槛,但见店里已然清空,一个白衣少年正站在空荡荡的柜台旁,用手帕把一些细软包起来。
“小兄弟,”不得已,罗依只得对那少年问道,“请问你家店主在哪里?”
少年专心的把一枚翡翠戒指放在帕子里,头也不抬的答道:“在隔壁的铺子吃早点呢。”
还好,到底给她留了一线生机。罗依赶忙谢过少年,匆匆跑到了隔壁的酒家:整条街上,唯独这处酒家早上还卖早点,汤圆极其有名,整个屋里坐满了客人,然而今日的气氛却不比往常,屋内偶尔有人低声交谈,同时也弥漫着一股股诡秘、紧张、不安的气氛。罗依环顾四周,立即就发现了制造这种反常气氛的来源——她没有找到白衣白裤的老妇,却找到了一个一袭白衣、风度翩翩的年轻公子。
在景国,绝对没有大早晨能抛头露面的男人,即便是做奴隶、奴才的男人们,也断然不会在公众场合吃饭。而这位白衣公子不仅犯了这个忌讳,在他的桌上,甚至还放了一把拴着纯白流苏的宝剑——看此情形不难判定,这个白衣公子恐怕是明国人——而这也正是让屋内众人紧张而不知所措的关键,她们反感有胆敢有男人与她们一起吃饭,她们甚至明知对方是敌国人,却因为如今景国日渐战败的颓废趋势,不敢轻易找这男人的茬。
白衣公子倒丝毫不在意身边女人们的眼光,慢条斯理的吃着碗里的汤圆。在罗依踏入门内之后,他便放下了羹匙,抬起眼来,递给罗依一个温和的微笑。
“你是罗姑娘?”他问,在气氛诡秘的店内,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清越好听,见罗依局促的点了点头,他便又招了招手,“过来坐吧。”
感受着周遭异样的目光,罗依坐到了白衣公子面前。
她刚刚坐定,白衣公子便微微一笑,先行自我介绍道:“在下白沐尘,今天是专程替奶奶收拾店铺的,奶奶临走前告诉我,你今天可能会来找她。”
“你奶奶……她去了哪里?”罗依问,“她还对你交待什么了?”
“她要回老家处理些事情,”白公子答道,语气显然禁止罗依对此多问,复又转而道,“她临走时说,如果你想出京城,可以和我一起走,我们恰好顺路。”
罗依对老妇留下的这番话匪夷所思。
她不想出京城,小远还留在德王府里,她怎么能出京城!她找那老妇,只想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延长在景国的时间,更想知道怎样才能把风华救出来。
“我不想出城,”罗依绝望的说,垂下眼睛,觉得自己眼眶有些发烫,但她克制着不让自己在外人面前哭出来,忍了好久,方才对白公子礼貌的一笑,“替我谢过你的奶奶,我先……”
“刚刚外面那么乱,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白公子打断她。
“大概是,有辆囚车经过吧。”罗依说,提及“囚车”二字,她的心里有一阵难过的翻腾。
“我也听说是这样,”白公子说,仿佛丝毫没察觉罗依脸上已经很明显的红眼圈,谈论天气一般的轻描淡写道,“好像那犯人和明国有什么瓜葛,刺杀王爷未遂,现在要送回明军的军营里发落了。”
本来一直沉浸在不知所措的伤心中,正神情恍惚的罗依,听到白公子这句话,陡然打了个激灵,立即反问:“明军的军营?”
“是啊,明军已经攻克了洛城,现在就驻扎在城内。”白公子漫不经心的说,但一双眼睛却紧紧的盯着罗依,默默的观察着她的每一丝神色。
“洛城在哪里?”罗依追问道,发现白公子微微扬了扬眉梢,勉强一笑,又补充了一句,“我……我不是本地人,对地形并不熟悉……那么,洛城离这儿有多远?”
“如今正值战乱,从京城到洛城,大约需要半年左右吧。”白公子答道,正欲问罗依什么,忽见一个白衣姑娘走了进来。
“少爷,东西都置办妥了,现在可以动身了吗?”
白衣公子朝那姑娘点了点头,随后也站起身来,向罗依简单而礼貌的告了别,拿起自己的佩剑向门外走去。罗依注视着他的背影,不知道是否该追上去——那老妇暗示她与白公子同行,意思就是要她去洛城救风华吗?洛城与京城不过半年时间的路程,由此看来,明军不久之后就要侵、入京城,德王爷能保护小远那么久么?
救风华,她一个人要如何深入明国驻军?她肯定不能带着小远去找风华,这一路上实在危险,她不能让孩子冒险。那她还能做什么,直接带着小远走,毕竟风华的心愿是让小远活得好,可她又怎么能放弃风华!
风华分明是景国人,却被当成明国奸细送到敌人的阵营——罗依知道明军是怎么对待景国男人的,放弃他,就等于杀了他。
怎么办,谁来告诉她该怎么办!
就在罗依坐在桌旁万般纠结的时候,白公子忽然又回来了,他站在门口看着她,问了一句:“罗姑娘,我就要启程了,你——走还是不走?”
走还是不走?
罗依无端的想起她昨天对风华匆忙离别前的承诺:不离不弃。
她抿了抿嘴角,最终站了起来,跟着白公子跨出了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