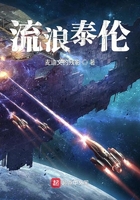纯粹
记得小时候,祖父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小男孩上了半年学,他爹想考考他,就用脚在地上划了一横,问那是什么字,小男孩不认识,惹得他爹大怒,说读了半年居然连“一”字都不识,小男孩委屈地说,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一”字很细,没有那么粗。
这个笑话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可以说,小男孩为现象迷惑,没有上升到本质层面,因而不过是笔画粗细上的变化,竟然让他连一字也不认识了。也可以说,小男孩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一字当作本质的一,其他的种种写法也就不是一了。对这个笑话进一步的反思,或可归结为耽于纯粹。
纯粹的爱情,纯粹的友谊,纯粹的灵魂,纯粹的理性,纯粹的人,诸如此类的语汇我们是很熟悉的,在互联网上搜索,还能看到纯粹摄影、纯粹邪恶、纯粹回收、纯粹偶然,等等。显然,纯粹是人人向往的。作为一种理想,一种境界,纯粹当然是值得追寻的。问题是,没有什么纯粹在某处静静地等待我们,存在着的都是不纯粹的。
生活中,我们总是期待纯而又纯的东西,稍微有点不纯,就对它的性质发生怀疑。沉迷在爱情小说中的读者往往以为,要爱就不去计较身高、相貌、收入、工作,爱是纯粹的,没有一点杂质的。初涉爱河的人,往往对父母讲究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想法不屑一顾,觉得那是庸俗的态度,为爱而爱才是天底下最纯粹的爱情。殊不知,他/她所谓的纯粹,其实并不纯粹,也是有所企图的,只不过和父母的企图不同罢了。父母的企图是现实的,儿女的企图往往是表面的,或者,对自己的企图一无所知。
人们往往感叹,世间纷杂,物质的诱惑太多,人性又善变,无法营造一个纯粹的环境,来容纳纯粹的感情。按照这样的逻辑,纯粹真是温室中的花朵了,它的酸涩、无奈和无力,不正表明了不可能和无能吗?无论环境怎样恶劣都能坚持不懈,才是纯粹的。纯粹正是体现在对纯粹的追求中。如果把纯粹和注定使它产生的过程截然分开,从而把一切辩证的过渡都排除在外,只能陷入把最终目的和运动分开的空想。
为了纯粹,先得承认不那么纯粹的因素,接受它,适应它,同时又孜孜不倦地和它斗争,该妥协的时候也得妥协。对纯粹的追寻与其说是向着某个对象,不如说首先在于改变自我、提升自我,同时又塑造着对象。纯粹既是最终的目标,也是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和培养起来的。
上面这些,是读卢卡奇《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时想到的。
缩略语
用较短音节的组合替代相同指称的较长音节组合,就是缩略语。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不过,直到现代汉语诞生,缩略语的出现才越来越频繁。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缩略语更是成为普遍的现象,除了各类人名、地名,各类组织机构或企事业单位的名称,社会生活的表述中渗入了大量的缩略语。John Paxton在为Eve-ryman's Dictionary of Abbreviations所作序言中感慨:缩略语的生产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一门产业。
化肥、话费、房补、节育、语文、文艺、编程、保费、私企、思政、牡丹卡等等,都是缩略语。总这样说,反倒对其缩略性质没有感觉了。一些缩略语用得多了,完全可以脱离开原式独立使用,如北大、科技等。但也有一些缩略语,始终依赖相对应的原式才能获得理解,如工体、首体等。
缩略语是一种简化。既然是简化,在一般的场合使用还可以,正式的、庄重的场合就不能随便使用,得用原式;在背景相近的人们之间使用显得亲切,遇到不那么熟悉的人还是用原式恰当,免得让人迷惑。周晓康在《人名的缩略与简称》中说,长短不同的语词表示说话者之间感情的远近;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直觉中,很容易把短词与平等、友爱,长词与社会、心理差距联系在一起。
缩略语的出现,主要在于原式使用频繁。音节组合较长的原式为人频繁使用,必然要求缩短其自身的长度。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国家刚推行义务教育法的一段时间内频频见诸报端,因而出现了“普九”。除了简洁,原因还在于,有些原式所指称的对象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由此,表达该对象的原式就一缩再缩,至于极限。
缩略语的大规模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信息传递出去,体现在语言上,就是用尽量少的音节组合去表达丰富的内容。音节减少丝毫无损于意义,反倒彰显了时代或某个阶层、年龄段、圈子的特点。
形容词
读小学时写作文,老师一再要求多用形容词,形容词用得多,老师红笔圈圈点点的就多。我抓耳挠头,绞尽脑汁,拼命地想这里该加一个什么形容词,那里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一下。有了形容词,名词就鲜活起来,丰富起来,充实起来。若没有形容词开路,名词就显得干瘪,空里空洞,句子就没有生气,像条死鱼。
后来,知道了通感的妙处。原本形容声音的词可以用来形容味道,形容天空的词可以用来形容大地,一切的感觉都是相通的,一切的形容词都是可以互换的。如人们常用“甜美”来形容歌声,“甜”本属于味觉印象,“美”属于视觉印象,“歌声”则属于听觉感受。钱钟书在《旧文四篇·通感》中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譬如,“响亮”一词,是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热闹”、“冷静”二词,把表示温度(触觉)的“热”与“冷”同表示听觉的“闹”与“静”结合起来,通同一气。
《荷塘月色》中有这样一句:“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荷香为气味,只能以嗅觉感知,歌声为乐音,凭听觉方可获得。但朱自清把“声”、“香”联系起来,嗅觉与听觉得以沟通,使读者生发这样的景观:歌声从远处高楼上飘来,无法听得真切,只能时断时续,隐隐约约,却更具吸引力,使人不由自主地凝神倾听;荷香淡淡,不会浓郁扑鼻,只能时有时无,如丝如缕,然而愈是如此愈能唤起人内心微妙的情感,情不自禁地去捕捉这种令人喜悦的清香。“声”与“香”这两种作用于不同感官的知觉,由于在人的心理反应上存有相似点,得以自然而然地沟通。此外,“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一句,也有通感的效果。以“旋律”、“名曲”喻指光和影疏密起伏和轻重浓淡的色调,读者的感受也就不再停留在单纯的视觉上,而是诉诸听觉。通感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小提琴有着高低起伏的音律和轻重缓急的节奏,它的和谐与光影的和谐有着天然的相通,两相衬托扩大了意境的内涵,也给原有的意境带来了温馨、幽雅的艺术氛围。
人至中年,说话作文就越来越少用形容词了。人生这个词从一个人的唇中吐出,你毋需看他脸上的皱纹,但从他的声音,就能判断出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了。若他喋喋不休地使用形容词,那不外乎掩饰、夸张与撒谎:掩饰自己的富有或贫寒,夸大自己的幸运或不幸,以及自欺欺人。至少,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一切的名词都有一个或一些形容词伴随着,环绕着,后者决定了前者的性质。像童年这个词,原本就内含着稚嫩、可爱、快乐一类的意思,只不过有一些童年是不幸的、悲惨的,童年这个词反倒中立起来,仅仅用来指示某个年龄段。老师鼓励孩子们,以及小孩子们刻意地使用形容词,正是要给名词一个属性,一个确定,其中有引导,有发挥,有召唤,有对世界的想象和自我的期许。
通感的使用,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全身心地去感知生活,感受审美对象。“风来花底鸟语香”,将听觉的声音转化为嗅觉的气味;“风随柳转声皆绿”,是听觉的声音转化为视觉的颜色;“鸟抛软语丸丸落”,又是将听觉的声音转化为视觉的形象。“便教春思乱如云,莫管世情轻似絮”,人到春天的思绪乱得像飞云一样飘忽不定,世态人情轻得像飞絮一般不可琢磨,晏殊把主观情感视觉、触觉化了,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是抽象的情思,“春水”是具体的事物,两者似无关联,但一经沟通,这位亡国之君深长、沉重、无穷无尽的哀愁,就真切、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千年之后,依然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对中年人来说,形容词反倒是可有可无的了,所有的名词都蕴含了形容词,后者已经浸透在前者之中了。那些大量地使用形容词的人,不是缺乏自信,就是善于欺诈,刻意隐瞒什么,至少,也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其词。形容词用多了,就像浓妆艳抹的中年女性,没有自然的魅力,只能在皮肤表层涂脂抹粉了。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时代来说,也是如此。
文章三度(1)
早晨出门散步,忽然想到,写文章要讲究三度,即长度、宽度和深度。
所谓长度,就是说,要把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展开来,说清楚。这个来龙去脉可以是问题内部的,如由来、缘起、最初的讨论,以及后来的重新提出,不过,我所说的长度,主要是指问题所置身的历史链条。对链条有所把握,对问题在链条中的位置有所了解,文章的历史感就出来了。
所谓宽度,包括内在的宽度和外在的宽度两个方面。前者是在问题的内部拓展空间,让问题变得圆润、厚实,富有伸缩性;后者是在问题的外围东拉西扯,旁敲侧击,纵横比较,自由地发挥。
至于深度,和高度属于一回事,只是认知方式不同罢了。所谓深度,是把根扎下去,所谓高度,是让树干不断上扬。同样的立体,从下往上看,感觉到的是高度;从上往下看,深度的感觉就出来了。无论深度还是高度,都需要哲学方面的阐发。引入了哲学概念,一下子就深刻起来,崇高起来了。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题来说,我选择了1938至1942年间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作为主题。要想有长度,就得梳理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的线索;要讲究宽度,就得围绕旧形式、民间形式和新文学形式,把方方面面的意见都摆出来;深度或高度上的追求,自然离不开形式和内容这对概念。
文章三度(2)
生活的转型使得人们停留在室内的时间越来越长,几乎80%以上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因此,室内空气质量的好坏对人的健康生存异常重要。专家提醒,判断室内环境的标准有三,即温度、湿度和洁净度。
对我们这些成天看文章、写文章的人来说,文章也是我们的一个生存环境,看文章好比去别人家做客,自己写文章呢,就像建设自家的环境和氛围。在这里,温度、湿度和洁净度同样值得关注。
有的文章让读者耿耿于怀,有的文章让读者喜笑颜开,有的文章让读者心生寒意,有的文章让读者如沐春风……这些不同的读感我们都有过体验。这和主题有关,和贯穿于其中的情感有关。文章的温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情感的温度。那么,如何保持适度的情感,是写作时需要考虑的。该激烈时激烈,该缓和时缓和,该热则热,当冷则冷。
生活中离不开水分,过于干燥的空气会让人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紧绷,还会引起家具的变形、开裂,地板、墙砖的走形等。文章里同样需要足够的水分。和不同的题材相应,有的文章里小桥流水,有的文章里大河东流,有的文章里泉水叮咚,有的文章里山洪爆发……在阅读时,我们会感受到湿润,水汽的弥漫,或者水的流动、奔涌。
文章里的洁净度,主要体现在用词和句法上。语汇的干净,句法的利落,该柔软时且柔软,当缠绵时则缠绵,该断然时不犹豫,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功力。
一篇优秀的文章,在温度、适度和洁净度上都是无可挑剔的。读者感觉不痛不痒的文章,温度肯定需要调整;读者味同嚼蜡、干巴巴的文章,大半是湿度不够;读者觉得啰里啰嗦的文章,多数是洁净度有待提高。
读物四种
我把读物分为四种。
第一种读物是工具书、地图、健康手册之类。不一定每天都用得着,但有这些读物摆在案头,就绝对心里踏实。这些读物提供的知识是客观的,是可以作为学术研究和生活指南的。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是它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经验和策略,若是少了它们,我们难保陷入无所适从、步履蹒跚、犹豫不决的境地。
第二种读物是经典一类,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乃至数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我都会购置来插在书架上。有的经典是读了又读,甚至有数十遍之多,每一次都有新的感悟。有的经典刚据为己有时激动地翻看几页,而后就被束之高阁,难得再接受我的检阅。有的经典干脆直接成了藏品,但偶尔望望它的书脊,还是觉得厚实和宽慰。经典提供了高度,开阔了视界,它让我们深入到生命的深层地带,触摸到最敏感、最丰富的岩浆。经典给予我们莫大的感动,莫大的幸福。经典在手抑或书架,一如有伟大的人物相伴,即使对其中的思想不甚了了,也足以自诩和自满:呵,瞧瞧我的朋友,就知道我多有品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