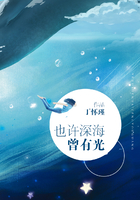其实,在夏侯濯说出那句:爱她的时候,她是有一瞬间当真的。
这样的一句话从一个这么好看的人嘴里说出来,哪个女子不会心动?
在看到夏侯濯之前,她一直以为段梚卿是最好看的人。
她想她对夏侯濯也许不只有恨?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的感情?
所以才会想都不想的答应他,嫁给他。
明明知道,他只是拿她当挡箭牌,兴许,她是有点痴心妄想的。
她在狱中甚至还妄想过,夏侯濯会去救她。
两个人的手十指紧紧相扣,十指连心,他们的心呢?
他们的心却隔得很远,很远。
身后的柳素盯着他们牵在一起的手,做戏……这戏到底是做给二皇子看的还是做给他自己看的?
一顶碉楼精美的轿子映入应昔的眼帘,夏侯濯伸手将她扶上轿,应昔有一瞬间的恍惚,好像他的温柔是真的一样。
“小心点……”夏侯濯笑道,狭长的眼睛弯了起来,风吹过扬起他的长袍,却没有吹散他眼里的笑意。
坐在夏侯濯身边,应昔浑身不自在,僵硬的挺直身板,闭着眼睛假寐,篡着裙摆的手透露她内心的不安。
柳素坐的是另一架轿子,那架轿子里的柳素掀开了轿帘,秋水美目望向前面那顶轿子。
夏侯濯眼睛睨向僵坐着的应昔。
这个女人,和初见时比起来,变了很多。
他的初见,是那时候在茶楼雅间半掩的窗里瞥到她的那一眼,那一眼他看到的是一个看似落魄却倔强的挺直腰板的小女孩。
再后来,他看到她仓皇逃出小弄,他只是朝着楼下倒了一杯茶,就惊起了不安的她,他以为她看向他的眼神会是害怕,或者紧张。
她只是淡淡的朝着自己这边看了过来,眼眸里波澜不惊,他曾经诧异于她的淡然。
她落魄的像是个乞丐,他就给乞丐施粥。
在之后,他很久没有看见过她,他都快忘了她了,施粥却成了夏侯府每天必行的善事,初衷是什么,他已经忘了。
直到后来,她撞破自己杀人,他差点就失手掐死她,她那时候艰难的呼吸,她面色坦然,她说:生何欢,死何惧。
那时候她还是一如从前的淡泊,好像生死都无所谓,连死士都怕死,她倒是显得坦然。
她的改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夏侯濯记得,好像是桐陵王来江南带走段梚卿之后,她变得怯懦。
特别是面对自己的时候,她总是小心谨慎,连说话都再三斟酌,甚至于连一个眼神都不敢给自己。
她说:她的勇气都源于桐陵世子。
她对自己的敌意显而易见,却毫无缘由。
兴许,她就是一条藏匿了毒牙的毒蛇,一旦被惊起就会张开毒牙淬毒入骨。
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在自己身边,虽然是用一个谎言维系的关系,虽然他们中间还隔着很多东西,但是她的身体里有自己的骨肉。
为什么他不去救她?
他想起柳素在自己面前哭的梨花带雨的脸,“濯哥哥,兵权还在我爹手里。”
他想要江山,就不能放弃柳素。
现在,紧跟着段梚卿的脚步,二皇子、罗氏摄政王也在朝着这里赶。
“二皇子,是我同胞的哥哥。”夏侯濯忽然开口,喉咙没有做好发音的准备,声音有点沙哑,“别问我是谁了,只要记得以后我是你官人。”
应昔睁开眼,眼睛瞥向暗红色的轿帘,“苌垣十四年天下归夏侯氏所有。”轿帘被风掀起一角,轿外漆黑一片,“夏侯濯……怪不得。”
轿里陷入无言,安静的连轿外随从的脚步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能下得一手好棋的人,怎么会布不得一手好局?”夏侯濯笑着道,他清楚的看到应昔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慌乱,伸手掀开轿帘,“你看,天真黑啊。”
“公子想说什么?”应昔顺着夏侯濯掀开的轿帘往外看去,外面黑茫茫的一片,晚上的街道是和白天的不一样,她领会过。
夏侯濯脸转向她,狭长的眼角绽放出笑意,“你说,我们的孩子叫什么好?”眼神自应昔白皙的颈脖移向她的小腹。
“公子,这个孩子与您无关。”应昔没有直视他的眼睛,依旧盯着已经垂下的轿帘,暗红色的丝绒轿帘起伏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轻笑,用宠溺的口吻,“怎么会无关呢?不然你生下来看看到底是像谁?”凝视着应昔消瘦的侧脸,“真瘦。”
应昔无言,重新闭上眼,紧紧攥着裙摆的手已经松开了。
“天乐。你说,天乐怎么样?”夏侯濯不依不饶,唇角含笑,满满的愉悦,“夏侯天乐。好听吗?”
“天乐。”应昔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天乐,天天开心快乐么?生在夏侯濯身边,他能天天开心快乐么?
她总觉得夏侯濯在策划着一个天大的计划,虽然她不知道他在计划什么。
“公子,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应昔睁眼,看向夏侯濯,但是还是避开了他的眼睛,视线停留在他如玉的手上。
“叫我官人。”夏侯濯眼眸弯起,笑着道,避重就轻的忽略了她的问题,眼睛一瞬不瞬的对上应昔的眼睛。
应昔不敢再出声,她瞥开眼睛望向别处。
夏侯濯奸计得逞似的笑出了声,盯着应昔发红的脸颊,“孩子都有了,你在羞什么?”应昔的脸愈来愈红。
“又不是你情我愿的……”她小声嘟哝,声音恰好落入夏侯濯的耳里。
他盯着脸红到脖子根的应昔,口吻暧昧,调笑道,“不如,我们你情我愿一次?”
她也会有脸红的时候,他还以为她是什么都不在意的木人,“脸红的时候,你才像个女人。”他一本正经,眼里却是掩不住的笑意。
应昔闭紧了嘴,一声不吭。
“听说,你喝了藏红花?”看着应昔紧张的绷紧了身子,夏侯濯脸上一派风淡云轻,口吻慵懒散漫,像是无意提起,“还挨了不少棍子。”
“这么瘦的人,能吃得消几棍子?”夏侯濯好似感慨,缓缓说道,“你都这样了,我们的孩子都还安在,你说是不是就注定你要和我有个羁绊?”
应昔僵坐着,她没有别的孕妇那样用手护着肚子的习惯,两只手僵硬的放在两膝上,她的肩颈也累的发酸。
夏侯濯说的话,她充耳不闻。
摇晃的轿身兀的平稳了,落轿了。
“到了。”夏侯濯起身,在轿子里他站不直腰板,弯着身子站起,修长如玉的手指搭上应昔的肩膀,看着应昔如惊弓之鸟一样看向自己,眼里的笑意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