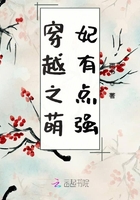一等段东麒从矿上回来,惠春爱就告状。段东麒除了心疼老婆还心疼女儿,见女儿吃个桃子就被骂成这样,着实恼火。又不好和贺红雨大吵,就阴着脸提着一把斧子往桃树下一站,冲着母亲的窗口大声说,妈,咱们把这桃树砍了吧,你看怎么样?这桃子谁也别吃了,省得以后生麻烦。贺红雨隔着窗户听见他这样的口气,心里就明白是什么回事了,顿时也心中也十分窝火,心想,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才娶了个媳妇就不认娘了,哪里还有一点点良心。于是窗户都没开,就隔着窗纸,在里面冷笑一声说,吓唬谁呢,砍吧,谁怕谁啊。又不是我每天站在那树下等着吃桃子。
段东麒本来也是气话,这外公家的老桃树长了多少年才这么大,人都死了三茬了树还活着,看着新的人又生出来,简直像这院子里最老的一个成员了,只是它不会说话而已。但听她这么一说倒觉得不砍不行了,人活一口气,不砍倒成了他们一家三口就是每天巴巴地等吃桃子的人。他提起斧子闭着眼睛就砍了下去,第一斧子下去的时候他几乎流泪,就像砍在一个老人身上一样,他都怀疑这树会不会流出血来。可是第一斧子下去第二斧子就不能不砍了,已经由不得他了。他便咬着牙乱砍下去,砍到最后手都软了,感觉自己像杀生一样,满手是鲜血的感觉。桃树带着一树的桃子终于倒地身亡了,桃子纷纷掉到地上,珠溅玉碎。这桃树的尸骸在院子里躺了好几天都没有人去动,谁都绕着它走,看都不敢多看一眼,似乎要由着它去腐烂了。
平时贺红雨每天出出进进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桃树,因为她老觉得在这棵树上能看到父亲、老姨太太和贺天声。他们并不显形的,只是她站在树下的时候似乎就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气息。因为他们都在这树下站过,都吃过这树上的桃子,所以现在就算是那些人已经不在了,可是睹物思人,一看到这树便觉得好像他们的魂魄还住在这树上似的。她每天从树下出出进进的时候便要向这树看一眼,其实却是在看那些隐匿在树里面的人,就像是,她在这一天里和他们打过招呼了。好多次她从树下经过的时候眼睛就会不由自主地变湿。她想这是怎么了,当年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时候,她是多么恨他们啊,她巴望着早一天能从这院子里逃出去。现在,她一个人像收复失地一样收复了这座废弃的城堡,也收复了他们留在这里的魂魄。她像是他们的主人一样守着他们,可是现在,她为什么还是有想流泪的感觉。
现在她一进门的时候老觉得那棵树还在那,就像一个人一样老在那等着她。可是进门一看,那里是空的,就像那个人突然就不辞而别了。没有了树,院子里一下空旷得有些荒凉了。正房厢房都赤手空拳地晾在阳光下,连一点遮挡都没有了,看上去就像人没穿衣服一样,别扭得很。贺红雨怔怔地站在那里,像是还没有反应过来那树已经不在了。她要在那站好一会才能醒过来,这棵树确确实实没有了。就像一个人死了一样,死了就永远消失了。她便绕过那片空地,木木地向自己的屋子走去。但是她嘴上什么都不说,绝不说一个字。后来她再一进门的时候就低着头匆匆往里走,还是要竭力避开看那棵树的影子。
她尽力避免去看那块桃树站过的地方,就像尽力不去看死掉的亲人留下的遗物,免得睹物思人。那天她正在街上走着,猛地看到路边有个小孩子在啃着一只大桃子,她突然就想到了自己家院子里的那棵桃树。突然之间她的泪就下来了,又像是看到了自己已经亡故的亲人。她边走边想,这桃树为什么会被砍掉呢,究竟是谁的不是。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想起了老姨太太,她看到她正对着自己笑。她吓了一大跳,路也不敢走了。老姨太太竟走到她面前笑着说了一句,你和我又有什么不一样?贺红雨走得快了些,她害怕看见老姨太太,可是这一路上她一直就听见老姨太太的小脚跟在她的后面。
她一边走一边还是不停地听到有个声音在自己身体里细细地响着,你和我又有什么不一样?你和我又有什么不一样?突然之间,她扶住墙就哭了起来,竟哭得像个小姑娘一样。是的,她和老姨太太……究竟有多少不同呢?老姨太太那么宠贺天声,那样对自己,因为她没生过儿子,她觉得自己没地位,她恐惧自卑了一辈子,才会对别人生的儿子那么好。那时她是真的恨那些男孩子们,包括贺天声,都是人,差别却是天上地下。她讨厌他们,讨厌这些老女人们。可到了她自己出嫁后呢,在没有生出一个儿子之前,她也是多么恐惧啊,她怕段星瑞嫌弃她,怕他对她不好了,不疼她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疼她?她没有了最起码的安全感。现在,她为什么那么不待见那个小孙女,还不就是因为她不是个小子,她觉得这个儿媳妇对不起段家,对不起她儿子,不能给她段家把香火继续下去,还有什么脸面在她面前理直气壮?可是,她有错吗?她不就生了个女儿?就像自己当年不是也生了女女,二女女,还有那个……死去的三女儿。像是在那一刹那,她突然惊恐地发现,老姨太太其实就站在她的身体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其实这么多年里她一直跟着她,一直就站在她的身体里,像一种毒液。现在,她和她合二为一了,她们合成了一个人。所以,她其实比老姨太太当年更残忍。
桃树的死亡像一种标志,自从桃树被砍倒以后,段东麒一家就和他们分家了。说是分家却还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仍然是他们住西厢房,段星瑞和贺红雨住东厢房。说是分家其实是分锅。分开各吃各的,到中午的时候,贺红雨在东边做饭,惠春爱在西边做饭,各冒各的炊烟,做好了都不让对方尝一口,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有时候看到惠春爱在煎肉,贺红雨第二天便也买来肉煎了吃,让肉的香味一定要压倒惠春爱的。她想,看我吃不起个肉?我还就要吃给你看。你一个外姓人,在我贺家的院子里威风什么?两个人像打擂台似的,一个吃了挂面,另一个就势必要吃挂面加鸡蛋。一个煎了碗五花肉,另一个就要煎碗纯瘦肉,还要放上多多的八角和生姜,一定要把肉味全都给逼出来,让整个安定县都能闻得到。
此后,贺红雨和惠春爱在一个院子里出出进进的就像不认识一样,互相都不看一眼。惠春爱有事要出门的时候,就是能把云云放到邻居家里也决不用贺红雨。贺红雨逢人就说,你说说这生儿子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是怎么拼着命把他生出来的,他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忘了我当初是怎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的。那儿媳妇更是白眼狼,你养她多长时间都养不熟的。当初那么困难的时候还舍得花了我们家的三百块钱,说穿了不就是被她娘家卖过来的吗?你看我那亲家什么时候敢上我的门,她做贼心虚,哪敢在我家门前放半个屁。他这一家子养着养着都养成仇人了。嗯?你们给我说说,这和仇人有什么区别?我就当我从来没生过儿子,就像我们家的老姨太太一样,一辈子没有儿子也左不过这样了,我看我老了是连她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