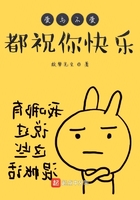戴长乐先是一愣,然后忙走过来做了个揖,先向许平君和杜君宁陪了一笑,叫了声“姐姐”,又向刘病已这边叫了声“大哥”,陈遂乐了,“呵,你小子有胆儿啊,你在这里干什么?”
戴长乐有些羞赧,“小弟说来拜寿,两天便回怕父亲疑心要打,听说有个集会也来逛逛。“说完,让店家再送两只烧鸡上来,又看杜君宁青衣灰鞋,头脸素净一丝装饰也没有,乍一看甚不起眼,觉得奇怪:”姐姐,今天怎么这副打扮?“
杜君宁刚要回他,杜佗作势咳了两声,杜君宁没理他,“不是集会上人多嘛?怕有些登徒子没事找事。”
戴长乐心想这登徒子指的不就是自己吗?红透了脸,也觉得没意思,低了头一边坐着。
陈遂又说:“你看你可疑的很,你不消走,跟我家去,过两天一起去你家看看,是不是贼看了便知。“
戴长乐觉得有人跟自己一起回去也好,父亲也不好十分教训,自己也得多玩几天,想都不想就点头说:“也好,也好。“
刘病已附耳陈遂说:“你真去啊?”
陈遂说:“这小子家法严,我让他多游荡几日回去好挨骂,再说我们一向不曾到北边去玩,你们如今再回老宅去,不怕有人说亲吗?不如避到茂陵去玩玩。”
张彭祖靠得近,听清清楚楚,点头说:“这话有理!”
刘病已也不再言语,一伙人看完了戏,又转一圈,可怜戴长乐那五个家人就像专门为了替他们提东西的一样,杜君宁看一样,戴长乐就在旁边叫好,又说时兴,又说有趣,吃得玩的,吹的打的,穿的戴的,杂七杂八,不等陈遂上前,他就麻溜的会账,把个杜君宁奉承的欢喜极了,戴长乐一口一个姐姐,杜君宁口口声声叫他戴长乐,两个融洽极了。
陈遂看着杜佗不住的递眼色,杜佗只摇头。许平君看着都称奇,怎么一时就像旧相知一般?
临走又每人吃了一碗油茶,回到家里杜君宁吩咐家人说:“这是戴长乐戴公子也是家中的朋友,今日集上会见邀来家的,你们不许怠慢!”说着,让人带那五个家人下去吃饭,让人给他们喂马。
陈遂听得这个话,气得直跌脚,”这是我朋友?“
杜佗下意识挠了挠头,张彭祖见了,笑对陈遂说:“你今日集上买了帽子!”
被杜君宁听见,指着他脸骂道:“你们每日称兄道弟,登堂入室的他不戴帽子,戴长乐就是戴帽子了?”
张彭祖忙陪礼,“是晚生不才,不曾想给兄弟戴个帽!“
杜君宁气得跳起来,撸起袖子叉起腰,冲上去就要打。平君靠得近,一把抱住她的胳膊:“好姐姐,你跟他计较什么?他胡说的,这些混话不理他就行了,反去争什么?”
杜君宁一腔的火气,哪里听得下,许平君身单力薄何尝是她的对手,被她一甩一丈远差点没站住,亏得戴长乐就在后面离得近扶住了,刘病已赶上去将许平君拉定:“你快回屋去。“
平君犹豫了一会儿,知道自己也是劝不住的,在这里让病已担心,看了他几眼,点头去了。
戴长乐见众人为他闹得这步田地,心里也没趣,只说:“大哥,姐姐,莫不如我这就走。
张彭祖和杜君宁同时叫道:“你敢!”
张说:“你惹下的事,你躲哪里去。“
杜说:“你走什么,我不让你走,谁敢让你走?“
杜佗急得叫道:“姐姐,你听我说,他是胡说,你大人大量,不要听他这狗话!“
陈遂一屁股坐在堂上:“罢了,罢了,丢下我这脸不要了吧!“
杜君宁啐了他一口,“你丢什么脸了,同是个朋友,怎么姓刘的姓张的来得,姓戴的就来不得?”
张彭祖冷笑了两声,“不是姓戴的来不得,只是明日你还交姓王的,姓龟的呢!“
杜佗急得跺脚,“你放屁,一嘴的胡喷,你几只眼看见的?姓了王,再辩不迟!“
杜君宁兜胸一脚踹过去,刘病已急扯着张彭祖朝后,两人跌在了一处,杜君宁一脚踹空也摔了跤,杜佗赶紧上去抱住:“亲姐姐,你看我面上,你可别动手,我替你好好骂他,明天叫他给你陪礼。“
杜君宁握住杜佗的手,两眼垂下泪来,”好兄弟,还是你肯为我着想,不像有些人屁也不放一个,看着我被人欺负。“
陈遂坐在地上,回头看了一眼,实在没什么说的。
刘病已起身上前,和杜佗一起将她扶起来,温言说道:“不怪你要生气,他这话说得混账。但是看在往日的相知上,你认识我们岂是一两天的吗?你看长乐吓得,你们今日为他动了手,大家没趣。陈遂不为你说话,是他敬你的意思,他敢拦一下吗?还是让你打呢,不让你打呢?今天也逛了一天了,你也累了,让他们把新买东西给你送到房里去,明日歇一天。”
杜君宁抹抹眼,刘病已扯了陈遂起来,掐了一把:“赶紧回房去吧!”
戴长乐吓得靠在墙边,动也不敢动,直到见他两个走了才喘一口气,摊坐在地上,刘病已说:“这不关你的事,你好好歇歇吧!“说完同杜佗两个人,拉着张彭祖回房要说话,张彭祖气呼呼得还不肯走,刘病已板起脸斥道:”你发作这一顿,你还委屈了?你没有姊妹出门吗?不曾交过朋友吗?青天白日放着我们大家在旁边,什么王八乌龟,我看你是热昏头了!“
张彭祖心里不服,口里不好回说。陈遂急匆匆跑进来,叫人说:“快让厨下,煮一碗桂花蜜藕送进房去。“说完,探头从杜君宁刚才坐处拾了个面具,回身对他们说道:“这是彭祖为我的心,我看没什么错的!“
杜佗和刘病已奇得睁大了眼睛,陈遂把个张彭祖的肩拍了几拍,念道:“你说的就如我心里想得是一样的,可是我能说吗?难为兄弟你受了这场屈,咱们当男人的只打碎了牙往肚里咽吧!从此也不消提了,我只当是命!“
戴长乐在角落听到这话,“大哥,这真是没有的事啊!“
陈遂瞟了他一眼,不想说话。
杜佗说:“你既如此想,他两个在集上,你怎么不当面拦着!”
陈遂顿时气短了半截,刘病已圆场道:“你只戴上鬼脸背后装人吧!“说着替他戴上鬼脸,推着一起出去了。
陈遂一路回了房,他们几个也各自回房,平君不放心就在门口等病已,病已上去牵了她的手,“做什么,在门口站着。夜风不冷吗?“
“不冷,不冷,怎么样了?不闹了吗?“
“没事了。“病已拉着她就在月下坐着,那一片月色亮汪汪的撒在院里,人就如坐在水里一样的,平君轻轻靠在他肩上,“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呢?”
“你想回去吗?”
平君摇了摇头,“不想!“
“那就好了,我这次回去之后,是再不得闲了,咱们见面都要难了!“刘病已叹道。
“为什么?”平君意外道。
“因为明年我大了,张公和叔公和舅公们商量要找个差事,下半年要学一些吏法,明年就更分不得身了!”
许平君心下替他添了几分忧虑,担心他学业太重,又怕他前程不顺,还恐不得相见要生变数,刘病已将她的神情全都看在眼里,握住她的手说:“你只好好在家里做些针线,安心等我就是了,一点事没有。“
只这一句话,就是治她的心病的良药了。月明如水,清风徐来,两人坐在阶前,地下倒影成双,如画如梦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