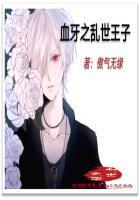“只不过...刚刚那个洛景枫已被你一脚揣进了十八层地狱,现在坐在霍小姐面前的只不过是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
天哪,你不是来道歉的嚒,怎么听着像是来挑衅的呢!
另一个声音在洛景枫的体内不可思议地惊叹着。
这家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好话歹话,捡起来就说,一点也不计后果。
这一刻,被激发出了无穷斗志的霍雨桐总算是抬头瞧了他一眼,只是那眼神中敌意尽显,好似连弩发发狠厉,让人看后不禁有种透骨寒凉之感。
“你跟卢庄是什么关系啊?上次见你们俩一起去听戏,好像还挺亲密的...”
洛景枫觉得自己刚刚言语欠妥,收回了些理智的他决定放低姿态,可没成想自己竟又说了句不太中听的话。
呦,真新鲜,对面这家伙竟关心起自己同卢庄来了,且这话怎么听都有种醋坛子被打翻的酸涩味。
“你是我什么人啊?我跟谁一起做什么事需要向你解释嚒!”霍雨桐毫不客气地丢了话给他。
算你狠,一句话直接把洛景枫噎到了墙根底下。
哎,刚才怎么没人叫酒,真扫兴,洛景枫只能低头猛饮了两口茶。
“啪”的一声,他将茶杯撂在桌上后,靠在椅背上不爽不快地又言道:“有意思么?你这么对待我有意思么?”
“你和蒋伟诚那天如此羞辱我,你觉得你有意思么?”
“好,如果你还对那天的事耿耿于怀,那我今天,我洛景枫今天就在这给霍小姐你赔个不是,行不行?”
话虽到了,可语气中却听不出半点诚意来。
“太迟了,你的道歉太迟了,我受不起...”
霍雨桐依旧冷言冷语,冷漠至极。可她心里的那道坚强壁垒却不知为何正在瓦片纷飞。
被对方用刀子逼进了漆黑的角落,洛景枫想哭想叫可最后却只发出了几声冷笑。
“对,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从来没有,要想让人喜欢你得有让人喜欢的资本,你长得好看么?你性情温和么?就你,一个姿色平平,冷酷淡漠的女人,我除非是脑子坏掉了,才会对你动心!”
声嘶力竭中充溢着满满的自我质疑。
是啊,他当然不会喜欢我了,他那么一个自高自大的人,连基本的尊重都没弄懂,又怎会对一个平庸的我动心呢,从前种种充其量也就是为寻个乐子罢了。
更何况他刚刚不是还送鲜花给了一个漂亮的女伶么!
一声冷哼夹杂着五分苦闷,五分肃杀盘桓在幽南山内久久不散,令人于凄凉萧索中找不到生路。
“你的喜欢我从不稀罕,更不敢奢望,还是留给你自己慢慢寻欢吧!”
心头的那滴泪几欲滑落的最后一刻,霍雨桐起身便走,没再犹豫。
这场冷战终于结束了,旷日持久,却也是弹指一间。
这么多年来,他洛景枫的意识里从来就没出现过“认输”二字,可这一次,他输了,真的输了,彻彻底底地输了。
该说的话一句没说,不该说的话却是不绝于耳。
怨不得旁人,这一切都怨不得任何人。
谁让自己是个口是心非的硬骨头,活该被人淘汰,被人唾弃。
幽南山内静坐的洛景枫此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孤独。
自己就好比一只被放逐于冰天雪地中的孤舟,飘荡无依,漫无终极...
好在不一会,卢庄和方竟成终于小解归来,让他的这场孤独心旅戛然而止。
可本还一路欢笑的二人进屋后见霍雨桐不知去向,卢庄当即瞠目愕然。
“雨桐她人呢?”
“她走了...”重伤后的洛景枫了无生趣地回答着。
“走了?怎么突然就走了?她说什么了么?”卢庄不明就里,自然想要问个清楚。
“别问我...女人心海底针,我这么蠢,怎么可能猜得出来呢...”洛景枫依旧意志消沉。
这算哪门子的回答,看来他二人当真有事,早知如此就不该留他俩单独一起,卢庄不禁暗暗后悔。
可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竟好像有血海深仇一般...
紧接着,卢庄放心不下走出了陶然居探看雨桐是否走远。
可雨桐真的走了,早已不见了踪影。
没办法,卢庄只得返回了幽南山中。
而这之后,卢庄特意留意起了洛景枫来,见其一脸的落寞颓唐,此刻,卢庄坚信二人的关系绝不简单。
1899年的早春,一连数日的阴雨将广州城浸泡的几欲失去根基,而多日未见阳光的人们心情也似乎被忧郁久久充斥着,可尽管周遭被阴沉笼罩,但顺利于秀江书院毕业的洛景枫却未受影响,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此时,选择去香港官立技术专科学校继续深造的他其实并不清楚未来的自己该何去何从,只是一心想要外出游历闯荡,以解情伤。
其父洛康靖担心其离家太远不便返乡,因而洛景枫才会就近选择香港。将儿女私情暂抛的他最近在香港的这些时日总算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清气爽。
不久后,闲来无事的洛景枫于周末某日看到了一则《中国日报》的招募启示。
洛景枫精于绘画,又擅长写稿,因而他萌生了个念头,决定前去报社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