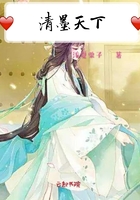今天七月十六是他二人的大婚之日,她怎会不来?
只是才得到消息的她来的有些迟了。
刚刚他就在人群中搜索她的身影,可却寻觅未果,他想着这样也好,没留下落魄的影像,她日后若能想起自己,定还是那翩翩潇洒的俊郎姿态。
哎,可惜呀可惜,她最后还是来了。
而霍雨桐之所以会姗姗来迟,是因卢庄出事后,卢欧下令先不要去惊扰霍家,免得她们心惊胆寒,当时的他对儿子出狱信心满满,觉得婚礼顶多会被延误几天。
可多方打探后发觉此事并非自己想象的那般简单,于是接下来卢欧将心思全部扑在了营救儿子这事上,每日忙的焦头烂额根本无暇他顾,所以霍家那边也就一直没得到消息。
昨日下午得知开堂一事的他直到今早出门敢去府衙前,才一拍脑门想起了今日这婚是结不成了,于是他赶紧派人前去霍家告知实情。
换了新服、画好妆容的霍雨桐静静地端坐于大宅内默默地等候着卢家人的到来。
大红盖头下,一对明月珰轻轻摇晃着,不知为何,她的心竟隐隐掠过了几丝彷徨与落寞。
都说身安不如心安,自己的身明明安好,可心为何却总是幽忧难安...
与女儿不同的是,王芳苓的心情明显要欢喜顺畅许多。
可眼看上午吉时已过卢家的媒人堂倌竟全没露面,霍家母女双双凝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一刻钟过去了,霍家的大门敞开着,竟仍是不见一人前来。
就在王芳苓于空荡荡的大宅中坐立不安,翘首以盼,决定出门打探之时,卢家的下人却匆匆忙忙呼哧带喘着冲了进来。
“霍夫人,今个婚礼取消了,取消了...”
这话一出,母女俩皆感大惑不解。
“出什么事了?好好的婚怎么能说不成就不成呢?”
王芳苓赶紧问那下人话,脸上已是布满了不解不快。
待那人歇了口气后,继续上气不接下气地回话说:“我家少爷他...出事了,我家老爷本以为能把少爷平安救出来,所以一直没有跟霍家讲,可不知怎的,他千方百计也没救出少爷来,待会我家少爷就要被巡抚大人开堂审讯了!”
这一刻,端坐的霍雨桐赶紧取下了头上的红盖头,匆匆冲出后惊愕地问那下人说:“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听了答案后,虽难以置信,可下一秒,霍雨桐一把甩掉了红盖头,摘下了头戴的凤冠,飞也似地朝外跑去。
一路上,她拖着略长的红裙向前狂奔,好几次都险些被脚下瞧不见的东西给绊倒,好在那下人一直跟在近旁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待她和那下人赶至府衙后,刚挤进人群的一瞬,已是筋疲力竭的霍雨桐便瞧见卢庄正被衙役带了下去。
“卢庄!卢庄!等等我...”
她百感交集地呼唤着对方,只盼他能看她一眼,或是跟她说上几句话。
明明好好的婚礼怎地就成了诀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她那本就千疮百孔的一颗心再一次血流不止。
而那个他心爱的姑娘今日本该成为自己的新娘。
可惜等不了了...
等不了了...
哎,就让这场本就有些牵强的婚礼潦草地结束吧,结束吧。
既然选择了革命,选择了牺牲,那情爱本就应是虚妄,自己只能将绝情和残酷留给身后这些人了。
“雨桐,对不起,让你失望了...不用记得我...若能再遇上称心的人...你就嫁给他...好好...活着...”
话音刚一出口,那停下的脚步在他再次痛下决心后猝然决绝地拖着沉重的脚链远去了。
他没有回头,始终没有回头。
可所有人看不到的背后却是一张赤红的,痛苦的,泪迸堤决,几近扭曲的面庞...
霍雨桐呆立堂外只感迷茫费解又无助无措,接二连三的打击早已将她的心拧碎,好似被屠戮的城池,满目疮痍。
她耳上挂的一对明月珰在周遭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竟是那般的招摇,那般的讽刺。
艳丽红装下的瘦弱身躯只感飘忽无依,好似一片离枝的枯叶被狂风卷起,抛下,再卷起,再抛下...
命运的无情戏嘲消耗掉了她全部的气力,这一刻,她已经没有勇气呼喊,更没有力气伸出手来去拼凑自己那支离破碎的残骸...
被押回牢中的卢庄转而又被谭浩麟下令以严刑逼供之法逼迫其供出同党。
煞费苦心的清吏们对卢庄施以了拔手足指甲、火铁烫烙等惨绝人寰的酷刑。
从小锦衣玉食,几乎没吃过苦头的卢庄忍着剧痛,仍咬紧牙关坚持着信念,任凭敌人多么凶狠毒辣,自始至终,卢庄竟都没有动摇。
此时此刻,卢庄惊奇地发觉自己原来可以这般顽强,他真想不到那个在旁人眼中和煦温厚的自己竟有着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范。
死牢内,冷静沉着,铁骨铮铮的卢庄自始至终傲视清吏,牙关未启,没有出卖一个同志。
蒋寿、谭浩麟等人见无计可施,只得在七月二十日这天将他杀害。
那一日,闪电飞光,雷声轰鸣,暴雨倾盆,仿佛云在哭泣,风在哀嚎,天地万物都在为这个年仅二十岁的生命逝去而怆然感伤。
很快,卢庄就义的消息传遍了广州城的大街小巷,革命党人痛心疾首的同时,皆深感其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难能可贵。
远在重洋之外的兴中会领袖孙逸仙更是称赞卢庄为“面貌似玉、筋骨如铁、心地光明若雪”的革命英豪。
几日后,逃至香港的洛景枫也知晓了这一噩耗。
这消息是冯少白偷渡回港后亲口告知他的,他惊愕地拿起了项荫南传来的电报后,顿觉五内焚灼,肝胆崩裂,直接栽在了地面上。
待清醒后,他痛苦不已地堆萎在座椅上,翕动着唇角,似是在自言自语:“卢庄选择牺牲是为了保护会众,保护我们几人,可点燃炸药的人是我...我洛景枫安然无恙地逃到了香港,却害的卢庄白白搭上了一条命...”
这一刻,他凄厉的哭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生命,没多久,日报社成了泪海,压抑的情绪四溢。
洛景枫只感自己是个千古罪人,他好恨,亦好悔...
恨的是自己没有一击炸死蒋寿,悔的是自己不该仓促离开广州,也许那样卢庄就不会枉死,而死的本就应是自己。
“为什么死的是他?不是我?”
大恸的洛景枫哭的昏天黑天,几日几夜都消沉颓靡,完全走不出卢庄已逝的阴影。
他总觉得卢庄的死与自己有关,是自己的失误才害得对方命丧黄泉,因而他精神恍惚,好似将死的病患。
冯少白见此,作为其良师益友只能从旁劝慰开导:“景枫,你应该明白,要革命,就一定会有人牺牲,这回牺牲的不是卢庄,也会是其他的同志。卢庄看起来文质彬彬,但骨子里却坚强如铁,他是个伟大的勇士,他的精神会一直照耀着我们革命党人奋力前行,如果人人都像他这般视死如归,革命何愁不会有成功的一天!”
的确,革命不是儿戏,不是空想空谈,而是改革弊制,推翻腐朽统治,重建新的秩序,所以要革命就一定会有人牺牲,不是卢庄,不是他自己,也一定会有其他的同志。
少白的谆谆教诲令洛景枫清醒了许多,可若要彻底重振,怕是还需要些时日。
卢庄蒙难的几日后,总督府内,正襟危坐的蒋寿一脸阴鸷地浏览着桌面上的出入记录簿,此刻,他的护卫匆匆而入,在他的耳畔轻声嘀咕了几句,忽然,他眼角冷冷一抖,鼻翼两侧的沟壑塌陷地愈发残忍,杀气旋即满面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