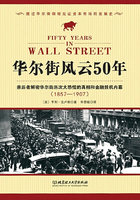中国的土地制度最早实行的公有制,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如果将井田制看作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延续形态,则在西周结束前,中国的土地制度都是实行的公有制形式,其持续的时间有一千五百多年,实际上与土地私有制持续的时间大体相当。有人认为井田制是一种私有制形式,原因是这种田制的经营单位是家庭,而家庭是私有制的细胞或元点。但井田制并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原因有三点:其一,井田制下土地分配实行的是计口授田原则。《汉书·食货志》称:“民,年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这说明,当时的授田是以是否具有成员权和劳动能力为依据的。其中关于无劳动能力人员的供养规定,正是体现了公有制的集体福利制度。其二,土地分配过程中实行严格的公平原则,何休在《公羊解诂》中提道:“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的土地分配原则,体现了公社成员的平等权利,这也是公有制的鲜明特征。其三,井田制下土地不得私相授受和买卖,“田里不鬻”是为维护井田制的公有制性质而制定的严格规定。实际上,井田制被彻底破坏,正是由于《汉书·食货志》所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所以,从土地权利的获得与保障等规定来看,井田制无论如何不能看作一种土地私有制形式。但井田制已经不是纯粹的农村公社时代的土地公有制形式了,在井田制具有典型性的西周时代,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已经私有化了,即周天子宣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拥有全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并在家天下的分封制下,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被层层分解给各级诸侯、官吏,最后由农户耕种。虽然在土地形制上仍然采取井田制形式,在土地分配上仍然贯彻公有原则,但农户助力公田的性质已经由生产公共产品变为向领主提供私人劳役,以供其享用了。助力公田性质向私有化转变,使劳动者耕种公田的积极性下降,如《吕氏春秋·审分览》所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公田的生产荒废了。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农村家庭逐渐具备了对土地的独立经营能力,对协同劳动的需求极大的降低了,因而脱离公社,独自开垦私地并独立经营的情形开始盛行起来。农户将全部精力投入在私地的生产,对助耕公田则完全丧失积极性,不肯尽力于公田,造成“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公田荒芜景象。《汉书·食货志》概括整个春秋时代的情况是“上下相诈、公田不治”。可见,以公有制形制来保障私有制权益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或者换句话说,在私有制前提下,维持公有制形制有着天然的局限和困难。其改革的出路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统治者放弃对土地的所有权,以纯粹公仆的姿态参与管理,完全恢复农村公社时代的土地公有制;另一种是统治者承认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实际占有权,并将自己的所有权收益与土地使用者的实际收益联系起来,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土地制度的私有化。很显然,由私有制退回到公有制并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甚至也不符合普通百姓的利益,所剩的唯一办法就是土地私有化了。而春秋时期各国土地变法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废除公田与私田之分,一律按土地面积征税的举措,这表明,土地制度私有化的序幕正式拉开了,到秦商鞅变法后,不仅“废井田,开阡陌”,而且对土地“民得卖买”,到秦始皇宣布“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制就完全确立起来。
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逻辑在于对公有制固有弊端的否定,即纠正公有制下不可避免的“搭便车”现象对土地经营效率的消极影响。确立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并对其所有权加以保护,其目的是要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这是土地私有制确立的出发点,是土地私有制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是与中国土地制度元点的家庭经营形式重合的。此时,在家庭经营中,土地就不单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资料,而且具有了排他性质,私有土地的产出可以被私人占有和支配,这是农户家庭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最终目的,拥有土地和拥有土地的产出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因此,在这里,以提高土地经营效率为目的的土地私有制逻辑发生了转换,土地私有制的效率优先的逻辑异化为追求和占有更多土地财富的逻辑。在土地私有制下,在家庭核算单位中,财富的增加可以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现有土地的产出率;二是增加土地拥有数量,因为更多的土地意味着更多的产出。但提高土地产出意味着更多的劳动投入,这必然受制于家庭规模,财富增加必然是艰辛、漫长和有限的。土地可以买卖以后,为个体增加土地拥有量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土地兼并就成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一种常态化行为,土地私有制的逻辑因此最终转化为土地兼并的逻辑,它无法避免,也无法禁止。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都会发生土地兼并高潮的根本原因。
土地兼并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必然是一方所失。土地对于农民来讲是维持生计的根本,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已经到了破产的境地,农民是不会将其出卖的。因此,土地兼并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逼迫农民破产的过程。导致农民破产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反复无常、贪得无厌的税赋负担。如两汉时代,农民为逃避政府赋税,纷纷将土地投献于权贵豪强,以求荫庇,这就助长了权贵豪强的土地兼并。平等交换的土地买卖在土地兼并过程中虽然存在,但只是个别的行为,不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形式。权贵豪强为了满足其对土地的无限渴求,其兼并土地的手段不会限于购买,对自耕农土地的强取豪夺是土地兼并极其重要的手段,往往伴随着暴力和血腥,土地兼并史实际上就是自耕农破产的血泪史。
土地兼并的产生,在一些人看来是人地关系紧张的结果。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人地关系不太紧张的封建社会早期,如两汉时期,土地兼并也经常发生,而且会在兼并土地的过程中将劳动力一起兼并,这些劳动力就成为东汉地主庄园的依附民,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封建农奴。这种连人带地的兼并方式显然不是人地关系紧张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在劳动力要素稀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时的土地兼并需要以超经济强制来加以保障,因而这种土地兼并必然不是具有平等契约精神的买卖关系,自耕农在失去自己财富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这种兼并被看作非市场化的行为,对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没有多大帮助,因而是一种不良的制度。这也就说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逻辑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逻辑,这个逻辑最终会将是土地财富增值的条件(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也一并纳入土地兼并之中。在封建社会后期,在人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土地兼并的市场化因素反而增加了,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反而降低了,地主不再需要兼并土地上的劳动力,而是听凭农民竞佃,将土地租给愿意出更高佃租的农民,这当然会使土地使用权最终由具有更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农民拥有,土地私有制的逻辑似乎又回到了效率的主线上来了。但这种契约租佃制与庄园农奴制比起来,甚至更为残忍。因为,在所谓平等契约关系掩盖下,存在着事实上土地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农民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是更大部分的土地产出被地主占有。同时,农民竞佃的失败则意味着完全的生存危机。在明清时代,永佃制的盛行和押租制的扩大,是土地私有制逻辑支配下衍生出的新的土地经营形式,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土地兼并或土地所有权频繁变动对佃农从事农业生产的影响,有利于鼓励佃农持续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的基本逻辑,甚至更为残酷。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货币化,意味着农民要获得佃种土地的权利就必须要有预付资本,对于那些赤贫的农户来讲,除了饿死,没有其他办法。
因此,当土地私有制的逻辑演变为土地兼并的逻辑后,作为中国土地制度基本单元的农户家庭经营形式就必然具有了不稳定性,小农经济的解体必然导致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构。一般来讲,经历社会动荡后,中国土地制度会回到元点,家庭经营的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得以重新建立,然后在土地私有制逻辑支配下,又会重演封建土地私有制从重生到毁灭的周期性循环。这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演变的主要特点,是土地私有制逻辑支配下的必然结果。
总之,土地制度私有化的逻辑不是一个纯粹以效率为中心和主线的逻辑,它必然演化为土地兼并的逻辑,成为经济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今天,一些人提出的农村承包地应该确权到户,并加以固化和长久不变,允许自由流转的观点,实际上仍然重复的是秦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民得卖买”的土地私有制确立办法,其主张的效率优先逻辑仍然逃脱不了被异化为土地兼并逻辑的规律,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第三节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中的公有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