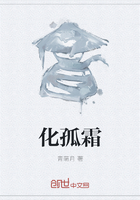北六息多了一位伤友,被申不时搀扶着躺到旁边,正是松浦隆信。
北六息此前没有见过他,但也能猜一二,明显能看出他是为剑气所震,受了内伤,伤在谁手,不言自明。
“看来申兄的皇图霸业要成泡影了。”他打趣道。
“也许吧,没想到林寻舟如此之强。”
“还没结束!”松浦隆信突然睁眼,“休息数日,我可再战!”话音未落,又一阵剧咳,吐血不止。
申不时连忙拿来银针为他扎穴。
“申兄还会医术?”北六息惊讶不已,要是他看到申不时弯弓搭箭想必会更加震惊。
申不时笑笑,“为了造反,我可是做了充足准备的。”
北六息不住咋舌,又忽然想起来什么,忙问,“那个女子呢?”
“已经杀了。”
“噢……蛮可惜的。”
“只有弱者才需要她们。”松浦隆信冷冷道,“真正的武士,向来是独自一人,一个人杀敌,一个人疗伤,一个人饮酒,一个人去死。”
“这就是所谓武士么?”北六息轻笑,转而问申不时,“申兄已经见识过林寻舟的武功了吧,现在有什么打算?”
“哪有什么打算,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那林寻舟?”
“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打败林寻舟,只要拖住他就行了,一旦我们拿下应天,他还能以一人之力抗一城么?”
“拖住?说得轻巧。”北六息眼神轻蔑,在与林寻舟交手之后他彻底抛下了往日的傲慢,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平凡。
“刀剑当然是拖不住的,那就只好用言语拖住了。”
“他会听你废话?”
“大概不会,不过会听其他人废话。”
台州城内,号令声不绝于耳,城南一块废弃的民房直接被推平,用作演武场,戚继光所招新兵,皆在此训练。依照号令,数人一组,手持各类兵器,进退有度,喊杀震天,气势如虹。
林寻舟翘着腿坐在一堵矮墙上,饶有兴趣地看着士兵操练。
“大哥哥!”身后传来奶声奶气的声音。
林寻舟回过头来,后面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眼睛一眨一眨的。
林寻舟也朝他眨眨眼,“干嘛?”
“这个给你。”小孩拿出背后的篮子,里面装着几个小饼,“奶奶做的,希望你能早点赶跑倭寇。”
林寻舟愣了一下,接过篮子,把小孩也抱到墙上坐着,拿了一块小饼,也给小孩拿了一块。
有点硬,不过很好吃。
“赶跑倭寇不是靠我。”林寻舟指了指操场,“是靠那些勇敢的人。”
孩子伸手擦了擦嘴,“但是他们没有你厉害啊,大家说你能呼地一下从城墙上跳下来。”说着他也从矮墙上跳了下去,“就像这样。”
林寻舟哈哈一笑,再把他抱上来,很认真地对他说,“任何时候,一个人的力量都是很渺小的,你只看到了我威风,其实倭寇随时会卷土重来,只有军队,才能彻底驱逐倭寇。”
“听得懂吗?”林寻舟问他。
小孩摇摇头。
“那就玩去吧。”林寻舟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好,哥哥再见。”小孩跳下墙就欢快地跑开了。
号令声暂时停止,新兵们得以歇息一会,军官们也趁机喝口水,湿润下干燥的嗓子。
戚继光大步流星向林寻舟走开,甲胄声声作响。
“将军操练还穿着铠甲呢。”
“操练亦是兵事,岂容马虎?”
林寻舟递了一个饼过去,被戚继光谢绝了,“先生看这新军如何?”
“虎狼之师,大抵如此吧。”
戚继光一阵大笑,用力拍了拍林寻舟的肩膀,指着操场,“先生请看,我以十一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后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分挡左右倭寇突刺,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用南方毛竹,削成尖状,留四周尖锐的枝丫,用以刺杀敌人和掩护推进,再是四名长枪手,左右各二人,照应前面两边队友,最后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负责警戒,支援。倭寇进攻,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退却,则由长枪突刺。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需要熟悉自己的操作,只要相互配合,令行禁止,即可无往而不利。”
忽而戚继光又怅然道:“此乃某在山东所设想的阵法,起初只是为了快速训练新兵,没想到会在东南用上,虽然小有成色,但倭寇凶狠,真不知能否取胜。”
“会赢的。”林寻舟肯定道,“不但会赢,还是大破倭寇。”
“那借先生吉言。”
“将军此阵可有名字?”
“这……草创之初,也取过几个,只是都不如意罢了。”
“比阵左右相对,形似鸳鸯并行,不如就叫鸳鸯阵。”
“鸳鸯阵。”戚继光叨念了几遍,越发高兴,“好好!就叫鸳鸯阵!”
当晚,李让买来饭菜和顾少言一起吃。偌大的杨府,只有大堂亮着烛灯,显得颇为冷清。
长久的沉默,只余碗筷碰撞之声。
“那个……”李让忽然出声,“有个问题一直想问。”
“什么?”顾少言夹了一把菜。
“你那时为什么要回京城呢?”
“不是说了吗?父母给我在朝廷安排了职位。”顾少言头也不抬地回道。
“我是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顾少言扒饭的手停住了,放下碗筷,抬起头看他,“你想说什么?”
“你那时候走,会让人误解的。”
“我不得不走,那是我父母的命令。”顾少言幽幽道,“自幼他们就给我安排好了一切,习武,识文,甚至我交的朋友也是他们安排好的——为了家族间的交往。直到来了书院,才略得喘息,可我身上已经打上了他们的烙印,洗刷不掉了。他们要我回去,我怎么能反抗呢?”
“你该和我们说一声的。”李让遗憾道。
可顾少言忽然笑了,“你们?是指哪些人?林寻舟那时已经失去理智了,我和他说我要回京城他可能会当场拔剑杀了我,我只能悄悄离开。”
“我早就说过,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不仅仅是指地位,还包括对人事的看法——我在乎的你们不在乎,你们在乎的我不在乎,分歧就是这么来的。”
“这么说你是不在乎小师叔了!”李让盯着他的眼睛,不让他有分毫躲闪。
顾少言也根本没有躲闪,他只是沉默良久,然后轻声道:“说不清。”
啪!似乎是什么东西折断的声音。
李让茫然向夜色中看去,刚刚出口,“什么声音?”
顾少言一把将他踹倒,呼地吹灭了桌上蜡烛,一脚蹬在桌上,借力划向墙边,“别动!刺客!”
那是木箭折在墙上的声音,看来刺客是从屋顶而来。
屋顶还有许多陷阱,但除了第一声之外再无声音,刺客大约是没有料到会有陷阱,中了一招,而后便精准地绕过一个个陷阱。
实力可见一斑。
顾少言屏住呼吸,贴着墙角无声移动,悄悄取下绣春刀,握紧刀柄,但他不能立刻拔刀,刀光会暴露他的位置。
他转头看向李让的位置,那里远离窗边,不在月光之下,吹灭蜡烛便一片漆黑,人影被黑暗笼罩,完全看不出轮廓,只要李让不动,刺客应该不会首先发现他。
李让也确实一动不动,虽说他从没见过大内高手而有些无所畏惧,但如今的阵势也吓到他了,他很想问问顾少言有没有他能帮上的忙,又想了想还是安心闭嘴的好,便缩在墙角一动不动。
四下寂静,就连风呼虫鸣都消失不见。
顾少言摸回桌边,夹起一支筷子,倏地打向门框。
当!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显得格外刺耳。
夜色中却毫无动静,仿佛并没有什么凶神恶煞躲在暗处。
“没事吧?”李让小声问道。
呼!话音未落,他就感到一阵劲风直扑面庞,仿佛要将他割接开一般。
那其实有两道劲风,一道是刺客的匕首掠下,一道是顾少言投出绣春刀。
一把匕首,离他的眼眶只有两寸距离停住,被钉在墙上的绣春刀所挡。
“跑!”顾少言大喊一声,同时起身冲过来。
划拉——刺客掠空而出,再次消失不见。
顾少言双手握刀,双脚随时准备发力,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他把李让护在墙边,后者倒没受什么伤,只是生死一线,惶恐不已。
砰的一声,墙壁裂开,刺客居然从墙后出手,直接洞穿了墙壁,匕首更是撇开了后面的李让,直冲顾少言的后颈而去。
大惊之下顾少言侧身肘击,他下意识地将攻击者当成了站在自己身后的人,这一肘直接打在李让身上,重重的一肘,李让闷哼一声,踉跄着跌坐在地上。
无暇道歉,顾少言全力一刀劈开墙壁,墙后黑影一闪而逝,顾少言立马跟了出去,略一扫视,便翻身上了屋顶。
刺客站在房顶,毫无躲藏之意,顾少言这才看清刺客——身穿夜行服,手提匕首,腰间无物,手无护腕,一双眼眸冰冷地盯着顾少言。
这无疑是真正的高手,除了一把匕首再无他物,唯有对自己的武功自信到极致的刺客才有这样的胆量,否则,既是对雇主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性命的不负责。
很少有人知道大内高手的存在,他们是皇宫中的影子,这些人自幼生长在皇宫,由天子钦定的老师教导,经过极为残忍的训练,十八门武艺样样精通,暗杀潜入无所不能。锦衣卫虽然直属天子,但他们是有明确组织的“亲军”,大内高手则是彼此独立的“高手”,相互之间并不见面,所有人只听从于皇帝或者他们的首领。
顾少言执掌锦衣卫,对大内高手早有耳闻,但这还是他第一次真的见到这些神秘的高手,虽然锦衣卫中也有不少人自幼习武,但两者间的气势绝然不同。
刺客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很难让人想象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训练。
自从离开书院之后顾少言就再没有勤奋练武,他虽然是锦衣卫指挥使,可更多的时候都是坐在案头处理公文。两次遇袭,不过都是凭着过去的底子应付罢了,否则他也没必要修筑陷阱。
如今大内高手在前,他怎敢妄言退敌,只好稳住阵脚,看刺客如何出手,见招拆招了。
相持数息,见顾少言毫无动静,刺客高高跃起,借夜色掩护身影,顾少言本想听声辨位,竟然除了风声之外再无杂音。
再出现时,刺客已在顾少言身后,手中匕首无声捅向顾少言的后心,直到数寸之间,顾少言才反应过来,附身负刀,以刀面挡住匕首,刺客作势划向后颈,身形却鬼魅般地闪到侧面,一记重腿将顾少言踢飞出去。
哗啦哗啦……瓦砾一片片被掀起,接连从屋顶落下,顾少言被这一脚踹得飞出一丈之远,顺着屋顶滑下,眼看就要摔下屋顶,顾少言猛地起身,握紧刀柄插下,这才勉强在屋顶边缘停住,抬头一看,刺客居然站在原地,没有趁势下手。
这是……蔑视吗?
未等顾少言想明,胸口就再中了一脚,砰——闷声之下,顾少言从房顶上倒飞下来,吐血不止。他明明是正对刺客的,却根本来不及挡住这一脚。
太快!
当啷。
绣春刀落在顾少言的手边,他却没有力气去捡——此刻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口中尽是血水,恍惚中,好像看见刺客站在屋顶俯瞰自己,他没能看清眼神,但还是能体会到那种冰冷。
李让捂着胸口从堂中窜出,捡起地上的绣春刀,对准了房顶的刺客。
顾少言想让他走,刚一开口就被血水呛住,一边咳嗽一边拼命喘息,用眼神示意李让快走。
李让看不见——他背对着顾少言,死死地盯着那人,意思很明确——我们不会逃,但也不会乖乖受死。
当当当。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李让和顾少言忽然间感觉不到那种冰冷了,秋末的凉风虫鸣又回来了。
再抬头,哪里还有刺客身影。
好似黄粱一梦——然彼此身上的剧痛却明白地显示着这是真的。
敲门声还在继续。
顾少言挣扎着坐起来,和李让对视一眼——无论门外是谁,现在都能轻易杀掉他们二人。
不过既然愿意敲门,总归不是坏人吧?
李让一摇一晃地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队兵士。
为首的伍长看了看李让,说道:“我们是胡宗宪大人的部下,大人听闻最近有飞贼出没,特派我等来此巡视,你们没事吧?”
李让不知如何回答,回头看了一眼顾少言,伍长也探了探头,看见顾少言满脸是血,吃了一惊,但什么都没有问,只是说“你们没事就行,我们就在附近驻守,有事高呼即可。”说着便退了出去,李让跟在身后连连道谢。
“咳……哇!”顾少言又吐出一大口血,李让连忙关了门跑来,紧张地问道:“你没事吧?”
“应该还死不了。”顾少言已经口齿不清了,说话的同时还有血从嘴角流下来,被他用手擦掉。
“那就是大内高手?”
顾少言点点头,把嘴里的血吐干净了,说道,“我还还在书院的时候能和他打,现在只能靠林寻舟了。”
“可林寻舟在台州啊。”
“所以,我们不能再住这里了。”
李让却愣住了,脸色又很快变得坚毅起来,他把顾少言扶起,“你走吧,我留下来!”
“回头再来给你收尸吗?”顾少言气极反笑,“那就呆在这好了,总归还有胡宗宪的人在。”
李让望向房顶,“那人是因为这个才走的?”
“明显是的,钱芳肯定知道了一切,但不能悄悄地杀掉我们,他就会很麻烦,尤其是现在胡宗宪已经知道了此事,就更要小心。”
“对对!胡大人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李让如梦初醒,此前他一直处在惊慌的状态没有恢复,“那我们怎么办?”
“明天去找胡宗宪啊,问问什么意思。”
“那现在呢?”李让愣愣地问道。
“现在扶我起来去疗伤!”顾少言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