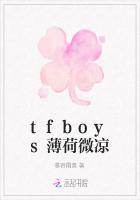他们扭住了我和瓜娃,我和瓜娃拼命挣扎,芹菜这个时候突然像疯了一样扑过来,帮着我和瓜娃,对胡来劈面就是两爪子。女孩子动手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打人用拳头,芹菜用指甲,没看到芹菜怎么动手,胡来和他带来的两个喽啰已经被芹菜给挠花了,脸上满是指痕和血流,连哭带骂地翻身扑过去抓芹菜。
芹菜真是个偶尔露峥嵘的角色,在我的印象中,芹菜一向就是个内向文静的女孩儿,自从她父母被日本人杀害,奶奶收养了她之后,芹菜变得更加沉静甚至忧郁了,即使跟我们伙在一起玩耍,也很少再像过去那样嘻嘻哈哈地笑出声来。同时,跟奶奶练功也是她第一勤苦,瓜娃第二,我属于差等生。今天芹菜却变成了一只疯虎,不,应该说她简直是一只疯狂的野猫,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比她高大强壮,可是她却奋不顾身东抓一把西挠一爪,片刻之间把胡来和他的喽啰们挠了个人仰马翻。这个时候,芹菜平常苦练的功夫就发挥了作用,尽管奶奶教她的主要是那种用来逃跑的“清风步”,可是,芹菜现在用清风步不是逃跑,而是躲闪,她并不跑开,就是那么东躲西闪地在胡来跟他的喽啰中间穿梭、翻飞,胡来和他的喽啰们疯了一样捕捉她,却连她的衣襟都沾不上,反而被她东一爪西一掌挠得一个个都成了戏台上的三花脸。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脑子里闪现出来的念头竟然是,芹菜现在好像不太咬东西、咬人了,原来她改成挠人了。胡来跟他的喽啰们全力对付芹菜,反倒把我和瓜娃晾在了一旁,我招呼瓜娃:“上啊,打啊。”瓜娃这才反应过来,扑上去加入了战团。我是连踢带打,打谁方便就朝谁身上招呼,拳头就像炮弹一样朝他们身上、脸上、脑袋上轰击。瓜娃是抱住谁谁倒霉,他逮着一个就死死抱住不放,连啃带咬带抓挠,凡是被他逮着的没有一个不发出杀猪一样的哭号声。
胡球来看到我们打成一团,在一旁着急得挥舞着手枪,枪口一会儿对着这边一会儿对着那边,却无论如何没有开枪的机会:“胡来,你们让开,你们让开,我灭了这几个小贼。”
我看到瓜娃正抱着胡来啃得香甜,连忙提示他:“瓜娃,抢胡球来的枪去,把胡来放了。”
我之所以让瓜娃出面抢枪,是因为瓜娃跟着奶奶练功比我刻苦扎实,我觉得他出面抢枪手脚肯定比我利索,说实话,奶奶教得都是机巧功夫,瓜娃这样抱着人家死啃,浪费工夫,样子很难看,说出去也太丢人。
瓜娃听到我嚷嚷,松开了胡来,胡来捂着脑袋痛苦不堪,也不知道是脑袋被瓜娃啃烂了还是脸被芹菜挠破了,满脸污血,瓜娃松手,他顿时轻松,蹲到地上连哭带骂:“你奶奶的熊啊胡球来,狗日的开枪,快开枪啊,把狗日的小贼都灭了。”
瓜娃扔下胡来,按照我的命令朝胡球来冲了过去,大概是出于本能,他对胡球来用上了奶奶让他苦练不辍的“蹬云腿”,蹬云腿就是全身发力,朝墙壁或者垂直的陡坡飞奔,到了墙壁或者陡坡跟前,改变发力方向,利用奔跑的速度加上由前冲改为上提的力道,一举飙升到墙壁或者陡坡顶端。这有点像飞机从跑道上起飞,是练习轻身功夫的基本功,功力越浅需要的跑道越长,功力越深需要的跑道就越短。奶奶练成了,要攀爬到房顶上,用不着跑道,几乎原地拔起就能够到房梁上。
瓜娃子脑子僵化,别的功夫还没有练过,就死练这一套,用起来也只会这一套,听到我让他抢胡球来的枪,便把胡球来当成了墙壁、陡坡,发力朝他猛跑过去,还没等胡球来明白过来,瓜娃的脚已经踩踏到了他的身上。那么大的冲劲儿,胡球来又没有防备,也说不清是被瓜娃子给踹倒的还是撞倒的,立刻摔了个大仰壳,活像一堵土墙倒塌下来,扑通一声巨响,青砖铺就的街面都震动了几下。瓜娃练就的蹬云腿目的是攀高,并不是踹人,胡球来倒了,他还顺势上升了将近一丈高,才落到地上。胡球来倒地的瞬间,枪从手里摔了出来,瓜娃落地恰好踩在枪上,顺势弯腰捡了起来。
“给你,开枪打。”瓜娃真够意思,捡到枪并没有据为己有,跑过来递给了我。
说来也怪,手里有了枪,人顿时也有了精神,有了胆量,反过来,靠着枪耀武扬威的人,没有了枪顿时就变成了稀屎软蛋,胡球来从地上刚刚要爬起来,看见枪到了我的手里,顿时定格,活像一条大鳄鱼翘起脑袋瞠目结舌地看着比他更大的猛兽,胡来和他的喽啰们更是一哄而散,跑到远处躲在墙角里当起了旁观者。
我吩咐芹菜和瓜娃:“你们两个快跑,我断后。”
芹菜和瓜娃茫然地站着,芹菜问我:“朝哪里跑呢?”
我这才想起,那个王先声他们的老窝芹菜和瓜娃并不知道,我还得带路。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奉奶奶之命到周承甫他们的老窝打冒,但是瓜娃和芹菜并不知道打冒的盘子就是王先声他们的老窝,只有我知道。
我用枪对着胡球来吓唬他:“狗日的汉奸,敢跟我们来,我就开枪灭了你,把你种到地里去。”
胡球来连连摆手,嘴大张着却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朝后面偎蹭,我也不再管他,估计他也没有那个胆敢跟着我们,便带着瓜娃和芹菜朝王先声他们的那条街猛跑。
功夫是练出来的,功夫高低是比出来的,跟着瓜娃和芹菜这么一跑,人家两个人的功夫立刻把我比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跑得太快了,而且一点也显不出正在奔跑,看着好像在走路,可是速度却是我连跑带蹦也难以追上的。跑一会儿,他们发现我没了,回头看看,我还在后面挣命,只好站下来等我,瓜娃还一个劲儿催促:“你快些,小心胡球来他们撵上来。”
我苦笑,暗想,连我都追不上你们,别说胡球来父子俩那两个蠢猪狗熊了。我领着他们穿街走巷,找到了王先声他们的住所,从外面看,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民宅,无论是院墙还是大门,都跟那条街上别的院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青砖砌就的门楼下面有三级台阶,台阶的上面,朱红的木门紧闭,我猛敲一阵,里面却声息全无,难道他们都跑了?如果这里没人,只剩下一座空宅,我们该到哪里去呢?瓜娃和芹菜围了过来,我心里的问题,他们俩异口同声地问了出来:“没人咋办呢?”
奶奶吩咐我们找王先声他们,然后要求他们将我们送出城,到山里去找我爹他们。然而,奶奶却没说如果王先声的老窝没有人该怎么办。这些日子日本人天天大搜查,街面上冷冷清清基本上没有人,我们三个人站在门口非常显眼,别说别人看着怪异,就连我们自己都忐忑不安。
“管他有没有人,先进去躲起来再说。”这是我眼下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绕到旁边吧,这里太显眼了。”女孩子心细,芹菜提醒。
我们就沿着旁边的小巷子转到了这所院子的侧面,我对他们俩说:“就从这里翻墙进去。”
话音刚落,瓜娃迫不及待地腾身上跃,脚在墙面上蹭了几下,人就已经坐到了墙头上。芹菜也没啥问题,跳跃着接住了瓜娃的手,瓜娃稍微使力,芹菜顺势就上了墙。剩下我就比较麻烦,平时不用功,用时烂稀松,这话说的就是我。我跳了几次也够不到瓜娃伸出来的手,芹菜着急了,让瓜娃下来我一把,瓜娃又从墙上跳下来,蹲到地上:“你踩到我的肩膀上。”
我踩到他的肩膀上,瓜娃站立起来,我还是够不到墙头,芹菜将脚丫子垂下来:“拽我的脚。”我只好拽着芹菜的脚,借力使力,总算爬上了墙头。虽然爬上了墙头,我却也脸面丢尽,暗叫惭愧,不敢看芹菜的眼睛。瓜娃的功夫的确练得到家,稍微退后几步,发力奔跑几步,很轻易就蹿上了墙头。
上墙难下墙易,我领先跳了下去,瓜娃和芹菜也先后跳了下来。刚刚从墙上跳下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三四个汉子,每个人手里都端着枪,每个人的枪口都瞄准了我们,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儿,我估计他们看到我们是三个孩子,否则肯定会不搭腔先开枪毙了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
“狗日的还跳墙呢,干什么的?”其中一人喝问。
我刚要答话,猛然间想到,万一这些人是汉奸队的,我说找王先声那就麻烦大了,就现编了一个谎:“我们想进来看看有没有吃的,我们敲门了,你们不开么。”
他们相信了,主要还是我们三个娃娃的模样儿糊弄住了他们,无意中,他也漏出来一句真话:“狗日的敲门对不上暗号,谁能给你开?这里没吃的,赶紧滚。”
我这才明白,到他们这里敲门,还得有暗号,没有暗号敲门,他们明明有人也不会开。在他们的枪口逼迫下,我们转身朝外面走,他们中间一个眼尖的却发现了我插在腰里的王八盒子:“站下,你腰里藏的啥?”说着,抢上一步撩起我的衣襟,看到枪便一把将我的枪给收了,“嘿,还是日本货呢。”
其他几个人马上警惕百倍地围定了我们,收我枪的人追问:“老实说,你们是干啥的?不老实就地枪毙。”
我的枪被收了,我这才想起注意看看他们的枪,他们一共四个人,两个人手里的枪我很熟悉,正是那种叫勃朗宁的,还有两个握的是匣子枪,除了从我这儿搜去的王八盒子,他们拿的都不是日本枪。看明白这一点,我脑子里忽悠闪了一闪:这些人肯定不会是日本人那一伙的!
“我们是来找王先声的,对了他有两个伙计,一个叫周承甫,一个叫李云君。”我决定蒙一把。领头的就是那个搜我枪的,我这会儿从他说话的口气、旁人对他的态度诸方面已经得出了这个判断。
果然,那几个人犹豫不决了,相互看看,然后领头的那个人说:“管你们是干啥的,既然来了就不能走了。”
瓜娃却反问人家:“刚才你们不是叫我们滚么?”
领头的说:“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然后摆摆手,对其他三个人吩咐,“先关起来。”其他几个人正要带我们走,他却又想起来问了一句,“你们到底是干啥的?”
瓜娃和芹菜茫然,他们确实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他们都是被蒙在葫芦里,什么也不知道。
我回答:“我们是洪家班子的,你给你们王先声一说他就知道。”
我错了,不但他们王先声知道洪家班子,这几个家伙显然也知道,领头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胡说吧,你们是洪家班子的?就你们三个半大人儿?”
我拿捏不住,到底应不应该给他们这几个显然是小喽啰的家伙说奶奶的情形,瓜娃和芹菜更是茫然,他们到现在连洪家班子是什么都不知道。想起奶奶临走时候的吩咐,我连忙说:“赶紧给王先声说,他要的东西我知道,奶奶让我们领他去拿东西,耽搁了可别怪我们。”
听了这话,领头的马上追问:“什么东西?”我说:“不给你说,直接给王先声说,给你说了你就得死呢。”
那人吓坏了,满脸焦急:“这咋弄呢?他不在啊。”
我现在的主要目的还是找个安身之处,听他这么说,我便说:“那就给我们安排好住处,我们在这里等,你们赶紧想办法找他去。”
“好好好,你带他们几个先去歇下,给灶上说做饭待客,我们三个分头去找王组长。”领头的对我们态度大变,不但客气了许多,还立刻安排了我们的食宿。安排完,他们三个人急匆匆就往后院走,我叫住他:“我的枪给我。”
那人却拒绝了:“不成,在这里除了我们外人不能带枪。”
我又说:“你们不赶紧找王先声,朝后面跑啥呢?是不是他在后院藏着呢?”
那人不耐烦了:“事情咋恁多,前门不敢走。”
我们三个被领进了东面的厢房,这个院子我跟奶奶来过两次,我记得上一次跑来走财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对面的西厢房找到的钱和枪。其实瓜娃和芹菜也来过,就是奶奶准备“扒他们的皮”,让我们踩盘子的时候。我们假装在外面玩耍,随时盯着院子里的人的出入情况,那天趁他们都出去的时候我和奶奶晚上潜入到这里“扒了他们的皮”,那一次还因为藏私被奶奶惩罚饿了好几天。瓜娃和芹菜不知道晚上我和奶奶出来走财神的事儿,地方和人对不上号,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王先声”的住处就是我们曾经踩盘子的地方。
东厢房里有一铺大炕,地当腰有一张八仙桌,桌旁放了两把太师椅,八仙桌依靠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堂,上面写着岳飞的《满江红》。
这首词用潇洒的行草写就,有一些字写得太草我们不认识,不过这首词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日本人强迫我们学校学日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叫我们背诵这首诗,背着背着大家就开始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过后不久,我们的老师就被日本人抓去用刺刀给捅死了,我们也就不再去上学了。
这首词挂在这里,令我顿时对这个院子的主人,具体地说就是王先声、周承甫、李云君有了强烈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