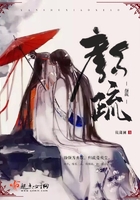我转身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老道的一记拂尘,但是出奇的,今天后脑没有再受到一次重击。我也不知道该说是自己幸运还是不幸,因为我清楚,老道从来就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我的所作所为一定会被他记在心里,然后等到晚上没饭吃的时候再爆发开来。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一记拂尘可以解决的了。但是相较于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更能忍受的还是老道无休无止的絮叨,因为哪怕是一些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抱怨,我也确实明白他是在乎我的。即使有些烦,却真的能给我温暖。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对是错,因为如果老道没有收我这个徒弟,他往日的平静不会被打破,我也仍旧要流落街头,或者回到那个我不想要忍受的家庭。而老道如今也不用在烈日下东奔西走,遭人白眼。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喜欢闲适的生活更多的的人,不然他也不会放弃山下的道观长居于山上。可是如今他因为我而屈心抑志,我却非但不领情,还使他的努力付之东流。我想,如果这样下去,我可能只能被扫地出门吧。但是那样或许也好,经历了父母的事件之后,我已经不希望这个世界上再有任何一个人为我而勉强,如果老道为了我要牺牲那么多,倒不如还他一个宁静的生活。只是那样,我一定会很遗憾的。
想到这里,我整个人就像一条被抽走了骨头的咸鱼,安稳的躺在厢房的木板床上,只是听着拂尘肚子里传来的呼噜声还有偶尔的一声猫叫,我才发现自己对不起的不只是老道,还有拂尘。
出乎意料,老道晚上没有训斥我,只是扔给我两个烧饼,还是温热的。而他自己则一展道袍,背靠在我的床头,又开了瓶小二。我知道,他又有话要说了。
“徒儿,你是不是很看不起师傅。”听到这句话,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而在此刻,装睡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撕着手中的一块烧饼,慢慢悠悠的喂着拂尘。拂尘有了东西吃,也不叫了。于是,冷清的空间里此刻就只剩下老道的声音在回荡。
“其实我也不想站在街头去兜售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而且说实话,就算是祈愿逢考必过,也应该去孔庙上柱香,绝不是在我们这里挂个绘马。可是时代变了啊,大多数人都行色匆匆,没有多少人能够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再去选择修身养性,所以他们宁愿去买个开过光的佛珠,又或者带上基督教的十字架,也不愿意听我们这群臭老道讲风水,不愿意看我们做法事。可是事实上,道门的所有乐舞都是从上古时期的祭祀之乐流传而下。只是,遗忘了这些的不只是世人,还有道门中人。”说到这里,老道的声音有些沙哑了,于是他灌了一口酒。
“的确,我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哪怕是在这里挂了绘马,我也没有法力去帮他们做到逢考必过,也没有途径让他们心想事成。可是只要我还卖的出去一件木牌,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来买我的木牌,不光是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有了寄托,我清风子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到师傅面前说我道门还有传承,这青山观还没有倒。徒儿,我知道你是个追求自由的人,甚至于你骨子里更能操守着安贫乐道,你比我更适合当一个道士。但是徒儿,时代变了啊。想要立足在这红尘之中,我们已经不能和先辈们一样隐世了啊,不做出改变,山门就要倒在我手里了。要是这样,我怎么去见各位老师傅,怎么去给师兄们一个交代……”
师傅说到这里,又是一口小二灌进了喉咙,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些哽咽。他看不到我的表情,但是我自己知道,眼泪已经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可是我不想哭,至少,我不想在安慰老道的时候自己先流下眼泪。
“其实在你上山之前我也收过几个徒弟,但是一个个都不是踏实肯干的人,把道馆传给他们我也不放心,所以上山没几天我就把他们都给踹了。但是你不一样,你要面子,有自尊,重情重义,又有操守,不盲目,所以等到师傅驾鹤西游,你会是继承道观的最好人选,而我也觉得不能再给你找到一个过关的师弟了,所以把道观交给你,师傅也放心。只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行,太过清高的你不会有什么朋友,可是如果你不去接触外界,别人又凭什么来接近你这个濒临灭绝的职业?这样下去,你在这个世界甚至不会有一片立足之地,我没有传你道经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你太执拗,而道经也已经不适合现在了,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大逍遥大自在,你会走得很艰难。做出改变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都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还好,师傅还有些年月,你不想干就不要去干了,但是答应师傅,不要师傅的心血葬送在你的手里。”
说完这些,老道又要举瓶,而这一口下肚,他马上就要吹瓶了,只是我伸手抢了过来,先他一步把小二喝了个精光。看着他有些泛红的脸颊,我尽力做出恶狠狠的表情。
“上次你就抢我的酒喝,这一点留给我又怎么了?”
结果老道眨眨眼直接跳了起来,“放屁,我什么时候抢过你的酒?小小年纪还学我一口闷?你也不嫌辣?”
我知道,这只是老道掩盖自己脆弱的说辞,所以他又开始装疯卖傻,但是这样不就够了吗?一个能好好说说话,一个能安安静静听,这样的交流,已经很难得了。只是两个道士都有些上头,差点因为这瓶酒打了起来,也幸好我的床铺不高,所以老道从床上摔下去的时候也只是昏迷,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故,不然我可能就要提前继承小观了。
第二天清晨,我比老道醒的更早,宿醉让我有些头痛,所以撕掉一半的烧饼塞进了自己嘴里,另一半随意的丢到了老道手中。然后,我把老道搬上了床,自己则打开房门,去清扫分坛的庭院,走过绘马架时,我发现昨天还空空如也的木架上,多了两个在风中摆荡的木牌,各自有两行娟秀的小字。
这一次,我没有再跳脚,也没有鄙夷,我知道,尽管自己的身体还没有迈入红尘,但是我的心,已经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