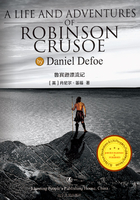陆地上空的云团此时高高地悬着,像一座座山峰。海岸似一条绿色的长带,背后是些蓝灰色的小山丘。海水呈深蓝色,深得简直都发紫了。他低头看海水,见红色的浮游生物在深暗的海水中浮动,太阳在水中映出奇异的光彩。他望望鱼线,看见它们一直没入水中看不见的深处。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因为这说明有鱼可捕了。太阳此刻升得更高了,它在海水中映出奇异的光彩,说明天气晴朗,陆地上空的云团形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那只鸟此时几乎不见了踪影,水面上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摊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黄色马尾藻和一只紧靠着船舷浮动的水母。这只水母那胶质的浮囊是紫色的,外形跟普通的水母一样,此时闪烁着光芒。它歪歪身子,然后又摆正位置,像个大气泡般高高兴兴地漂在水里,那致命的紫色长触须在水中拖在身后,长达一码[21]。
“Agua mala[22],”老人骂了一声,“你这婊子。”
他轻轻摇着桨,从他坐的地方低头朝水中望去,看见一些颜色跟那些拖在水中的触须一样的小鱼,它们在触须与触须之间以及浮囊所投下的一小块阴影中游动着。水母身上的毒素对小鱼没有影响,但对人就不同了。老人捕鱼时,水母的一些触须会缠在鱼线上,触须上带着紫色的黏液——中了毒,他的胳臂和手上就会出现伤痕和肿痛,就像被毒藤或毒栎刺伤了一样。而这种水母的毒素发作得很快,让人痛起来如同身受鞭笞。
那些彩虹色的“大气泡”很漂亮,但它们是大海里最具欺骗性的东西。老人最乐意看的是大海龟把这些水母当美餐吃掉。海龟一旦发现了它们,就从正面向它们进逼,然后海龟会闭上眼睛,全身藏入龟壳作掩护,把水母连同它们的触须一并吃掉。老人喜欢看海龟吃这种水母,也喜欢在风暴过后在海滩上遇到它们,喜欢听自己用长着老茧的硬脚掌踩在它们上面时发出的爆裂声。
他喜欢绿海龟和玳瑁[23]。它们游水姿势优美,速度很快,价值不菲。对于体形庞大、笨头笨脑的食肉巨龟,他有些瞧不起,却也心怀好感。这种龟的龟壳是黄色的,做爱的方式很奇特,而当它们把这些水母当美餐吃时总喜欢闭着眼睛。
他驾船捕杀海龟有些年头了,觉得海龟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他替所有的海龟难过,甚至那些跟小船一样长、重达一吨的大棱皮龟也让他恻然。人们大都对海龟残酷无情,因为把海龟杀死、剖开后,海龟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小时。老人内心在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脏,我的手脚也跟它们的一样。”他吃白色的海龟蛋是为了使自己长力气。他在五月份连着吃了整整一个月,到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就有充足的体力捕捉真正的大鱼了。
他每天还喝上一杯鲨鱼肝油。那只盛肝油的大桶放在许多渔夫存放渔具的棚屋里,不管是哪个渔夫,谁想舀着喝都可以。大多数渔夫讨厌肝油的味道。但再怎么也不会比摸黑起床的滋味差。喝肝油对于预防一些伤风感冒都大有益处,对眼睛也很好。
老人此刻抬眼望去,看见那只鸟又在盘旋了。
“它找到鱼啦。”他大声说。这当儿,并无飞鱼冲出海面,也不见小鱼四处逃窜。然而老人望着望着,只见一条小金枪鱼跃到空中,一个转身,头朝下钻进水里。在阳光下,这条金枪鱼闪着银白色的光泽。等它回到了水里,又有些金枪鱼一条接着一条地跃出水面,朝四面八方乱跳一气,搅得浪花翻腾了起来。它们追捕着小鱼,一跃就是老远,绕着圈子,把小鱼朝一处驱赶。
“要不是它们游得那么快,我可以把船划进鱼群里。”老人心想。他眼看着金枪鱼群把海水搅得白浪阵阵。只见那只鸟俯冲下来,扎进惊慌失措被迫浮上海面的小鱼群中。
“这只鸟真是个好帮手!”老人说。就在此刻,船尾的那根踩在他脚下的鱼线绷紧了(他把鱼线绕了个环儿套在脚上)。他放下双桨,紧紧抓住鱼线,动手往回拉,感到上钩的小金枪鱼不断抖动,有点分量。他越往回拉,鱼线抖动得就越厉害,他可以看见水里那蓝色的鱼背和金色的鱼身。于是他把鱼线呼地一甩,那条鱼越过船舷,掉进船里。鱼儿躺在船尾的阳光下,身子结实,形状像颗子弹,一双呆滞的大眼睛傻瞪着,灵巧的尾巴快速甩动,不要命地砰砰砰地把船板拍得山响。老人出于好意,猛击了一下它的头,一脚把它那还在抖动的身子踢到船尾背阴的地方。
“是条长鳍金枪鱼。”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用来当鱼饵倒是相当棒,恐怕有十磅重。”
他独自一人时喜欢大声地自言自语,他也记不清这种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了。在过去的那些岁月,他一个人的时候曾唱过歌,当轮到他独自在小渔船或捕龟船上负责掌舵时,他有时候就在夜里唱歌。这种自言自语的习惯大概是在男孩离他而去,只剩他孤单一人时才养成的吧。不过,究竟是何时他已记不清了。他跟男孩一块儿捕鱼时,他们一般只在有必要时才说话。在夜里,或者碰到坏天气,被暴风雨困在海上的时候,二人倒是喜欢聊天。出海时没有必要就不说话,这被认为是优点。老人一惯持这种观点,并始终如一。可现在,他心里想到什么便屡屡脱口说出,因为旁边没人,不会因此而干扰到任何人。
“要是别人听到我自言自语,会以为我疯了呢。”他大声地说道,“不过我没有发疯,也就不用管那一套了。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对着他们说话,把棒球赛的消息讲给他们听。”
“现在可不是记挂棒球赛的时候。”他心想,“现在应该只记挂一件事——我生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那个鱼群附近很可能有一个大家伙。我只从那群捕食小鱼的金枪鱼中抓住了一条落单的。可惜它们速度太快,已经游远了。今天露出水面的鱼都游得飞快,还都朝着东北方向去。难道一天的这个时候都如此吗?还是说,这是一种我不了解的天气征兆?”
这当儿,那道绿色的海岸线已看不见了,只看得见那些青山的白色山峰,像披着皑皑白雪,还看得见山峰上空的层层浮云,如高耸的雪山一般。海水颜色深极了,阳光射在水中形成了一个个棱柱。由于红日高悬,那数不清的斑斑点点的浮游生物已看不清了,老人看得到的只有深深浸在蓝色海水里的巨大的光柱,以及他那垂直没入一英里深水中的鱼线。
渔夫们把所有这类鱼都叫金枪鱼,只有到了出售它们或者用它们换鱼饵时,才叫它们各自的专有名称。此时,这些鱼又钻进大海深处了。阳光炽热起来,老人感到脖颈上热辣辣的。他摇着船桨,觉得脊背上汗水在一个劲儿地往下流淌。
“完全可以让小船随意地漂,”他心想,“我睡上一觉。把鱼线在脚趾上缠一圈,有情况我会醒的。不过,今天是第八十五天,我该好好钓它一天鱼。”
就在这时,他望了望鱼线,看见其中有一根高高挑起的绿色钓竿猛地往水中一沉。
“有情况,”他叫了一声,“有情况。”他轻轻放下船桨,小心翼翼地没让船桨碰到船体发出声响。然后他伸手拽住鱼线,将鱼线轻轻捏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此时鱼线没有绷紧,也感觉不到分量,而他用手轻握,没有放松。情况又出现了!这次,鱼线被试探性地扯动了一下,那扯动既不紧又不重,但他心里有数,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在一百英寻的深处有条大马林鱼正在吃用来包裹钓钩尖端和钩身的沙丁鱼。那个手工制的钓钩是从一条小金枪鱼的头部穿出来的。
老人有技巧地攥着鱼线,用左手把它从钓竿上轻轻地解下来。现在,他可以让鱼线在手指间滑动,而不会让鱼感到任何扯动的力量。
“这片水域远离海岸,又是这种月份,鱼的个头一定非常大。”他心想,“快吃鱼饵吧,大鱼啊。吃吧,快吃吧。这些鱼饵多新鲜!你在六百英尺深的冷冰冰、黑黢黢的海水里,游上一圈,再返回来把鱼饵吃掉吧。”
他感到一下微弱的扯动,随后是猛的一扯。八成是大鱼咬住了沙丁鱼,而沙丁鱼的头很难从钓钩上扯下来!再接下来就没有动静了。
“快吃呀!”老人说出了声,“游一圈再返回来呀!闻闻这些鱼饵,难道它们不鲜美吗?美滋滋地把它们吃掉,再吃那条金枪鱼。这可是瓷实、冰冷、鲜美的鱼啊!别不好意思,大鱼啊,尽情地吃吧。”
他把鱼线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等待着,同时眼睛盯着这根鱼线以及另外的几根鱼线,因为大鱼上下游动,说不定在哪个位置。随后,鱼线又被扯动了一下,仍是轻轻的一扯。
“它会咬饵的。”老人大声说道,“上帝保佑,让它咬饵吧。”
但大鱼没有咬饵。它游走了。老人觉得一下子没了动静。
“它不可能游走的。”他说,“上帝知道,它是不可能游走的。它在兜圈子哩。也许它以前上过钩,还留有一些记忆。”
说着说着,他感到鱼线被轻轻扯动了一下。这让他乐不可支。
“它刚才不过兜了个圈子。”他说,“它会咬饵的。”
鱼儿轻轻扯动鱼线的那种感觉让他高兴。随后,他感到鱼线被猛地一扯,那力量大得叫人难以置信——那是来自大鱼的分量。他松手让鱼线朝下滑,一直朝下滑呀滑的,把那两卷备用鱼线中的一卷都续上了。鱼线不断下滑,从他的指间滑过,虽然轻轻巧巧的,让他的拇指和食指几乎感觉不到压力,但他却仍然能感受到鱼的巨大重量。
“好一条鱼呀!”他说道,“它从侧面把鱼饵咬在嘴里,叼着鱼饵要游走了。”
“它会兜个圈,把鱼饵吞下去的。”他心想。他没有把这话说出声,因为他知道,一桩好事如果说破了,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他明白这是一条非常大的鱼,想象着它把金枪鱼横叼在嘴里,在黑暗中游走的情形。这时他觉得它停止不动了,可是鱼线上的分量却没变。接着,那分量在不断增加。于是,他又放出了一些鱼线。一时间,他的拇指和食指捏紧了鱼线,而鱼线上的拉力在持续增加,直直地向下拉。
“它上钩啦!”他说道,“那我就让它先美美地吃一顿吧。”
他让鱼线在指间朝下滑,同时伸出左手,把两卷备用鱼线空着的一端紧系在旁边那根鱼线的两卷备用鱼线的环套上。这一下万事俱备了。除了正在使用的这个鱼线卷,还有三个四十英寻长的线卷可供备用。
“再吃一些吧。”他说,“美美地吃吧。”
“吃呀!让钓钩的钩尖扎进你的心脏,取你的性命。”他心想,“慢慢地浮上来吧,好让我用鱼叉刺入你的身体。来吧!你准备好了吗?你这顿饭吃得时间够长了吧?”
“来吧!”他叫了一声,用双手使劲猛拉鱼线,收进了一码,然后连连猛拉,使出胳膊上的全部力气,用身子的重量作为支撑,双臂轮流使劲拉啊拉的。
结果白费力气。大鱼还是慢慢地在游走,老人哪怕把它往上拉一英寸都办不到。他的鱼线很结实,是专门制作用来钓大鱼的。他把鱼线贴在背上猛拉,鱼线绷得紧紧的,线上的水珠都弹起来了。鱼线在水里发出拖长的咝咝声,而他握住鱼线死不放松,身体后仰,整个人抵着座板。小船被扯动了,开始慢慢地向西北方向漂动。
大鱼不间断地游动,带着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徐徐行进。其他的几个鱼饵仍沉在水里,没有鱼上钩,因此不需要管它们。
“那孩子在跟前就好了。”老人大声说道,“我被这条鱼拖着走,都成了缆桩[24]了。我倒是可以把鱼线拴得死死的,不过只怕它会把线扯断。我得拼全力把鱼线握紧,它挣扎得厉害,就放出一些鱼线给它。感谢上帝,它只是朝前面游,而没朝海底钻。”
“假如它非得朝海底游,我就无计可施了。如果它沉到海底,死在那儿,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心想,“现在得采取措施,办法多着呢。”
他紧握住贴在他背上的鱼线,眼睛盯着水中倾斜的鱼线,小船被牵着一点点向西北方向移动。
“这样会叫它送命的。”老人心想,“它总不能永远这样撑下去吧。”然而四个小时之后,大鱼仍拖着小船在大海里游动,而老人也丝毫不敢放松地紧拉住贴在背上的鱼线。
“我是中午把它钓上的,”他喃喃自语道,“可我连它的影儿都没有见到呢。”
在钓上大鱼之前,他曾把草帽拉下,紧紧扣在头上,这时草帽勒得他脑门痛。他还觉得口渴,便双膝跪下,小心翼翼地不扯动鱼线,尽可能向船头移动,用一只手够到了水瓶。他打开瓶盖,喝了一点水,然后靠在船头上休息。他坐在从桅座上拔下来的桅杆和船帆上,竭力什么都不去想,准备一直坚持下去。
此时他转头向后望,发现陆地已不见了踪影。“这没关系,”他心想,“晚上有哈瓦那的灯光引路,我总能摸回去的。离太阳下山还有两个小时,也许在这期间它会浮出水面的;要不然,它会在月亮出来时浮出水面;再不然,它会在太阳升起时出来。反正我的手脚又没抽筋,我觉得身上充满了力量。它能把鱼钩吞进嘴里,而且它扯鱼线的劲儿那么大,肯定是一条大鱼。它的嘴准是死死地咬住了钢丝钓钩。但愿能看到它。真希望能看看跟我抗衡的鱼是个什么样子,哪怕只看一眼也行。”
观望天上的星斗,老人可以看出那鱼整整一夜始终没有改变它的路线和方向。太阳落山后,寒气袭人,老人的脊背、胳膊和衰老的腿上的汗水已经干了,他感到冷飕飕的。白天,他曾把盖在鱼饵箱上的麻袋取下,摊在阳光下晒干了。太阳落山后,他把麻袋系在脖子上,把它搭在背上,再小心地把它塞在横在肩头的鱼线下面。有麻袋垫着鱼线,他就可以弯腰向船头靠一靠,感到还算舒服。实际上这个姿势只能说可以少受些罪,可他觉得几乎算是舒服了。
“我拿它没办法,它拿我也没办法。”他心想,“它这么折腾下去,双方都无对策。”
中间有一次他站起身来,隔着船舷撒了泡尿,然后抬眼望着星斗,确定他的航向。鱼线从他肩上一直钻进水里,看上去像一道磷光。船速放慢了,缓缓移动着。哈瓦那的灯光显得并不怎么亮。于是他明白,海流肯定正把他们带向东方。
“假如看不到哈瓦那的灯光,那我们一定是到了更向东的地方。”他暗忖,“因为,如果这鱼没有改变路线,几小时内都是可以看到灯光的。不知今天的棒球大联赛结果怎么样了。捕鱼时有一台收音机那才叫棒呢。不该老想这种美事儿,应该想想手头的活儿。愚蠢的想法是不该有的。”
接着,他大声地说:“那孩子在跟前就好了,可以帮我一把,也让他见识一下这场面。”
“人上了年纪,就不该独自生活了。”他心想,“不过,要躲也躲不过。至于那条金枪鱼,在它变坏之前得吃掉它,好保持体力。可得记住呀,再不怎么想吃,也得在早晨吃掉它。”“可得记住呀!”他自言自语道。
夜间,两条鼠海豚游到小船边来,他听得见它们翻腾和喷水的声音。他能辨别出雄的发出的是噗噗的喷水声,而雌的发出的则是嘘嘘的喷水声。
“它们都是好样的。”他说道,“它们嬉戏,彼此相亲相爱,就和飞鱼一样,是人类的好伙伴。”
此时,他开始对这条被他钓住的大鱼产生了恻隐之心。“它真棒,真奇特!不知它有多大年龄了。”他心想,“我从没钓到过这么力大无穷的鱼,也没见过行为这么奇特的鱼。也许它太机灵,不愿跳出水来。它跳出水来,或者会来个猛冲,完全可以叫我死无葬身之地。不过,也许它以前多次被鱼钩钓住,知道如何跟人搏斗了吧。它哪会知道它的对手只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个老头子。这是条多么大的鱼啊,如果肉质好的话,在市场上能卖好多钱呢。它一口咬住鱼饵,看样子像雄鱼,扯鱼线的力量也像雄鱼,搏斗起来一点也不惊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计划,还是就跟我一样准备拼死一搏?”
他想起有一次遇到一对大马林鱼,用鱼钩钓住了其中的一条。一般进食时雄鱼总是让雌的先吃,那条上了钩的正是雌鱼。它发了狂,惊慌失措,拼命地挣扎,不久就筋疲力尽了。雄鱼始终守在雌鱼身边,在鱼线旁蹿来蹿去,陪着雌鱼一起在海面上兜圈子。雄鱼离鱼线非常近,老人生怕它会一甩尾巴将鱼线切断——那尾巴像大镰刀般锋利,连大小和形状都跟大镰刀差不多。老人用手钩把雌鱼拖出水面,用棍子打它,抓住它那边缘如砂纸似的剑锋长嘴,朝它的头顶一顿猛揍,直打得它颜色跟镜子背面的颜色差不多,然后由男孩帮忙,把它拖上船。而雄鱼一直守在船舷边。就在老人解鱼线、准备鱼叉的时候,雄鱼在船边高高地跳到空中,想看看雌鱼在何处,随后又落入水里,向深处下沉,淡紫色的翅膀——它的胸鳍——大大地张开来,把身上淡紫色的宽条纹一下子都露出来了。老人记得,它看上去很美,还久久不愿离去。
“它们那副样子让人看了太心酸了。”老人心想,“那孩子也感到难过。我们请求那条雌鱼的原谅,随后立刻动手把它宰了。”
“真希望那孩子在跟前呀。”他一边出声地说道,一边把身子靠在船头已被磨圆的木板上。通过勒在肩上的鱼线,他感受着钓到的这条大鱼的力量,而大鱼朝着它所选择的方向不停地游去。
“由于我设圈套欺骗了它,它才迫不得已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老人心想,“它原来选择的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诡计。而我选择的是到别人都不去的地方捕获它——全世界谁也找不到这儿来。现在,我们俩被拴在了一起,打中午就没有分开过。我们各自为战,身旁都无人相助。
“也许我不该当渔夫。不过,我生下来不就是要干这个行当的嘛!我一定要记住,天亮后就吃那条金枪鱼。”
快到天亮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咬住了他背后的一个鱼饵。他听见钓竿啪的一声折断了,而钓竿上的鱼线从船舷上缘朝着海中急速下滑。他摸黑拔出鞘中的刀子,用左肩承担着大鱼所有的拉力,身子朝后靠,就着木头船舷上缘,一刀将鱼线砍断,然后把另一根离他最近的鱼线也砍断了,摸黑将备用的两个鱼线卷的断头系在一起。他用一只手熟练地操作着,当将线头系牢时,一只脚踩住鱼线卷,不让它移动。他现在总共有六卷备用鱼线。他刚才割断的那两根有鱼饵的鱼线各有两卷备用鱼线,加上被大鱼咬住鱼饵的那根所备的两卷——六卷全都接在一起了。
“天亮后,”他暗忖,“我要退几步,摸到那根沉入四十英寻深处的鱼线边将它也砍断,把那些备用鱼线卷统统接在一起。这样一来,我将丢掉两百英寻优质的加泰罗尼亚鱼线,另外还有钓钩和导线。这些都是可以重新置备的。即便我钓上了别的鱼,若把这条大鱼丢了,那可无法重新置备了!我不知道刚才咬饵的是什么鱼。很可能是条大马林鱼、剑鱼,要不就是鲨鱼。我没来得及细想,就赶紧砍断鱼线,放走了它。”
“真希望那孩子在跟前呀。”他出声地说道。
“只可惜那孩子不在跟前。”他心想,“这儿只有你一个人。你应该赶紧摸到最后的那根鱼线边,不管天黑不黑,把它一刀砍断,系上那两卷备用鱼线。”
他照着自己的想法做了。在黑暗中,他倒是费了些气力。有一回,那条大鱼向前一蹿,把他脸朝下拖倒了,他眼睛下方被划了一道口子。血从他脸颊上淌下来,但还没流到下巴上就凝固,变成了干血块。他又摸回到船头,靠在木板上休息。他调整了一下麻袋,小心翼翼地挪动了一下肩上的鱼线,给它换了换地方,再用肩膀头把它紧紧顶住。接着,他抓住鱼线,谨慎地试了试大鱼的拉力,然后伸手到水里猜度小船行进的速度。
“真不明白它为什么要往前蹿一下子。”他心想,“八成是鱼线在它脊背上高高隆起的地方打滑吧。它脊背疼,肯定比不上我的脊背疼得厉害。哪怕它劲儿再大,也总不能拖着小船永远地跑下去吧。现在所有可能惹麻烦的障碍都排除了,而且有充足的备用鱼线。没什么可求的了。”
“鱼啊,”他温柔地大声说道,“我会奉陪到底的。”
“看来,它也要和我奉陪到底了。”老人心想。他在等待着天大亮。眼下正是曙光出现前的时分,冷飕飕的。他把身子紧靠在木头船帮上取暖。“它能坚持多久,我也能坚持多久。”他心想。第一缕曙光出现时,只见鱼线伸展着,通向海水的深处。小船一点一点向前行进,那时初升的太阳刚露出一个边儿,阳光直射到老人的右肩上。
“它在向北游。”老人自言自语地说,“海流会把我们朝着东边带,送出远远的。”他心想:“但愿它顺着海流游,那说明它累了。”
等太阳升得更高了些,老人发现大鱼并没有显出累的迹象。只有一个现象是对他有利的——鱼线倾斜了,这说明它正在较浅的地方游动。这并不一定表示它会跃出水面,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上帝啊,就让它跃出来吧。”老人说,“我有足够的鱼线,对付得了它。”
“也许我把鱼线稍微拉紧一点,让它觉得痛,它就会跃出来了。”他心想,“既然是大白天了,就让它跃出来吧,让它脊骨上的那些气囊充满空气,它就没法沉到海底死在那里了。”
他试着再用一些劲拉鱼线。可是自从他钓上这条鱼以来,鱼线已经绷紧到了快要挣断的地步。他身子后仰使劲拉,觉得鱼线绷得过紧了,知道不能够拉得更紧了。“拉鱼线绝对不能猛地使劲。”他心想,“每猛拉一次,就会把钓钩划出的口子加宽一分。等鱼一旦跃起来,也许会把钓钩甩掉。好在太阳出来让我觉得好受多了——这次我不必盯着它瞧了。”
鱼线上粘着黄黄的海藻,但老人知道这只会让大鱼扯鱼线时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很高兴。正是这些黄黄的马尾藻在夜间发出的那些磷光。
“鱼啊,”他说,“我爱你,也非常尊敬你。不过在今天天黑之前,我非得要你的命不可。”
“但愿如此啊!”他心想。
一只小鸟从北边朝小船飞来。那是只刺嘴莺,低低地贴着水面飞。老人可以看出它已经非常疲惫了。它飞到船尾,在那儿歇了歇。然后它绕着老人的头飞了一圈,落在那根鱼线上,在那儿它比较舒服些。
“你多大了?”老人问这只鸟,“你这是第一次旅行吗?”
他说话的时候,小鸟望着他。它太疲倦了,竟没有细看那鱼线,就用小巧的双爪紧抓住了鱼线,在上面晃来晃去的。
“这鱼线稳着呢。”老人对它说,“十分稳当。夜间又没有风,你不该累成这个样子呀。鸟儿们这都是怎么啦?”
他心想可能是老鹰飞到大海上追捕这些小鸟吧。但这话他没跟眼前的这只小鸟说,反正它也听不懂他的话,而且它很快就会知道老鹰的厉害的。
“好好歇口气,小鸟。”他说,“歇过之后再去迎接挑战,任何人、鸟或者鱼都是如此。”
说说话可以给他提提精神,因为他的脊背在夜里变得发僵,这工夫疼得厉害。
“小鸟呀,如果你愿意,就住在我家吧。”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趁现在刮起小风的时候,扯起帆把你带回去。但我总算有个朋友跟我在一起了。”
正在这时,大鱼猛地一蹿,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他拼命撑住了身子,放出一段鱼线,那么他早被拖到海里去了。
就在鱼线猛地绷紧时,小鸟飞走了,而老人竟没有看见。他用右手小心地摸摸鱼线,注意到手上正在淌血。
“大鱼显然被什么东西伤着了。”他一边出声地说道,一边把鱼线往回拉,看能不能把鱼拉回来。就在鱼线快要绷断的当儿,他握紧了鱼线,身子朝后仰,来抵消鱼线上的拉力。
“这下子你可知道疼了吧,鱼儿。”他说,“上帝做证,我也疼着呢。”
这时他转过脸去找那只小鸟,他很想让小鸟和他做伴,而小鸟却不见了踪影。
“你可没有待多久呀。”老人心想,“海上哪里风浪都大,只有你抵达陆地才能够平安。我怎么会让那鱼猛地一拉,把手都拉破了呢?我一定是越来越笨了。要不,也许是因为只顾望着那只小鸟,一门心思想着它了。现在我要把心思放在自己的事儿上了,然后得把那条金枪鱼吃掉,免得没气力了。”
“真希望那孩子在跟前呀。还希望手边有点盐。”他出声地说道。
他把沉甸甸的鱼线转移到左肩上,小心翼翼地跪下,在海水里洗了手。他把手在水里浸了一分多钟,注视着手上的血在水中散开。小船徐徐前行,海水一下一下慢慢地拍打着他的手。
“它游得慢多了。”他说。
老人倒是很想把手在咸水里多浸一会儿,却怕那鱼又猛地蹿动,于是他站起身,振作起精神,举起受伤的手迎着阳光晾一晾。手上的皮肉只不过被鱼线拉了个口子,可受伤之处却是干活用得着的地方。他知道这件事结束之前还需要这双手,不喜欢还没开始干活手就被拉破。
“现在,”等手晾干了,他说道,“我该吃小金枪鱼了。我可以用手钩把它钩过来,舒舒服服地在这儿吃。”
他跪下来,用手钩在船尾钩到那条金枪鱼,小心不让它碰着那几卷鱼线,把它拉到自己身边。他再次用左肩撑着鱼线,以左手和左胳膊支住身体,从手钩上取下金枪鱼,然后把手钩放回原处。他单膝压住金枪鱼,从它的头颈到尾部竖着切割,割下一条条深红色的鱼肉——这是些截面为楔形的肉条。他从紧挨着脊骨的地方下刀,直切到鱼腹边,一连切下六条肉。而后,他把肉条摊在船头的木板上,在裤子上擦擦刀子,拎起鱼尾巴,把整副鱼骨扔到了海里。
“我想我是吃不下一整条的。”他边说,边用刀子将一条鱼肉切为两段。他可以感觉到那鱼线一直都绷得紧紧的,累得他的左手都抽筋了——这只手紧紧握住那沉甸甸的鱼线毫不放松,他厌恶地看看他的左手。
“这算什么手啊!”他说道,“要抽筋就抽吧。哪怕变成鸡爪也行。这对你没什么好处的。”
“快吃吧!”他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一边低头看看黑黢黢的海水,望望那斜拉着的鱼线,“吃了鱼肉,你的手就会有力量的。不能怪这只手不争气,你跟那大鱼已经较量好几个小时了。要斗,你可以跟它斗到底。还是先把这金枪鱼吃了吧。”
他拿起一条鱼肉,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那味道并非难以下咽。
“可要细细地嚼,”他心想,“把肉汁都咽下肚。如果加上一点酸橙,或柠檬,或盐,那味道肯定不赖。”
“手啊,你感觉怎么样?”他问那只抽筋的手——那手又僵又硬,跟死尸的手一样,“为了你,我要再吃一点。”
他拿起切成两段的那条鱼肉的另外一半吃了起来。他细细地咀嚼,然后把鱼皮吐出来。
“现在觉得怎么样啦,手啊?是不是这话问得太早了些?”
他又拿起一整条鱼肉,咀嚼起来。
“这条鱼壮实而且气血旺盛。”他心想,“我运气好,捉到了它,而不是捉到一条鲯鳅。鲯鳅的肉太甜。而这条鱼肉几乎一点也不甜,它的力气都还保留在肉里。”
“别的什么都没有用,还是实际点好。”他心想,“要是有点盐就好了。剩下的鱼肉不知道会不会被太阳晒干或者变质。虽然肚子并不饿,但我最好还是都吃完了的好。那条大鱼目前老老实实、安安静静的。我把鱼肉吃完,做好与它一搏的准备。”
“耐心点,手啊,”他说道,“我吃东西全是为了你。”
“真希望能给那条大鱼吃点东西,”他心想,“它可是我的兄弟呀。但我还是得把它杀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积蓄体力。”于是,他慢慢地闷头吃着,把那些鱼肉条全吃光了。
他直起腰,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好啦,”他说道,“你可以放开鱼线了。手啊,我要单靠右臂来对付它,直到你不再闹别扭。”他左脚踩住刚才用左手攥着的粗鱼线,身子朝后仰,用背部来承受鱼线的那股拉力。
“上帝帮帮忙,不要让我再抽筋了。”他说,“真不知那大鱼接下来会怎么折腾呢。”
“不过,这会儿它似乎很镇静。”他心想,“看来它正在进行着自己的计划呢。但它的计划是什么呢?我又有什么计划呢?我必须随机应变,根据它的动向制订计划,因为它的个头太大了。假如它跳出来,我可以杀死它。要是它老待在水底下,那我就奉陪到底。”
他把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擦擦,想给手指活活血。可是那手就是张不开。“也许阳光强了,它就张开了。”他心想,“等我把这壮实的生金枪鱼消化掉,这只手可能就张开了。到了非用这手的时候,我一定能让它张开,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但我现在不愿硬生生地强迫它张开。就由着它吧,让它自己张开,自动恢复吧。昨夜收拾那些鱼线,又是解又是系的,把这只手累得够呛。”
他眺望了一眼大海,发觉自己此刻是多么孤单。不过他可以看见黑黢黢的海水深处那棱镜般的光柱,看见鱼线在眼前伸展,看见平静的海面上不寻常的微波荡漾。由于信风的作用,此时云团正在聚集。他朝前望去,看到一行野鸭从海面上空飞过。那些野鸭的身影在蓝天的映衬下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后来又转为清晰。他顿时感到,一个人在海上是永远也不会孤单的。
他想到有些人驾船出海,看不到陆地的时候就心生恐惧之感。他知道在天气说变坏就变坏的月份,产生这种感觉是有理由的。可现在正处于飓风季,在没有飓风的时候,飓风季的天气可就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了。
“出海时,如果飓风要来,一般你总能提前好几天在天空中看见种种征兆。在岸上可看不见,因为人在岸上不知道凭借什么来判断。”他心想,“陆地上倒也会出现些异常现象,那就是云团的形状会发生变化。不过,眼下是不会刮飓风的。”
他望望天空,看见一团团白色的积云就像一堆堆令人馋涎欲滴的冰淇淋一样,而在九霄高空则是淡淡的卷云,以九月的天空为背景,似羽毛般浮在那儿。
“现在刮的是‘brisa[25]’,”他说道,“鱼啊,这天气对我,比对你更有利。”
他的左手依然在抽筋,但他正在努力慢慢地把它张开。
“我恨抽筋,”他心想,“这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背叛。由于食物中毒而腹泻或者呕吐,是在别人面前丢脸。但是抽筋(这时老人想到的是‘calambre[26]’这个词),是自己让自己丢脸,尤其是独自一人的时候。”
“要是那孩子在跟前,可以帮我揉揉,从前臂一直往下揉。”他又想道,“不过,这抽筋总会缓解的。”
此时,他用右手摸摸鱼线,感到鱼线的拉力有了变化,连它在水中的倾斜度也变了。他倾身向前,看见鱼线斜着慢慢地朝上移动,左手不由啪的一声猛地在大腿上拍了一下。
“它上来啦!”他说道,“手啊,快伸开呀!快伸开呀!”
鱼线慢慢地、稳稳地往上升,接着小船前面的海面鼓起,大鱼浮出水了。它不停地往上冒,身上的水从两侧哗哗地朝下泻。在阳光下,它通体闪着光泽,脑袋和背部呈深紫色,身体两侧有宽宽的条纹,在阳光下带几分淡紫色。它的长嘴像棒球棒那样长,逐渐变细,如一柄轻剑似的。它把整个身子都露出水面,然后又潜入了水中,动作流畅得跟个潜水员一样。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般的尾巴唰地钻入水里了,接着鱼线开始飞速向外移动。
“这家伙比我的船还长两英尺呢。”老人说。鱼线不断展开,又快又稳,显然大鱼并没有受惊。老人用双手竭力拉住鱼线,用的力气刚好不致让鱼线被扯断。他明白,要是他不能平稳施力使大鱼慢下来,它就会把鱼线全部拖走,并且挣断。
“这条鱼的个头真大,我绝对不能惊动它。”他心想,“绝对不能让它知道它有多大的力气,也不能让它知道一旦逃跑它会做出什么事来。我要是它,现在就使出浑身的力气逃跑,一直跑到把鱼线挣断为止。但是感谢上帝,尽管这些大鱼比我们这些杀鱼的人高尚,也比我们有能耐,却不如我们聪明。”
老人见过许多大鱼,其中有不少是超过一千磅的,在他的一生中也曾逮住过两条重达千磅的鱼,不过每一次他都不是孤军作战。现在他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连陆地的影子也看不见,跟一条奇大无比的鱼拴在了一起——那鱼个头之大,他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他的左手仍没法伸展,像攥紧的鹰爪。
“它会停止抽筋的。”他心想,“它一定会停止的,停止了好帮助我的右手。大鱼和我的左右手,这三样东西现在亲如兄弟,密不可分了。左手必须停止抽筋。它现在抽筋实在是可耻。大鱼的速度又慢下来,跟先前的速度一样了。
“弄不懂它为什么跳出水来。它那样做,简直就像是要向我显示它的个头有多么大似的。这下子我倒是知道了。但愿我也能让它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只怕它会看到这只抽筋的手。应该让它觉得我是一个男子汉,一个比实际的我更具男子汉气概的人。我会给它这种印象的。真希望我和大鱼能换一下——它力大无比,而我只能靠意志和智慧跟它抗衡。”
他舒服地靠在木头船帮上,默默忍受着痛苦。大鱼不停地游啊游,小船在黑黢黢的海水里徐徐前行。从东边吹来了风,海上起了小浪。到中午时分,老人左手终于不再抽筋了。
“这对你可是坏消息啊,大鱼。”他说着,把搭在他肩头麻袋片上的鱼线挪了一下位置。
他觉得舒适了些,但仍感到痛楚,只不过他根本不承认那种痛苦罢了。
“我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他说道,“但我情愿念十遍《天主经》和十遍《圣母经》,只要让我抓住这条鱼就行。假如能抓住它,我许诺一定去向科布雷的圣母朝拜。这是我的承诺。”
他机械地念起祈祷文来。有时候由于太累,他竟把祈祷文都忘了,于是他就念得特别快,让祈祷文脱口而出。他觉得《圣母经》要比《天主经》容易念。
“万福玛利亚,你蒙受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永生。阿门。”念完后,他又补了一句:“圣母玛利亚啊,求你让这条鱼死去吧——即便它是那么不同寻常!”
祈祷完毕,他心里坦然多了,但那种痛苦依然强烈,也许比先前还要强烈些。他背靠在船头的木板上,机械地活动起左手的手指。
此时虽然微风徐徐吹拂,但阳光灼热。
“最好还是将船尾处那根细鱼线装上鱼饵。”他说道,“如果大鱼再要撑上一个晚上,我得再吃点东西。瓶子里的水已经不多了。这儿除了鲯鳅,恐怕我也捕不到别的鱼。不过,趁着新鲜吃,鲯鳅的味道也不会差。真希望今夜有条飞鱼会跳到船上来。可惜我没有灯光来引诱它们。飞鱼生吃味道绝美,而且吃的时候,没必要把鱼切成一块块的。现在,能省力气就省力气。天啊,没想到这家伙的个头这么大。它个头再大,再怎么了不起,我也得杀死它。”
“这样做虽然不公平,”他心想,“但我得让它看看我的本事,让它知道什么样的磨难我都经受得起。”
“我跟那孩子说过,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子。”他说道,“现在是证实这话的时候了。”
这话他已证实过上千遍了,而他觉得那不算数。现在他要再证实一遍。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端嘛。他自证的时候,从来不去想过去。
“但愿大鱼能睡上一觉,我也跟着睡一觉,重温下关于狮子的梦境。”他心想,“为什么现在我一做梦就总梦见狮子呢?不要再胡思乱想啦,老家伙。”他告诉自己:“你就靠着船板悄悄休息休息吧,什么都不要想。大鱼在忙着呢,而你就尽量少费力气吧。”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小船依然缓缓地、不停地前行。不过这时从东边刮来的微风给小船增加了一分阻力,老人乘船随着不大的海浪缓缓地漂流,鱼线不再那么吃力,勒在他背上引起的疼痛减轻了些。
下午,鱼线一度再次升起。不过,那仅仅是因为大鱼稍稍上升了一个高度,在这个海水层上继续游动。阳光洒在老人的左胳臂、左肩和脊背上,于是他知道大鱼折向东北方向了。
他曾经瞥过一眼大鱼,所以能想象它在水里游动的样子——它那紫色的胸鳍大张着,就像展开的翅膀;直竖的大尾巴划破黑黢黢的海水。“不知道它在那样深的海里能看多远。”老人心想,“它的眼睛真够大的。比较起来,马的眼睛要小得多,但在黑暗里却看得见东西。在以前,我在黑暗里也能把东西看得一清二楚——并非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不过,我那时的眼力简直跟猫一样棒。”
阳光的照射和他手指不断的活动,使他的左手彻底不抽筋了,于是他就着手移动鱼线,让这只手多承担一点拉力,同时耸耸背上的肌肉,把鱼线从勒疼的地方挪一挪。
“你要是不感到累,大鱼啊,”他大声地说道,“那你可真是一条不寻常的鱼了。”
反正他已筋疲力尽了。他知道夜幕转眼就会降临,于是便竭力去想别的事情。他想到了棒球大联赛,用他的语言说就是“Gran Ligas[27]”。他知道纽约市的扬基队正在与底特律的老虎队对决。
“联赛已进入第二天,可我不知道‘juegos[28]’的结果如何。”他心想,“不过,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像了不起的迪马乔那样,他即使脚后跟长了骨刺,疼痛难忍,也把一切做得漂漂亮亮。骨刺是什么东西呢?‘Un espuela de hueso[29]’。我们打鱼的不长这些东西。骨刺是不是跟斗鸡的爪子上装的铁刺[30]一样,扎进人的脚跟里,会让人疼得要命呢?我想我是忍受不了那种痛苦的,也不能像斗鸡那样,一只或两只眼被啄瞎后仍旧战斗下去。鸟与兽真了不起,人类和它们相比就不算什么了。我情愿做那只待在黑暗的深水里的动物。”
“但鲨鱼来了就惨了。”他出声地说道,“如果鲨鱼来了,就让上帝保佑它和我吧。”
“了不起的迪马乔要是遇到这样的一条鱼,能跟我一样坚持这么久吗?”他心想,“我相信他能,而且时间会更长,因为他年轻、力气大。再说,他父亲原来就是打鱼的嘛。但是,骨刺会不会让他疼得受不了呢?”
“这就不知道了。”他出声地说道,“我从来没长过骨刺。”
太阳落下去了。为了给自己增强信心,他回想起在卡萨布兰卡[31]的一家酒馆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他跟从西恩富戈斯[32]来的大个子黑人掰手腕,那家伙是码头上力气最大的人。桌上用粉笔画了一道线,二人前臂直直上举,将对方的一只手紧握,胳膊肘压在线上掰了起来,掰了整整一天一夜。他俩都竭力要将对方的手压到桌面上。许多人都押了赌注。酒馆里亮着煤油灯,人们在灯光下进进出出,而他紧盯住黑人的手臂以及脸。过了八小时后,他们每四小时换一个裁判员,好让裁判员轮流睡觉。他和黑人手上的指甲缝里都渗出血来了。他们俩直视着彼此的眼睛、手和前臂;打赌的人有的走进走出,有的坐在靠墙的高椅子上观战。房间里的墙是木制的,被漆成了亮蓝色,而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了墙上。黑人的影子硕大无比,随着微风吹动挂灯,在墙上晃来晃去。
在一整夜的时间里,获胜的可能性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输赢难定。人们把朗姆酒送到黑人嘴边,还替他点燃香烟。黑人一杯酒下肚,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掰,一度还把老人的手(他当时还不是个老人,而是“El Campeón[33]”圣地亚哥)掰下去将近三英寸。但老人又把手掰回来,恢复了势均力敌的局面。尽管黑人是个出类拔萃的好选手,但老人坚信自己一定能赢。天破晓时,参赌的人要求以平局收场,而裁判员不同意。老人使出浑身的力气,硬是把黑人的手一点点朝下掰,直到压在桌面上。这场比赛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开始的,直到星期一的早上才结束。好多参赌人要求以平局收场,那是因为他们得上码头去干活,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糖装上船,或者到哈瓦那煤炭公司去上班。要不然大家都会希望决出个输赢的。不过,老人终于把这场比赛终结了,而且是赶在大家去上班之前。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人都叫他“冠军”。到了春天,他们之间又举行了一场比赛,不过这次赌金不多,他轻轻松松就赢了,因为他在第一次比赛中击溃了那个西恩富戈斯黑人的自信心,至此余威尚在。后来他又赛过几场,以后就没再参加过了。他认定如果自己一门心思掰手腕,完全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却又认定掰手腕会把右手伤了不利于捕鱼,于是便尝试着用左手参加了几次练习赛。可惜左手历来都跟他作对,不愿听命于他,所以他对左手缺乏信任感。
“阳光这一晒,该把这只手暖透了。”他心想,“除非夜里太冷,否则它不会再抽筋了。真不知今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一架飞机从他的头顶飞过,沿着它的航线向迈阿密飞去。他看着飞机的影子惊起了成群成群的飞鱼。
“有这么多的飞鱼,就该有鲯鳅。”他说着,并把身子靠在鱼线上向后仰,看能不能把那大鱼拉近些。但他没拉动,鱼线照样紧绷着,上面的水珠抖动着,简直都快要断了。小船徐徐前行。他注视着飞机,直到看不见它为止。
“坐在飞机里的感觉一定非常奇特。”他心想,“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朝下看,大海是什么样子。要不是飞得太高,飞机里的人一定能清楚地看到这条鱼。真希望我能乘飞机在两百英寻的高度飞行,飞得慢慢的,从高空观赏海里的鱼。以前捕海龟时,我爬到船桅顶的横杆上,即便从那个高度看,也能观赏到海里的许多景象。从那里朝下望,鲯鳅的颜色看上去比较绿,你能看清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斑点,可以看见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海里游动。在深暗的水流中,凡是游速快的鱼,脊背都是紫颜色的,一般还带有紫色条纹或斑点。这是怎么回事呢?鲯鳅当然只是看上去是绿色的,实际上它们是金黄色的。但当它们肚子饿了,跑来觅食时,身子两侧就会出现紫色的条纹,跟大马林鱼身上的一样。是因为愤怒,还是游得太快,鱼身上才出现这种条纹的呢?”
天黑之前,小船从一大片马尾藻前经过。马尾藻在微波荡漾的海水里一起一伏,那情景就像是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色的毯子下做爱。就在这时,老人的那根细鱼线被一条鲯鳅咬住了。只见它一下子跃到空中,在太阳的余晖下看起来真像金子,它的身子在空中狂扭乱摆。接下来,因为惊慌,它像在做杂技表演似的一次次跃出水面。老人慢慢挪回到船尾处,蹲下来,用右手和右胳臂拽住那根粗鱼线,用左手将鲯鳅往回拉,每收回一段细鱼线,就用光着的左脚踩住。鲯鳅被拖到船尾跟前时,绝望中,它拼命地左右乱跳。老人从船尾探出身,把这条带紫色斑点的金光闪闪的鱼拽上了船尾。它的嘴被钓钩钩住,痉挛般地一张一合。它用又扁又长的身子、尾巴和脑袋把船底板拍得咚咚响。老人操起棍子,在它那金光闪闪的脑袋上狠狠地打了下去,直到它抽搐了一下,最后不动了。
老人把钓钩从鱼嘴里取下,重新安上一条沙丁鱼做饵,将鱼线甩到了海里,然后他慢慢地挪回船头。他洗了洗左手,在裤子上擦干。接下来,他把那根粗鱼线从右手转移到左手,在海水里一边洗右手,一边看着太阳沉到海里,还注意着那根斜入水中的粗鱼线。
“这大鱼一点变化都没有。”他自言自语道。可是,观察拍打他手的水流的时候,他发现船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我要把两支桨交叉绑在船尾,夜里就会让大鱼的速度减慢的。”他说道,“它夜里能撑得住,我也一样。”
“最好稍等一会儿再给鲯鳅开膛,这样可以让鱼血留在肉里。”他心想,“这事可以等一会儿再干,现在得把桨捆起来,以增加水的阻力。此时最好不要打搅大鱼,别在日落时分过分地惊扰它。对所有的鱼来说,太阳落山时分都是难熬的。”
他把手举起来晾干,然后抓住鱼线,尽量放松身子,听任大鱼把他朝前拖。他将身子抵在船板上,这样小船承受的拉力跟他承受的一样大,或者说比他承受的还要大。
“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想,“不管怎样,这方面该怎么办,我是知道了。还有,别忘了它咬饵以来还没进过食呢。它身躯庞大,要吃,那得吃大量的食物。我已经把那一整条金枪鱼都吃进肚了。明天我要吃那条鲯鳅(老人叫它‘dorado[34]’)。也许,在清理那条鲯鳅的时候,我应该先吃上一部分。鲯鳅比金枪鱼要难吃些。不过话得说回来,没有哪一件事是容易的。”
“大鱼啊,你现在感觉如何?”他大声地问道,“我感觉还不错,左手比刚才好些了。我的食物还够我吃一天一夜没问题。你就拖着这船跑吧,大鱼。”
其实他的感觉并不怎么好,因为鱼线勒在背上让他疼得厉害,几乎叫人无法忍受,最后那疼痛感变成了让他不能相信的麻木感。“没什么,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也曾碰到过。”他心想,“我的一只手仅仅划破了一点皮,另一只手的抽筋已经好了。我的双腿状况都算良好。还有,目前在食物方面我也比它占优势。”
此时天黑了。九月份,太阳一落山,天马上就黑下来。他靠在船头的旧木板上,放松全身心休息。第一拨星星露面了。他不知道Rigel[35]究竟怎么叫,但一看到它,他就知道其他星星很快就会出来了,他很快就要有许多远在天际的朋友了。
“这条大鱼也是我的朋友!”他大声说道,“这样的鱼,我从没见过,也从没听说过。但我必须杀死它。幸好我们不必去捕杀星星。”
“设想一下,如果天天都有人想去捕杀月亮,那该是什么样?月亮会跑得无影无踪的。再想想看,如果天天都有人想去捕杀太阳,那又会怎么样呢?说来我们是幸运的了。”他想道。
他为大鱼没东西吃而感到难过,但他的难过心情并没有减弱他必杀此鱼的决心。“这条鱼够许多人吃的了。”他心想,“不过,那些人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就它的行为举止以及高贵的尊严来看,谁也不配吃它。
“这其中的道理真让人捉摸不透。还好,人类还没有被逼着去捕杀太阳、月亮或者那些星星。在海上讨生活,捕杀我们的难兄难弟就已经够呛了。
“现在,我得好好想想制造阻力的事儿了。这样做有危险,也有好处。倘若大鱼拼命拖船,那么绑在一起的两把桨就会制造阻力,船身就不太轻便了,我很可能就得放出鱼线,最终让大鱼跑掉。让船保持轻便确实会延长我们双方的痛苦,但这样会让我安全些,因为这大鱼游得极快,它的速度截至目前还没有展示出来呢。不管怎样,我得把那条鲯鳅开膛,免得它坏掉。吃点鱼肉,长长力气。
“现在我还是再歇一个小时吧。只要我觉得那大鱼稳定下来了,我就回到船尾去干活,再做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观察大鱼的行为,看它有没有变化。虽然把那两把桨绑起来制造阻力是个好招儿,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该谨慎行事的时候了。那大鱼还是很厉害。我看见那家伙嘴角挂着鱼钩,嘴巴闭得紧紧的。鱼钩的折磨对它算不上什么。饥饿的折磨,还有跟不可知的对手抗争,才会给它造成最大的痛苦。好啦,休息休息吧,老家伙。让它去折腾它的吧,等轮到你忙活的时候再说吧。”
他觉得自己休息了两个小时。这一晚月亮一直到很迟才升起来,所以他无法判断时间。其实他并没有怎么休息,只是喘了口气罢了。他肩上仍然承受着大鱼的拉力,不过他把左手按在船头的舷边上,逐渐把抗拒大鱼拉力的活儿交给小船去做。
“要是能把鱼线拴牢,那事情就简单多了。”他心想,“不过,大鱼稍微一挣,就可能会把鱼线扯断。我必须用自己的身体来缓冲鱼线的拉力,随时准备用双手放出鱼线。”
“可是,你还没合过眼呢,老家伙。”他出声地说道,“你已经熬了半个白天和一整夜,现在又熬了一个白天了,而你一直没睡觉。你必须想个办法,趁大鱼安生的工夫睡上一会儿。如果不睡觉,你的头脑会糊涂的。”
“现在我的头脑倒是够清醒的,”他心想,“简直太清醒啦,跟我的星星兄弟一样清醒。但我还是必须睡觉。星星要睡觉,月亮和太阳要睡觉,连大海有时候也要睡觉——大海在那些无波无澜、风平浪静的日子睡觉。你可要记得睡觉,得强迫你自己睡。至于这些鱼线,可以想个简单稳妥的办法弄好嘛。现在先回到船尾去把鲯鳅收拾出来。如果一定要睡觉,把船桨那样绑起来拖在水里可就太危险了。”
“我不睡觉也能行,”他对自己说,“但那样太危险了。”
他靠双手双膝爬回船尾。爬动时,他小心翼翼地,生怕惊扰了大鱼。“此时它也许正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心想,“可我不想让它休息,而希望它一直拖,直到累死。”
回到了船尾,他转身让左手攥住紧勒在肩上的鱼线,用右手从刀鞘中拔出刀子。此时星光明亮,他能把那条鲯鳅看得很清楚。他把刀刃扎进它的脑袋里,将它从船尾拉过来。接着,他把一只脚踩在鱼身上,麻利地把它剖开,一刀从肛门一直剖到下颚的尖端。然后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掏出鲯鳅的内脏,把鱼腹清理干净,再将鱼鳃扯干净。他觉得鱼胃在手里沉甸甸、滑溜溜的,就用刀把它剖开——里面有两条飞鱼。飞鱼还很新鲜,硬实实的。他把它们并排放下,将鲯鳅的内脏和鱼鳃从船尾处扔进海里。那些东西沉下去时,在水中留下一道磷光。鲯鳅冷冰冰的,在星光下显得像麻风病人的脸色那般灰白。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剥下鱼身上一边的皮,然后将鱼翻了个个儿,剥掉另一边的皮,再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割下来。
一松手,老人将鱼骨架丢到船外,还留心看了看水里是不是起了漩涡,却只见骨架慢慢下沉时磷光闪闪。随后,他转过身来,将两条飞鱼夹在两片鲯鳅肉的中间,把刀子插进刀鞘,慢慢挪蹭着朝船头移动。因为负着鱼线的重量,他弓着背,把鱼肉提在右手中。
回到船头后,他把两片鲯鳅鱼肉摊在船板上,旁边摆好那两条飞鱼。然后他把勒在肩上的鱼线换个地方,又用左手攥住鱼线,将手放在船舷上。接着,他把身子伏在船舷上,一边在海水里清洗飞鱼,一边留意着水流冲击在他手上的速度。他的手因为剥鱼皮沾上了磷光,他观察着冲击着他手的水流,发现水流不像之前那样急了。当他把手的侧面在小船的船板上擦时,点点磷光在水面上浮起,慢慢朝船尾漂去。
“那家伙累了,或者说正在休息。”老人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得用这条鲯鳅填填肚子,休息休息,睡一小会儿。”
借着星光,冒着越来越冷的夜间的寒气,他吃了半片鲯鳅肉,还吃了一条已经清除了内脏、去掉了脑袋的飞鱼。
“鲯鳅煮熟了吃味道该多好啊。”他自言自语道,“生鱼肉吃起来真不怎么样。以后不带盐或是酸橙,我就绝对不再登船。”
“如果有点脑子,我就该一天到晚朝船头泼海水,海水干了不就有盐了嘛。”他心想,“不过,我可是快到太阳落山时才钓到这条鲯鳅的。但说来说去还是准备不足。幸好我细嚼慢咽地吃鱼肉,并没有感到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