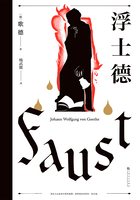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十六岁,在街角的一个不显眼处,守望一个人。
街上行人匆匆,逆着下午的阳光,我突然就有了一种孤独的感觉。阳光照射的目及之处—县人民礼堂,我看到了他。他用手撕扯着所有进去听下午戏的门票。我肯定这不是在制造一种戏剧效果,因为,这是我的初恋。我站在那个抬头正好目视他的地方,想我该找一个机会和他交谈。这种机会让我在这样的时空界限里等待了一年,我站在这里的全部意义就因时间的提示愈加无奈了。
事实上,是我自己在单恋。
1986年冬日,我坐火车去长春拍一部戏剧电影。在卧铺车的上铺,夜里兴奋得睡不着,看火车在静谧的华北平原中穿行,想《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也曾这样躺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从格子里看雪花飘浸的苦难的俄罗斯祖国,响起那三弄不已的旋律,每一次都有那黎明冉冉而起的激动。在火车上,一切仿佛是从一条道路到一条河流,当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存在并加以关注时,我想到我曾经的初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已经远我而去,想想看,我竟不曾与他说过一句话,永远看到的是拧着的眉,看人时从不多一点洞透,略微一扫,只记得大声吼过:“你们这一群唱戏的!”
我们这一群唱戏的,与现代生活截然相反的单调枯燥,却给我回味,那就是,历史以三五人的形象表演而延续着朝代更迭。历史很像是一幅图画里可以走来走去的部分,唱戏的虽不足解释整个生活的道理,却能让你读出近乎绝情的哀恸。
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不唱戏了,十几年唱来唱去,只演了一个被陈士美抛弃的秦香莲的女儿,怜兮兮一声声呼唤,如秦女士的两只水袖,佛来佛去,以不演唱故事的形式,延续着生活的继续。
我记得在长春时,我写过一封信给他。那是去伪皇宫回来,我为皇族社会最后一位皇后婉容心痛。郭布罗家族和爱新觉罗家族攀上了亲,做了一个退了位的皇帝的皇后,她的初恋诞生在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所有的子民已一律剪发喜庆共和,宣统只是一个空洞的尊号,给这样一个皇帝做皇后有多么尴尬苟且。她的初恋含合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意味,她最后疯死在延吉。信上我说,短的是初恋,长的是婚姻。婚姻是无法跨越的,因为我不能跨越初恋。
长春之后,我写过第二封信。那是在五台山。那里的女孩十五六岁,因恋爱不如意或别的什么而出家。人在剃度受戒之前是“在家”。而经过这道仪式之后,就算是出家了。有一女尼曾对我说,没有家,这里是我修行的地方。一句让我没有得到一点安慰的话。在信中我表达了我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可惜两封信都没有寄出。
1997年夏,我在北京和一位蒙族女人秀琴,在电影院看弗郎西丝卡和罗伯特·金凯的爱情故事。当时,有一些南方的同学很不屑于《廊》剧的演义,他们甚至无法相信一个人,怎么能用四十年的时间,去守候、去思恋、去执着一种仅存活了四天的爱情?秀琴说,恋爱是人永生的困扰,世界上如果真有爱情,譬如说被我们弄得没了心情,那就是失恋。秀琴说,人生目的太多,真爱定有。南蛮子的视觉之上,寸草不生。弗郎西丝卡和罗伯特·金凯,那是一种得到之后才找到的自己从前不知的遗憾和此刻的觉醒,用一生去守候。我和秀琴说起我的初恋。秀琴说,能解读那形象与姿势。初恋是没有实现的心愿,也是平庸中企图的奇迹,因此美丽。秀琴说,美丽的初恋让你站成一种永远等待的守侯。
想想人的一生,将会有多少东西遗失在路上?这是绝对的必然。我们无意抛弃人美好的一切,我们行走在生命途中,有一天会因心灵负载很重时,拾起被遗忘了的美好,感受着已往远去了的情调。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自然也就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了。我们常坐在沙发上说起往事。他说他曾经有过初恋,只是不记起对哪个女子有爱产生。那么说,初恋只能是一个过程,没有结果了,但决不可能没有记忆。他一定对我说了谎。这时,电视上正播放着香港的武打片《东邪西毒》。他说,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求爱?我说,哪有女孩子先行做事的。他说,理论上的绝对正确且难逃矫情的套路。这时,电视上的东邪正带着一坛新酒,从绿色遍染的东边到风沙燥烈的西域,送给那里的西毒。一坛酒,一世人,就只为了一个女人桃花。寂寞而又仇恨的旅行。桃花是以此试探西毒的真心,东邪是为借此一睹桃花的芳容,西毒是为了从此得到桃花的消息。一年一次,坛底见空。当手擎桃花的张曼玉,倚在夕照脉脉水晶晶的小轩窗前,肠断白苹洲时,结局自然明白。那种古典的浪漫情怀像破裂的一管箫音,自远而近。
初恋给我无尽的联想,我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存在。从恋爱的第一页到婚姻的最后,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它牵动着我的想象,让我相信世界上不仅存在着精神与念想,同时还有守候。我能够守候这些美好的事物,在生存的距离里与自然更为亲近,这样的日子我还需求什么呢?!
秋天是那样透明,高梁、玉米、毛豆,提着长裙走过田间时,思想在行进中就如水一样四处漫溢,我突然感到了某种温柔的触及。哦,这些泛着层层水波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