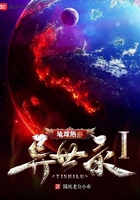也许,大多数时候,爱情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感动。至少在这一刻,他深爱着她。这是真相,可是这一刻已经流逝。
下一刻,不可预知也无迹可寻。
他重新闭起眼,将独孤息搂进自己的心口,然后闭眸假寐,不敢随便轻动,唯恐吵醒她。
直到——他发觉她自己坐起身。
“早。”贺兰无双笑笑,抬起头,正想去吻他刚才就觊觎很久的睫毛,接近时,才发现她的目光如斯冰冷。
“怎么了?”他轻声而不解地问。
“为什么要私自拿兵符?你不信我?”她的目光不知何时越过他,盯在床侧的那枚兵符上,“你猜忌我?”
“不是……”贺兰无双在看到兵符的一瞬有点慌乱,随即又镇定起来了,“我们就要成亲了,所以,不要再去理会这件事,可以吗?”
“你,不,信,我?”独孤息宛若未闻,仍然执着于最开始的问题。
“忘掉它。”贺兰无双也坐起来,凝视着她的眼睛,近乎命令地说:“以后再也不会了。”
“……可是为什么?”独孤息没有丝毫妥协,仍然追问。
她想不通,她已经倾尽所有,为什么仍然得不到他的全心信任?
“为什么……息儿,你为了炎子昊忤逆我的命令,你与他在阵前公然谈及婚嫁,你们在林中独处了一天一夜,他竟然毫无理由地为你退兵!你让我怎么想?这一切我都不想追究,你何必还穷追不舍,以证明你从来就是对的?!”贺兰无双也有点失控,失去了平日的冷静自持,许多话几乎不经考虑,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独孤息哽了半天,然后赤身走下床去,随便裹上件披风,扭头甩下一句话,“贺兰无双,你他妈混蛋!我竟然以为你是因为想我而来!”
说完,她赤着脚走了出去。
长发披散,光洁的小腿露在外面,微敞的衣服透出里面的春光。
外面的侍卫看直了眼,又很快将视线转开,满面通红。
她目不斜视,对自己造成的轰动效应无视之。直接闯进了裴临浦的房间。
裴临浦已经起床,正在那里整理文书。
他眼睁睁地看着独孤息走进来,打开他的衣箱。
“借几件衣服。”
她简短地命令了一句,随便翻找了几件衣衫,脱掉披风,一面将衣服胡乱套在身上,一面愤愤地向身边的裴临浦道:“马上启程离开这里!”
裴临浦却怔怔地看着面前的一切,面红耳赤,无法作答。
好半天,才讷讷地问:“去……去哪里?”
独孤息已经走到了门口,闻言又顿住了脚步。
去哪里呢?
“哪里都不准去!”贺兰无双不知何时也出现在裴临浦地门口,他盯着独孤息,粗声粗气道:“难道你想逃婚?”
“难道你又是真心想娶我的吗?”独孤息冷笑一声,剑拔弩张的模样。
“是。”贺兰无双却回答得极快,笃定而坚信,“除了你,任何女人都不够格当我的妻子。”
独孤息没有回答,仍然抱着手臂,冷冷淡淡地站在那里。
贺兰无双走过去。
他弯下腰,突然抱住她的腰,将她扛了起来。
独孤息一惊,正要挣脱,却听到贺兰无双低沉而磁性的声音,“我真想把你关起来,让任何人都见不到你的好。”
她于是安静下来。
裴临浦看见了她的笑。
她贴在贺兰无双的背上,双手拽得很紧,似乎生气,可是脸上却分明有笑,笑得那么舒心且幸福。
裴临浦突然觉得心底很酸。酸得发痛。
贺兰无双将独孤息扛了出去,他们第一没争吵,最后平静收场。
婚事,则紧锣密鼓地提上议程。
回到京都后,贺兰无暇很为大哥的决议感到高兴,前前后后的张罗着。
贺兰府的其他人,也都为这件亲事而感到欣慰:息夫人在军中的地位极高,而且才智也早已闻名遐迩,这样的女子与自己惊才绝艳的少主,本就是天生一对。他们的联姻,也保证了贺兰家问鼎天下的未来。
婚礼前半月的时候,他去看她,透过窗棂,却见她正在阅读一张细长的纸条。
听到门声,独孤息立即转过头,笑眯眯地唤了一句:“老公。”
守在独孤息旁边的小武望了望天,思忖着:无双公子不过二十多岁,年少有为,哪里老了?
贺兰无双微笑,从后面环起她的腰,目光下意识地看向被独孤息信手放在桌上的纸条。
他看到了炎子昊的落款。
上面只有寥寥数字。
“一月之约,望卿莫忘。”
很多年后,当独孤息想起她与贺兰无双之间的种种种种,她一直困惑于一件事:每当他们以为彼此相爱时,到底是谁率先毁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让一切再次陷入迷雾?
婚礼没有如期举行,天朝没有被合并的其他诸侯纠结起来,开始了最后一次困兽之斗。
贺兰无双连夜赶往如火如荼的前线,独孤息却被留了下来,包括她所有的亲信。
即便原本在战场的亲信也被连夜召回。
贺兰无双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独孤息对着蜡烛坐了整整一晚。
第二天,她忽而离家,并且修书给贺兰无双:我不能坐视不理,而将你弃于危险之中。
她违抗无双的命令,奔赴另一个战场。
这一走,又数倏忽几年。
几年中,他们聚少离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无非是军国大事。
而那一条长长的战线,也塑造了独孤息的另一个战场传奇。著名的‘以战养战’的理论,也在这条战线中被提了出来。
在缺少供给的情况下,她依然没有遇到过败仗。
一些人将她称之为救星,另一些人视她为恶魔。
可无论如何评价,独孤息以凌厉之姿,为贺兰无双解除了最后一个隐患,她是贺兰家立国当之无愧的功臣。
也因为她,贺兰家比预期早了十年统一了天朝,继而建立了贺兰王朝。
可贺兰无双对她反而淡了。
他对她时而温柔缱绻,可以在江南同食同寝、写下同生共死的诺言。时而晦涩难辨,更愿意呆在房间里看一夜的书,只留下个小丫鬟在旁边奉茶,而忽视着身边这位倾国倾城的美人。
被搁浅的婚事也就永远搁浅了。
理由总是很多,最大的理由便是来自炎国的威胁。
独孤息以为自己能理解,所以她决定履行与炎子昊之前的约定,用一月时间,将炎国的隐患彻底消除。
她去了炎国。
一月客居后,她与炎子昊打了一次赌。
这一次,他们赌的是布阵。
那次赌约,让炎子昊立下了有生之年不再入侵天朝的誓言。也让独孤息将他视之为终生挚友。
可是当她从炎国回来的时候,却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她已经被指婚给柳如仪。
那个秀气的,羞怯的,温雅的柳家世子。
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只有一张冰冷至极的圣旨,贺兰无双甚至没有见她。
她本想直接闯宫,却在最后时刻,站在了巍峨的宫门前。然后,她朝高高的宫门匍匐跪下,指甲扣在地板缝里,一字一句,冰冷生硬:‘息,谢主隆恩。’
她嫁给了柳如仪,事实上,一直在掀开盖头的时候,她才看清楚了柳如仪的脸,看见了一张俊秀的脸和满眼的爱慕与艳羡。
柳家也是天朝大家,这门婚事虽然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却也合情合理。
可是出嫁后的独孤息却似换了一个人,她被解除了所有兵权,然兵权于她本就可有可无。她是军队的神,无论她是否被授权。
她一直留在京城,却一直没有去见贺兰无双。
也从未进去柳如仪的房间,只是不分昼夜地在园子里大宴宾客,每日醉酒方归,形容洒然,醉意酣畅,一时成为京城文人墨客、风流雅致的另一个传奇。
杏花疏影里,吹笛至天明。
而柳如仪,只是安静地站在旁边等着,在宴会结束后,为她收拾残局。
有一天,似乎真的喝醉了——她一直沉于醉乡,却让人分不清到底是真醉还是假醉,只是这次,大概是真的醉了。因为酒散后,她竟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躺在花间石畔,一手执壶,一面风情万种地把玩着花束。
“你为什么要娶我?”她乜斜着眼,成亲后,第一没开口对他说话,“也是皇命不可违?”
柳如仪静静地看着她,看着月光轻洒,那个绝世出尘的女子醉卧花间,跋扈得不可一世却又说不出的寂寥萧瑟。
夜石冰冷,夜色如水。
柳如仪走到她的面前,轻轻地蹲下,第一没放肆地端详着她的容颜。
强势的女子,美艳自负得甚至对自己残忍的女子。让他总有一种不由自主去仰视去追随的冲动。可是今晚,她只是一个很美的女人。带着酒后微醺的余韵。
“是我主动向陛下求亲的。”他安静地回答:“我知道有点自不量力,可是……息夫人,你仍然是自由的。”
“为什么……”独孤息以手枕头,仰望着天际的漫天星空,梦呓般地问道。
柳如仪不太确定她到底在问什么,犹豫了一下,终于鼓足勇气道:“因为……因为我……”
他的表白没有说出口,独孤息的声音已经在夜风里传来。
“为什么他要背弃我?”独孤息明亮的眼睛似染上了星空的光辉,她转过头,定定地看着柳如仪,语气宁静得近乎无助了,“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为什么还是被背叛?告诉我,他是不是另结新欢了?还是……还是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