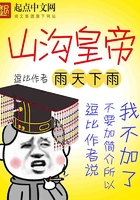这几日为了推广曲辕犁,苏良嗣可是费了一番心思,先是召集工部官员学习曲辕犁的制作方法,不用亲自动手,只要能讲出制作步骤,知道选什么木材,用多大的铁铧。
等到基本熟悉了制作过程,又将他们分配到各州,每一名官员带两件制作好的样品,十名能熟练制作的工匠,自洛阳为中心,慢慢向四周散开。
得益于曲辕犁既省了耕牛,又有更好效率,实际推广起来并没有太多阻力,只要试过曲辕犁的百姓,无不叫好,家底富裕的,直接掏上百多文钱买下,有些家中贫穷的买不起,大多数也能从官府手中借来。
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兢兢业业,恪守本分,林子大了,总会冒出一部分劣鸟。
这不,苏良嗣案头上的颂词已经压了一堆了,都是关于曲辕犁的,有的是官府不造,却将图纸给当地豪强,这些豪强造出的犁质量差,却要卖五百文,百姓去官府告状,却说衙门工匠不够,无法造犁。
平民百姓买不到新犁,豪强之家的田中佃户却家家都配上新犁。
苏良嗣有心整治贪官污吏,却人手不足,只能先剪除洛阳周边的一些不法之人。
这几日苏良嗣一举罢了四五个县令,县丞主簿更是抓了不少。
苏良嗣抓人抓得痛苦,一同负责推广曲辕犁的武三思却坐不住了。
“我说苏尚书,你管这些干什么,新犁给他们让他们自己造就行了,百姓世家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我大唐子民吗?难道还非要让那些泥腿子都用上新犁不成?”
依武三思的想法,只要有人用就行,具体谁用就不用管了,豪强们用还更好,起码他们知道孝敬自己,那些泥腿子哪里有钱给自己送礼。
听了这话,苏良嗣可忍不住了,本来太后让我们两人一同负责推广,你武三思不干正事也就罢了,毕竟这洛阳是个人都知道你武三思只知道媚上欺下、勾结朋党,无一点真才实干,那你就等着分功劳就行了。
“胡言,太后让我等推广曲辕犁,本就是为了给勤恳种田的农户更好的犁,让他们能多产些粮食,不将新犁给他们,还能给谁?难道要让那些豪强得了新犁,更加欺压百姓吗?”
苏良嗣这几日辛苦整治贪官,越说火气越大。
“你当我不知道那几个县令都是你府上常客?太后让你推广新犁,你不思造福黎庶,竟敢和这些小人勾结,将新犁都给了豪强,百姓拿着几倍的价钱,买到的还是制作粗劣之犁,本官明日就上书太后,看你能嚣张到几时!”
武三思见苏良嗣不仅不给自己面子,还要上书参他,气的指着苏良嗣道:“你…你…”
“你什么你,滚!”
看着苏良嗣怒发冲冠,一副要动手的样子,武三思却不敢再说了,扔下几句狠话,灰溜溜地回了府上。
“竖子!竖子!这个苏良嗣,一副将死之像,我看也没几天好活了!还有这个薛绍,不好好伺候太后,偏要弄出什么曲辕犁来,真是该死!”回府的武三思,将气都撒在了仆役身上,听着院里的惨叫声道:“把他们嘴堵上,听得本官烦死了。”
……
夏竹脚步匆匆,进了屋内,对太平公主行礼道:“公主,香水已经调配出来了,共有一百三十瓶。”
将视线从崇训身上收回,太平看向夏竹道:“很好,你分出二十瓶送进宫里给母后和上官姐姐,再给几位兄长的府上也各送去五瓶,剩下的就摆在店里吧!”
“我这就去办,公主不给其他皇室府上送吗?”
“不用,她们一个个消息灵通,不用我送也会知道的,成衣匠招够了吗?”
“已经招了近百人,都是原本尚衣局中之人,已经让她们开工了。”
太平握起拳头挥了挥,店铺已经装饰完成,成衣匠也有了,更兼香水这样的精致之物,百川商号不火都难。
刚开始还以为薛绍让她将五成利润交给内帑要赔钱,昨夜算过了香水的成本,才知道哪里会赔钱,分明就是要赚的盆满钵满啊!
或许是因为香水方便使用,又或许是因为留香持久,只要用上一次,便和以前的熏香说了再见,纷纷打听香水出自哪里。
一瓶仅仅五毫升的香水,成本不足五十文,就算配上下等玉瓶,成本也不过几百文,可太平以十贯一瓶的天价出售,剩下的百瓶香水,还没在殿中摆上半天,便都被抢购一空。
店中的内衣生意倒也可观,只是比起香水就没有那么火爆了,毕竟香水男女都能用,还有熏香的基础在,内衣就太过私密,除了富家女子,平民根本不敢穿,而男士的内衣,以太平的性格,哪里会去做,就算是有钱赚,她也只做女性的内衣。
太平瞧着掌柜送来的账单,眉目间喜不自胜,正要与薛绍分享之时,一则消息令两人的情绪都沉了下去。
刘仁轨薨了。
这位在白江口一战,灭百济,败倭军,一战奠定了唐朝在东方的地位,战功赫赫。
不仅军事能力出众,为政也是清廉刚正,一路升至宰相,在李治与武则天来洛阳之后,留他在长安主持事务,出将入相。
对刘仁轨的死,早就知道的薛绍却也无能为力,刘仁轨已经八十四了,在人均寿命不高的现在,已经称得上高寿了。
在后世都没能解决的事,薛绍也没有办法。
听到这个消息,太平脸上笑容尽去,幽幽道:
“郎君,刘公一去,母后的心思,已经无人能阻了!”
薛绍摇摇头,就算刘仁轨还能多活几年,武则天称帝也无法阻挡,此时武则天大权在握,称帝只需走个过场而已。
“莫要担心,只要保证李唐宗室不亡,天下富足安定,太后称帝也不是什么坏事,何况,她现在除了名号,与皇帝还有什么区别!”
太平摇摇头,她自然也是知道,此时武则天除了一个皇帝的名号,已经与皇帝没什么两样了,只是她想起兄长与姐姐,就难以放心。
“郎君,妾怕,妾真的担心,有一天醒来,就剩下妾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