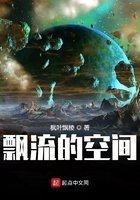小沈旭自告奋勇去开门,但打开门后,却被门口的人的眼神吓了一跳,急忙跑回了座位。
来的是个彪形大汉,一身的肥膘,如果双手换成猪蹄的话,就像是一头直立的肥猪。在他旁边,还站着同样肚大腰腰圆的妇女。
吓到小沈旭的就是这个妇女。一看到开门的小沈旭,她的眼神就像毒蛇一样,充满了恶毒。
“老朱,春花?”沈良看到两人,诧异地叫了声。
这夫妇俩是街头的杀猪匠,老朱,朱大元和他媳妇春花。
瑞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最近的一座城也有两百多公里,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瑞安没有车商,除了一些势力,普通民众根本没车,也就没法出城了。一些来往的货物,都是有的势力去批发来,民众们需要的再去买,或者二次批发了开店。
没有条件,瑞安城里养猪的也就不多,仅有的一些家养猪肉都是特定供给的,一般人想吃肉,只有城外游荡的野猪。
而朱大元,就是专杀野猪的杀猪匠,一些人专门去猎了野猪,或者侥幸遇到将死的野猪,害怕腥臊,都会带来给他杀了,再分配一定的份额给他,长久下来,一家人也吃的膘肥体胖。
但野猪不多,基本上几天才有一单生意,不杀猪的时候,夫妻俩就会坐到门前街上,没事的时候晒太阳,有事的时候就骂街。
长时间下来,妇女春花成了附近几条街的骂街一霸,每每有人看到她的骂街景象,都会深深地怀疑,她家的猪肉是吃到嘴上去了吗?
一般来说,朱大元都会坐到椅子上,晃着几乎被完全遮蔽的椅子,一边看妻子春花骂街。
如果要投最惹人讨厌的街坊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投他家,剩下的百分之九的人都吃了他家猪肉,或者企图去买猪肉能便宜点。
这样的一两夫妻竟然有一个奇怪的儿子,人傻傻的,传言是临近出生时春花正在和人骂架,腹痛了也强忍着等到骂完,才去生下儿子,导致其脑袋受损了。
而这个儿子,性格却和其父母是两个极端,人虽傻,但很有礼貌,不跋扈,其他孩子们都喜欢和他玩。还认死理,任他母亲怎么教他骂人,别把猪肉给玩伴们吃,他都当耳旁风。
知道的人都说,这孩子是天上降来给其父母赎罪的。
这个男孩,就是和小沈旭一起逃下皮卡,然后留在桥洞里的另一个一直流鼻涕的孩子。
看到这夫妻俩,沈良和陈虹的脸色变了又变。
尽管隔的不远,他们打的交道却不多,因为两家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没有意外的话,双方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交集。沈良家吃的肉也都是去肉市上买的,更贵一点的风干野猪肉。
现在意外来了。
没管沈良亲近的称呼,也没有客套话,春花进了门就态度恶劣地大喊着:“我的儿子在哪里?”
朱大元也恶狠狠地盯着在座的人,似乎把大家当作了砧板上的野猪。
没等沈良说话,陈虹就断然道:“不知道。”
她的性子虽然平日里文静,但女人间如果不和,那就是真的不和,不会和男人间一样有虚以为蛇的可能。
春花抢前几步,指着陈虹,“不知道?我儿子和你儿子一起被拐卖走的,为什么你儿子回来了,我儿子没有回来?”
原来也在前几天,平日里只有偶然发生的拐卖突然猖獗起来,附近几家遭到了光顾,孩子都不见了,多的有五六天,少的一俩天。
前天,几个失踪的孩子被找到了,就是沈良和李婧萍就出来的那几个,其他几家不平衡了,有的耐不住去了警察局闹了几次,被轰出来了,其中一个动了手的还被枪托打掉了几颗牙齿。
朱大元夫妻没去,心急火燎地盼着等着,终于听到了又有失踪的孩子回来了,但却不是自己家的,而是附近沈家的。
夫妻俩想了想终于耐不住,准备来沈良家问问情况。
陈虹冷冷地说:“我怎么知道?”
春花大怒,“你凭什么不知道?”
陈虹却不屑,“我凭什么要知道?”
春花撩起袖子,看过他骂架的人都知道,这是她准备开骂前的准备,“你不知道,就让你儿子来和我说话,我问他!”
陈虹冷笑,“你什么样不知道?除了你自己家的,哪家的孩子看了不怕?看了晚上不做噩梦?”
这几句话的交锋,几个男子竟是叹为观止,丝毫插不进去话,尤其是沈良,他可很少见过妻子这般模样。
正争吵间,街上又走来几个人,看到堵在门口的朱大元夫妇,愣了下,明白了什么,小跑几步凑过来。
沈良凑在门缝前看了看。是这条街住在烂胡同里的一家人,烂胡同是街上斜过去的一条胡同,环境幽深脏暗。
这几人一男一女都是中年,还有个白发佝偻的老妇人。祖孙三辈人生活在个窄窄的单间里,还用板子隔了两个放床的卧室,一个祖孙两人睡,一个容纳两夫妻。剩下的地儿,有人去过他家,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只能放张小桌子,供人站着围着吃饭。
至于上厕所洗浴什么的,烂胡同一共四户人家,商量着建了个单间,放在胡同角落一起使用,只是要自己烧水并且事后清理干净。
或许是因为麻烦和难堪,烂胡同里的人都洗漱不多,个个干的又是苦活累活,身上都带有馊味儿,其他人家都很难亲近他们。
这一家人,沈良也知道,从烂胡同口过时,偶尔也能看到,但没有交集,每次擦肩时各自都是低头狂奔着忙生活,哪有时间打招呼经营关系。
他家很低调,或者至于卑微,沈良倒是知道的,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和众人一致的远离,平时几乎没认注意到他家。即使在烂胡同里的几户人家中,他家也是最没存在感的。
没听说,他家的孩子也丢了。
但在这个时候,除了这个事,沈良也想不出为何他们会来。
走到离门地不远处,几个人就停住了,搓着手跺着脚,显得紧张,但又急促地不敢向前。
沈良见状,挤开朱大元夫妇的堵截,走出门,看着几个人,却想不起这一家人的姓名了。
他只能含糊道:“呃,兄弟,你来是有什么事吗?”
站在街边水沟前的男人,衣裤上都是泥,还有几个晃眼的破洞,挽着裤脚,很像以前憨厚的农民,自从来到瑞安后,瑞安无法耕作,沈良也很难看到这样的浑似农民的人了。
“听说你大儿子回来了,我想问问,我的儿子回来了没?”
即使沈良知道他会这样问,但还是哽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农民一样的男人沉默了,眼中的神采如烛光熄灭,半抬着覆盖厚茧的黄色大手,似乎想擦擦眼泪,但又迟疑着没动。
倒是一起站着的朴实妇女,忍不住哭了,捂住嘴没哭出声。她的年迈的瞎眼婆婆挨着她站,感受到她的身体颤抖得厉害,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
男人没哭,但不断喃喃:“儿子,我的儿子,到底去了哪儿呢?”
看到这一幕,沈良只能沉默。
躲在屋内最后的小沈旭拉了拉陈老的裤腿,指着屋外的老人,似乎说想要出去,但看到老人摇头,就没动了。
被沈良粗暴挤开的朱大元夫妇俩忽然没声音了,站着看了看戏,但看着沈良和其他人僵持住了,还没给自己想要的答复,顿时急了。
春花吼道:“沈砖头,你给句话啊!管这几个馊馒头干嘛?”
沈砖头这个称呼,叫的人不多。起初是春花去沈良的店里吃饭,想着自家掌握着这条街的肉食命脉,便要求沈良给她免了饭钱。沈良不肯,她就这样叫了,意思是像块砖头,冷硬硬的不给面子。后来有些想吃白食的,没能成功,也附和着叫。
沈良没回答她,对这称呼也不在意。
但另一家人可就在意了。自从那个人进了他家,说了句“你家的馒头是发馊了吗”,出去后,这句话不知怎的就流传了出去。大人不在意,孩子就在意了。
没有哪个孩子自尊心不强的,他家的孩子出来玩儿,就总被其他孩子们叫“馊馒头”,孩子怒了,打了几次打不过,就辩解说,“我们才不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洗澡的,那天我爸会早就回家,烧了水,一家人去洗。”没想到这话说了反而让人变本加厉,更加沦为笑柄了。
这也成了孩子心中的痛,每次出去被骂后,回了家就哭着对父母述说,有时还哀求能不能每天洗澡,当父母沉默后,更是生气撒泼起来。原本不在意地夫妻俩,也开始在意起来。
这时听到这话,即使畏惧春花的“威名”,妇女俩再忍气吞声也忍不了了,就想还口,却听到了陈虹的声音,感激地看了陈虹一眼。
陈虹见她还想说什么,便截道:“你还想吵的话,我陪你继续。”
论吵架她春花就没怕过谁,别说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她都不会认怂,更何况现在她孩子不见了,心火正旺,恨不得见人就喷。
她还没说,就被丈夫朱大元拉住了。
朱大元阴沉着脸道,“至少你儿子看到我儿子没,他们一起的,怎么就你儿子回来了,其他人家的没回来?该给个说法吧。”
他倒比媳妇春花理智,说的话不止说自己,还包括了其他人。
粗厚汉子果然往沈良看了过来。
沈良知道,这么僵持着不是件事儿,怎么也要给人家个说法,符不符合对方心意不重要,给了说法他就有理由让对方离开。
至于怎么说,事情来得紧急,他没想到,这会儿脑袋里一直转,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说法。
蓦地一个声音插了进来,然后一个人走了出来,沈良一看,是陈老:“他家的娃娃是我救回来的。”
所有人都看向老人,春花夫妇更是恶狠狠的。
老人面色不变,说道:“是我在城外看到那辆车,趁停车的时候偷了一个麻袋下来,没想到里面是个孩子,就送来了。”
朱大元问,“其他孩子呢?”这话让所有人瞩目,都看过去听过去,连沈良和陈虹也不例外。
老人摇头,连犹豫都没有,“不知道,可能还在麻袋里,被送走了。”
听到这话,其他人还没反应,小沈旭却惊诧地跳了起来,想要说话,但被眼尖的陈虹捂住了嘴,其他人都没看到。
春花喊道:“不可能,不可能,你们肯定是一伙的,一定是你们串通起来,把自己儿子送回来了,其他人都被带走了。”
老人突然转过身,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如果是在二十年前,就你说的这句话,我就能把你抓起来。”
春花没说话了,一方面是被老人话里的意思吓到,更多的,是畏惧老人的威严。
朱大元看了众人一眼,拉着自己媳妇走了,春花还想挣脱,但被他狠狠一拽,差点摔倒,也就没反抗了。
憨厚男人一家也沉默着走了,丈夫搀着妻子,妻子搀着瞎眼的婆婆。
几人回到屋内,沈良拿起饭扒了两口,看向老人,又端起了酒。这次老人没推脱,也端起了酒杯。
还没喝,小沈旭就说话了,“爸爸,老爷爷,那个大叔家的儿子就是小志啊,还有那个胖大婶,他儿子我也知道,那个鼻涕虫,和我在一起逃出来的。
我叫他们等着我,不过我没找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