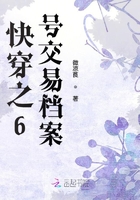星期天午后,黄轲和王大胆骑着自行车来到电影院,先把电影票买了,然后找了家台球室对撂起来。
他们没有赌博,否则王大胆多少钱都不够输,但为了混时间,黄轲就打得很随意,拿起杆子就捅,很少像瞄。
宝源虽然经过了断断续续的严厉打击,街上的治安好了很多,但是新成长起来的无业游民仍然不少。
虽然沿海的几个经济特区已经开放了八七年,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去那些地方打工,但距离大规模的打工潮来临却还有两年,
于是这些无能力、没技术、没文化的无业游民们就只有几个出路,当兵、打工、混社会。
混社会的有些脑子灵活,他们多数继承了一些古老的行业,比如窃、诈、诓、局等偏门。
剩下的大部分就聚集在城里的台球室、电影院、录像厅、火车站等地方混日子,有时候他们手中拮据的时候,就会向陌生的路人伸手,或敲诈点钱粮,或摆顿酒买几包烟。
宝源的台球室也是解决无业青年的一种举措,他们的同龄朋友便自然成了老客户,也为店主撑撑场子。
遇到有人想打球却没对手时,他们就陪着打一会儿混时间,顺便找有赌博因子的菜鸟搞几局,挣点烟酒钱。
既帮老板拉住了客人,也肥了自己的腰包。
黄轲和王大胆打球,自然有人专门摆球,旁边也必定有无聊的年轻人在看俩人打,时不时好意的指点几下。
于是,在摆球的时候,一个头发遮住了耳朵的年轻人说话了。
“有没有兴趣打几局?”
“没兴趣。”
王大胆头也不抬就一口回绝了,俯身开球。
“嘿嘿,这样打不进去,后手再低一点,下巴抵在杆上……”
年轻人不以为忤,仍然热心的给王大胆指点,他坚信只要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搭上话之后,应该能从这两个家境不错的学生口袋里掏点钱出来。
县中和二中的学生星期天一般有两个去处,男生多数会来到全城最热闹的电影院广场打打台球、看看录像、玩玩电子游戏,女生就是逛街,特别喜欢去有摆小摊贩的地方。
黄轲的家境没有王家深厚,但姐姐的铺子却可以包揽一家人的生活和零花,并且还能存些钱。
所以他的穿着也比较偏贵,虽然不是流行得不要不要的喇叭裤,但也是价格不便宜的牛仔,白衬衣也没有洗得变色、揉得皱巴巴的,手腕上虽然不是王大胆那种最贵的电子表,却也是一只上海牌机械表。
人们的思维就这样,明明电子表比几十上百的机械表要便宜,但大家却偏偏要疯狂的追捧。
当然,如果黄轲不是有一颗中年心,他也会同样如此,因为前世就是这样。
包括喇叭裤、蛤蟆镜、烫卷发等。
但黄轲的大哥就相当的不低调了,不但前面所说的几样都有,还有一台肩扛式收录机。
甚至最近又在引诱黄轲,让他找黄琴要钱去买一辆摩托。
他当然没有同意。
因为自己的小翅膀,改善了家里的经济条件,但同时也导致老哥陷入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中,他不知道该不该感到后悔。
人们说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但怎么活却有很多不同,有像李红那种活得卑微的人;有王大胆和老哥这样啥都追求流行时髦、充满虚荣心的人;也有买菜的时候,为了少几分钱就讲价半天,但身上的衣着却隐含着高贵气质的小资。
但社会上最多的,却仍然是挣扎在温饱线以下的普通老百姓。
当然,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达到了一定程度后,想适当地改善生活无可厚非,只要保持住做人的本心,那就没必要去指责。
所以,对于大哥黄强的做派,作为兄弟就没必要反对,更不可能鄙视,只要不超出承受极限,他还是会同意,并让爹妈不要随时都唠叨他。
因为大哥已经成年,属于招蜂引蝶的年纪,有这些举动很正常。
黄轲想想就有些好笑,自己是他的兄弟,而且还在读书,但是在家里却仿佛比他大,爹妈和姐姐什么事都不会满着自己,大事情也商量着来。却随时随地埋怨、甚至训斥黄强整天无所事事。
在前世,黄强高中毕业后,先是参加了体委的体操队,去省城参加比赛回来后却没解决编制,然后去了乡广播站上班,时间也很短暂,在乡上耍了个女朋友后就辞职不干,然后跟着别人去开小煤窑,先小亏,后大亏,直到家里的积蓄全部亏完,然后才去了沿海城市。
直到数年后黄轲开了家装饰公司,他才回来帮忙,然后就一直在装饰行业干下去了。
目前他还没去体委,也没有收到通知。
体操队他应该去,毕竟是一个美好的经历,但如果他又萌生了开煤窑的想法,黄轲就会坚决阻止。
他有这个能力,因为掌管钱的姐姐听他的,爹妈也会接受他的意见。
“想啥呢?”
王大胆用杆子捅了黄轲一下。
他赶忙笑笑说了句没啥,然后随手一杆打进一颗球,第二颗瞄半天又打,这回却没得进。
年轻人从穿着上看出两人的家境,又从王大胆挂在墙上的书包知道是学生,就暗自开始运作了。
“兄弟,你们这技术……啧啧,打得够烂的。让你俩球都随便赢你。”
王大胆看了他一眼,坚持把球打了才说道:“烦不烦你?就在旁边叽叽喳喳的,想打球就让三颗,敢不敢嘛?”
“不行不行,最多让俩球,毕竟你只要认真点打,我让俩球都不一定能赢,让三球还不如我请你们算了。”
陪打的主要目的是让客人起到过过瘾的目的,并且保证自己不掏台子钱,那么有时候会适当地让一两局,只要总的局数多了,几毛钱台老板是不会找陪打要的,何况本来就是朋友,收钱太生疏。
“呵呵,要嘛就让三球,要不就算了。”
王大胆摇摇头,并不为所动。
年轻人犹豫着,看他表情仿佛认为胜算不大、还在纠结,但手中却早已经拿起了球杆,边抹着巧克,嘴里继续念叨让俩球行不行。
黄轲一直没做声,继续和王大胆打着。
见这两个学生好像都没在乎他,年轻人便恨恨的说道:“好!我今天破例让三球,不过咱还是得带点彩,否则多没劲啊?”
“行啊,多少?”
王大胆斜眼看着他问道。
“一块?”
“行。”
每一局给老板两毛,惯例是赢家给,朋友间玩耍除外。
一块钱就能剩八毛,估计赢上七八局之后,输家一般就不会继续,否则就叫做不明智,但到手的也有五六块,够两天的烟钱了。
但是如果遇着俩人技术都差不多,打的局数又多,那么俩人都赢不到什么钱,甚至还亏,但最终有个赢家,那就是台球老板。
王大胆和年轻人打三局输三局,等把第四局球摆好,他突然把杆子朝黄轲一扔说道:“你来帮我打,你打得好些。”
黄轲摇摇头:“输了几块钱算了,干脆不打了吧。”
“别,输钱事小,但是被剃零蛋事大,咱得赢回来。……敢不敢加码?”
王大胆后半句是对着年轻人问的,嘴里冒话,眼里冒火,带着挑衅,带着不服输的骚劲。
“呵呵,加多少?”
王大胆指着黄轲说道:“我俩都不差钱,但他从不跟人赌博,输赢并不重要,主要是钱少了他没兴趣,而且最少五块,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往上加。”
“……”
台球室本来不止他们几个人,其它两张台子上也有人在捅,老板除了摆球,还要照顾隔壁的电子游戏厅。
突然听到这张台上赌五块,还说可以往上加,顿时一个个都看了过来。
年轻人心神不定的看了黄轲一眼,刚才怎么看他的技术都很菜,说不定真是一个嫌钱少丢份的肥羊。
“赢了钱晚上请客烫火锅。”
正犹豫间,耳边听到一个鼓动的声音,年轻人的心顿时热烈起来。是啊,经历那么多大风大浪,难道会栽在两个学生手里,咱好歹是广场一支红杆啊。
“好,但是只让俩球,加到十块。”
“可以可以,咱们押钱吧。”
王大胆经常干这事,咋呼着把手一翻,从兜里掏出一张大团结,递给台老板。
等年轻人也给了十块钱后,黄轲才拿起杆子,顺便一脚踩在王大胆的脚背上,发出一声嚎叫。
年轻人开球有进,轮到黄轲打的时候,台子上已经少了两颗。
他第一枪没有打进,只差一点。
年轻人又打进去一颗,再轮到黄轲的时候,终于打进去了一颗,还是在洞口弹了几下才进的,然后就是失误。
接下来又轮到年轻人打了,而这时他只需要打进去俩颗就赢,王大胆紧张的看着白球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