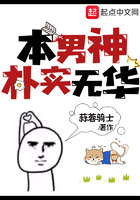我一眯竟然在这样十分恶心的洞穴里睡着!天哪真是服了自己的创举。不过,感觉这一眯也只是打了个盹吧,仍然头脑不灵光缺少脑细胞的活力素。这一切的发生和出现说实在的话好像不是我自己一个脑子在支配,宛若一只牵线的木偶被无形中的一根根绳子控制。我想自己再傻再笨这一辈子也只能傻逼一次,绝对不会再有下一回出现了。这样下意识的一番自我安慰和饶恕,一下子觉得自己的容忍度提高了不少非常庆幸!甚至那些臭烘烘的气味现在闻起来也不那么刺鼻和恶心习惯了这样恶劣的环境,无所谓行为付出的回报问题兴许感到更加可喜!
轮班下坑劳动的人马出现了。那只火把的照明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的通亮,隐隐约约有七八个人头攒动。我跟着最后一个人走了,好像前面的人巳经发觉我也没什么反应,反正各干各的事养成他们一种世态冷漠的人格!这里除了工钱以外的奢侈恐怕只有一天两顿饭的优劣问题比较关心。人的价值观意义就不计其内!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生活体现;活着似乎代表人生的全部贡献力更有了希望!我想坑道里干活的人,大部分应该是这样考虑。因为他们从未报怨过不乐意的情绪出来!
我一直默默不语尾随那队人马。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谁来接应我,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忐忑不安!要说不害怕和不担心告诉不懂事的小女孩马马虎虎。倘若稍微懂点知识的人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落后生产力,这样的不爱惜自己生存的环境,还有这样的麻木不堪的社群,要是说出来令人毛骨发颤。一会儿,从另外一个方向走出五个女性。火把的光照下看她们的年领并不是很大,目光呆板毫无年青的气色,却也找不到表情上的一点点痛苦和伤感!也许压力太大或者说巳经被苦难折磨的遍体鳞伤,所以,这么点艰难的日子算不了什么习以为常。我们被关进一艘乌蓬船上,有人撑着船离开岸边,没有划桨的声音因为水的响声很大,听起来都是溶洞的回壁音非常清脆容易去辨别。大约十几分钟的功夫船靠对岸了,舱门一开一个个人鱼贯而出。奇怪的事所有人竟然一点声响不发,甚至于呼吸都是一致屏息竭尽躲藏起来一般。因此周围的环境更加显得肃杀和凋敝。出了乌蓬船男队朝石手方向的洞穴走,女人朝左手的方向继续前行。分手之际我偷窥一下女队的方向,没有一个人回过头来望这边一下,微光之下整整齐齐往前踏步。不过机会就是那么十几秒间的事,过会儿连个人影也没了又是漆黑一团。
大概二十分钟的过程我们进入一个较大的洞穴平台。里面的微亮光线看得清前面的人影,但脸部仍然模糊不清。他们进了洞穴之后,各人知道自己的岗位在哪,没有人在这里吆喝指手划脚或者颐指气使!举火把的人大概就是领队的工头没有一点威望,手下的人也不会惹他倒是和平共处十分和谐!那些镐头和铁叉子等工具一律整排的靠在溶洞石壁上一目了然。我走过去随手正要拎一把铁锹,突然有人告诉我去那边帮忙推车就好。于是我和一个中年人负责把这些石渣推到三十米开外的一个下坡坎,然后卸载就行了。只谓下坡的那个鬼地方到底有多深多险黑不隆冬肉眼看不到,一个黑洞口呈现于面前好像永远填不满的大坑。这印象我的脑海中唯一可形容的就如宇宙的黑洞恰如其分,再也找不到如此具体的形象去比喻。几趟推车下来我巳经汗流夹背气喘吁吁。尤其是鼻孔感到特别的燥热,干巴巴要启了一层皮瘙痒感弥漫。这里的空气状况显然不同干燥而闷热氧分低很混蚀,呼吸起来有粉尘刺激压抑感倍增肺部受力很大,一会儿喉咙发干整个身体不适反应尤为迅速。我觉得一下子很渴喉咙里要冒火了。可是,找不到可供饮水的地方心里十分着急!一起推车的中年人看出来了,回程中从兜里抽出一只塑料小瓶递给我说抿一口吧!我接过来拧开盖子仰头一大口咽下去。天哪我差一点要跪落地上求人饶命!这瓶里那是净水啊分明是一种劣质的酒精有异味很呛人又烧心!顿时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刃眼睁睁瞅着剖开我的心脏那么可憎可怕!那时候我的额头淋汗不止,人的知觉与情绪瞬间塌方脚步开始出现漂移,胸口反胃水直往上冒一股说不清的浓液十分悲惨!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在回程的一个火把点瘫软般坐下来歇息一会。要不然我真的玩笑开大了,一旦虚脱命丧黑云坑哪有人给我葬身立碑呢?唯一可怜的是在焚烧之前让紫珍多看我一眼伤心欲绝!只于我最爱的妻子厉云却永远活在冥世的回忆里相见多么残忍的写照!我愈想愈发害怕。开始憎恨那个土郎中口出诳语难道这个坑人的常理不懂,非要骗我下矿底去体验一回拿我的命去做下赌注居心何在!我闭上眼休息一下,困顿于这混沌口般的氛围里哪里敢轻易睡去,万一醒不过来一切咒怨如愿得偿我才不会那样愚蠢透顶。我一忖度还是站立起来靠在洞壁上。我不得不自嘲一番谁叫我自告奋勇承担责任呢?像阿力说我们巳经完成任务,阿雄见不到不是我们的错是设计者脑残,把活人设置为死鬼来演绎死人设置成活靶去瞎推沙盘不是咱们的错!这样的游戏上帝即使派出十八骑士也不一定玩得转,何况我们是凡夫俗子呢?
午饭时有人送过来一桶稀薄的粥水馒头和咸菜。我喝了四碗粥水算是捞回来一条小命应该说值得庆幸!
有人搭着我,低道:“兄弟馒头多少吃一点点。要不然回去的话,你连路也走不动。”
我摇一摇头回:“放心走不回去的话,我一定想办法让自己做只狗也要爬回去嘿嘿!”我笑了。这时候人不会幽默点真的死了也会更加痛快!
那人拍拍我的肩示意跟他走。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和条件既然来了,在这里任何决定都是任人宰割巳经笃定得死死!那人信手摘下石壁上火把带路,我随他走了两个拐角的地方在一个黑洞口前停下。这时黑洞里一个男人讲,说自己就是吴天雄。我听那个声音大概是个四十来岁的人自称是阿雄。没错他是这样告诉我,当时我头脑特别清醒。还有一个女的声音她自称是阿雄的妹妹吴天莱。这两个名字如雷贯耳我再熟悉不过了。最后吴天雄告诉我,以后的联系由他妹妹出面并祝贺我这次初战告捷。我本来想询问几个重大的疑点心里早早准备好了。可是他们不给我这次机会!那人容不下自己去表现一点多疑的语气告诉我结束了。只好又跟着举火把的人回到施工现场;环顾一下所有人没正视过我一眼,就这样发生就这样宣告结束,就这样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完成神圣的使命。对,完成一个举世瞩目的神圣使命你会理解吗?浑浑噩噩你会懂了吗?天底下的大笑话莫过于如此夸张之大耳!
等我跟随他们收工回去巳是饥肠辘辘。那个在坑道里劝我多吃一个馒头的工人说的很有道理,回去的话会饿的我连路也走不动。现在我坚信他的话不亚于谶语与箴言!此时,我饥渴难耐疲惫不堪小腿肚肌肉颤抖不停。是的这不单单是肉体上的折磨那样痛苦不堪而是心灵的一次摧残。荒唐!觉得自己太那个荒诞不经可笑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