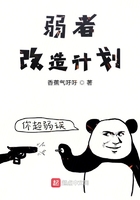听画家如此说,我只能去美国找他了,可是还要申请护照,到黑市上去兑换美元,一应事情搞下来,起码得半个多月,既然到了北京,不如先坐飞机去西海乌尔市生命研究公司看看。到底有何神圣,能否解除我这突现的幻境,以及后面噩梦成真的事情。我已经不忍再看下去。
绕过北京城楼,一胡同老墙根下见一位白发老人竖一个看相算命招牌,价钱倒不贵,五十元一算,认为说得不准可以倒付五十元,北京人都尊老爱幼,夸下如此海口,也倒没有寻事的,我眼见一个人算完,面色不怎么高兴,放下五十元,还想让老头再说说,老头摆摆手,示意他可以走了,说多了无益,然后低头看自己的书。
见如此的情态,看来这人应该是个高人,便也想算算最近的运势,怎么老是看见一些不洁净的场景,也就是不是正能量的东西,看能不能驱除,另外也想知道自己生世的来龙去脉,从西安骊山脚下秦皇陵附近的山洞里爬出来的孩子,是盗墓贼的孩子还是弃婴…….总得有个出处吧!那孙猴子也还有个出处是石头长成的天地生胎儿。
恭恭敬敬的呈放在那张木桌上一百元钱,算命的抬起头来,目光灼灼的看了一会儿我,却把钱推还给我。
我有些傻眼,以为老头懒得找钱,忙解释道,“请给我算算运势、命程。两项一起一百元。”
“你跟我们不是一类人。”老头一下子眼睛凛然,语气冷冽,“你命里无长短,至于运势,不是我这种俗人能预言的。”
“命里无长短,啥意思?”我瞪大眼睛,心里狂跳,听人算命的,要是命相太差都不收钱不愿意算,难道我已经是无药可救,命悬一线了。
老头看我紧张起来,抬抬手示意我坐下,语气依然严肃道,“你从大山里来的,曾身披磷甲,能见常人不见之景象,你命已然很长,过于久远,我推算不出你生于何时,当然也就推算不出你归于何时,所以这钱我不能收。”
一听这‘从大山里来的。’我心里就有了数,看来这老头还挺准的,于是把我父母捡到我时是1990年,当时的我大概三岁左右的样子,那么我就是1993年出生,身着短袖,必是盛夏,那就是七月,月圆时分,于是报上,“我生于1993年7月15日。”
“先生,您说笑了。七月半,鬼节,鬼无磷,只有魂,黑鳞皆有蛇龟神兽,无人能知其年轮长短。”老人捋须,轻摇羽扇,闭目沉吟。
我寻思这老头言语不怀好意,那是再拐着弯的说我是兽类,我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但是我还是忍住心中怒气,听他继续言语。
“你别误会。”老头仿佛知道我用眼睛瞪他,继续闭目道:“《山海经》中曾述蛇国人,生有磷纹,后而褪之,老朽认为你应该算是他们的后裔,年龄长者可达九百年,彭祖便是蛇国人。秦始皇当年曾四处寻找其坟墓,以求长生不老之术。人过一百岁后就可以进入新的一次元,以次渐近……..所谓人老成精,树老有灵,你有预知未来之幻境,那就说明你已经有长生之术了。”
“那我为什么不是看见美好的前景,而是些死亡之魂,山崩地陷,火海洪水…….”我寻思这老头也非常人,言中八九,也就把我之所见尽数告知。
“生从何来?死又何去?人与天地皆轮回,你现在先看到的死,那么后就会看到生。”老头睁开眼睛,开始跟我说些之乎者也的话。
“那么说我现在的状况还在死中,当然也就看到死的幻境了。”我略微思索了一下,顿然醒悟。
“聪明。”听得出老头是由衷的赞叹,“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死景,直到遇见解惑的人,便有了活景出现。”
“那我该去何处寻找解惑人?”我心有一线希望。
“这得随缘,”老头双眼炯炯有神,不似在欺骗我。
我想到来到北京满以为可以找到同类之人,一起探索,可如今他已远去美国。
“向西边去寻,以前蛇国人大多西进,因为那里山高林密,他们大多在那里生存。你可以去那里再打听。”老头说完,昂首看了看空的余晖,开始站起身来收摊,并把我给他的放在桌子上的一百元钱装进了口袋里,“这一百元钱,虽然没说出你的命理,但陪你说了这长时间的话,算是聊天费这该收此钱。”
“那是,那是,耽误你好一会儿,应该收,应该收。”我忙恭恭敬敬的答道,脸上堆满了笑容。
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我这才沿着北京广阔的马路行走,两边梧桐树高耸入云,我顾不上看沿途的风景,边走边想,“西边,西边,那西海乌尔市生命科学研究公司不就在西边吗?这与我初开始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管那么多,先找个地方歇息下来,明天就去西海乌尔市。”
躺在小旅馆,我还在翻来覆去的像老头的话,我是蛇国人不假,我的养父母也是,而他们却是我的守护人,我们难道没有死透,只是在兑变,又从婴儿开始重生,可是我对自己的前世的事没有一点的记忆,婴儿都是从父母肚子里出生的,而我们却是地下爬出来的,而且是将近一岁的幼儿,我们是如何生存,真如那种黑甲虫喂养吗?而不是它们吃掉我们,这跟传说中的返老还童大不一样啊!想着这些违背生命规律的事,我都头痛,现在身强力壮的我居然对女人么有一点兴致,一点生理反应都没有,难道埋在地下时间太久,竟然失去了欲望,想起在京梦城与同事一起去KTV ,有艳若桃李、美若天仙的小姐撩拨,我却心如止水,跟个傻子似的毫不动心,同事都说我心里有问题,身体有缺陷,可是体检报告的我,并非缺心少肺,一切正常。
飞机到达乌尔赶市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问了很多出租车司机,竟然都不知道有这个生命研究所,幸好,我包里还存着那张报纸,我把报上的地址给出租司机看,“愚山乡白村。这个我知道,不过路程很远,路也是崎岖山路,很难走,得五百元,返程根本就没有客人。”这个四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摆明是一副爱去不去,那不在乎样子。“好吧。”我心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这个公司到底能有多大的能耐给我解惑。
出租车半个小时就离开了宽敞的大道,进入了那倒也是柏油路,可是却满是盘山沟底的公路,满眼都是厚密的植被,绕老绕去的,眼睛都绿晃晃的。最后终于在山中一所高楼的院子前停了下来。
付完的士费,我回头就听见院子里有吵吵声,仔细一看,院子的中央停着一架有办公桌那么大的一个无人侦查机,这玩意我在京梦的见人玩过,不过那很小,有遥控器操作,这架无人机恐怕得卫星操控了,这是我目前看见的最大的。
不过这架无人机好像是受过伤似的,浑身斑驳陆离,羽翼都扭曲得变了形,有三男一女正面朝向我这边看那玩意,每个人的表情都很讶异。
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到来,偌大的楼房连个看门的也没有,我看他们中间有一个像是我高中同学李阳明,这小子后来读了生物工程学的,不会分到这里来了,可是听说生物工程的学程比医生还长,最少六年才毕业,可是这人分明就是,于是,我试着大喊了一声,“李阳明,我是秦山源。”
所有人都抬头看向我,果然是他,只见他和身边的一个中年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满脸微笑的朝门口跑过来
我记得大学毕业后,有一次在西安同学集会,这家伙还蛮胖的,行动迟缓,没想到五年不见,如今跑起来身姿矫健,行动利落。心里不由感慨,这生命科学研究所还真能改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