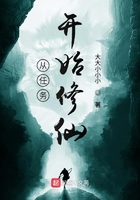巴金先生在获得官方送给他“人民作家”的尊号中度过了百岁诞辰。
“人民作家”照说应是被高度尊敬的一种称号,但“人民”什么的我们总感到听得滥了,好像有点说不出的味道,有点不大对劲,仿佛还欠缺了一点什么。
翻开巴金晚年扛鼎之作的《随想录》,在最后一集的《无题集》中,第一百九十五篇的题目是《“文革”博物馆》。官方所欠缺的,就正是这一座“文革”博物馆了。
在上一个世纪的下半叶,使中国人民最创巨痛深的就是“文革”。巴金晚年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建立现代文学馆,一个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现代文学馆得到官方的支持建立起来了,而“文革”博物馆却因为官方的冷淡对待,至今毫无影子,只是听说巴金家乡的成都,有一位草野小民建立了一座小小的私人的“文革”博物馆,私人的力量总有限,它的简陋可想而知。官方不支持,这座私人“文革”博物馆恐怕就充实不起来,支持不下去。
官方的不支持,是不是显得他们是有愧于人呢?反“文革”而不力,不愿揭“文革”的罪恶,撇开了历史的伤痕,使人们警惕不足,忽视灾祸重演?既然还知道尊敬巴金是“人民作家”,就应该实现他代表人民发出的呼声,了却人民心头的一大愿望才是。
巴金的《随想录》也受过一点小小的“文革”之祸,而且还殃及到鲁迅。一九九一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巴金写了一篇《悼念鲁迅先生》,同时在《收获》和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大公报》发表出来的是被删改了的文章。“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为什么会这样?据说在那时不久之前,北京的外办(当时香港工作的北京领导)有话传下来,中央指示有关“文革”的东西要少登。副刊的编辑们作不了主,由总编辑亲自动手删改了巴金的文章,文章被改得使人啼笑皆非。
巴金不知原委,气得要下决心不写了,后来总算改变了主意,否则这五集的《随想录》就不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要半途而废。
巴金在后来紧接着写了一篇《鹰的歌》。他记起了在高尔基的小说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高尔基赞它说:“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巴金说,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我也会滚下海去的吧。
巴金用《鹰的歌》抒发他的愤懑。这篇作品并没有在《大公报》上他的《随想录》中登出来,登出的只是文章的题目和作者的名字,其他是空白,就是所谓的“开天窗”。《真话集》出书时也是有题无文。直到《随想录》五集的合订本出版,《鹰的歌》才有题有文和读者见面。
这可以说是“文革”对巴金一点小小的遗祸吧。
“人民作家”的巴金,为人民作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人民政府能置若罔闻、长此不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