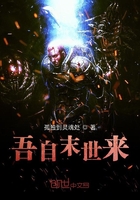初见
这两把琴,传到震哥儿手里,已经是第五代了。
对于一把小提琴来说,完美的音色需要经过时间的打磨,而它的木质也给了它经受时间洗礼的体质——使用的频度越高,它的降解速度就越慢,经过四代艺术家的调教,这两把琴刚刚达到它们的壮年,无论是音质还是演奏的舒适度,都臻于完美。
这两把琴,高祖辈的老琴师本是要传给儿女中最有天赋的一男一女的,但这一脉庶支不盛,到了震哥儿的祖父这一辈,竟成了三代单传,于是这琴就成了鸳鸯琴,小伙子把空出来的那一把作为定情物,送给心爱的姑娘。而这两把琴,经过这许多年的耳鬓厮磨,也像是两小无猜的少男少女互生情愫一般,借着演奏的机会互相赞美,互表爱慕,呢呢喃喃地说些它们之间才能明白的体己话儿,而且百听不厌。而琴的主人们呢,虽然都算不上一流的演奏家,却也能平平静静地厮守一生。
震哥儿天分高明,不但对音乐的领悟力好,更难得他手指细长灵活,祖父最疼,说他不知比他父亲聪明多少倍,几乎是把成名成家的希望押宝一般押在了这孩子身上。小震也是个听话的,愿意练琴,于是这家里头整日价儿回荡着老家伙说曲儿和小家伙唱谱的声音、一老一小你来我往切磋技艺的琴声和他们的笑声。
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一座三进三出的院子里,家里人少,就把空出来的屋子给租出去几间,倒也不是图这几个租金,难得的是这股子暖和和的烟火气。租他们房子的都是些小家庭,夫妻二人带着一两个孩子,震哥儿这个会拉琴还不淘气的家伙就成了一众顽童的“公敌”,谁愿意让老爸老妈整日价儿拿这么个“风雅人物儿”压自己一头呢?
在他们住的屋子隔壁,也有一个落单的小家伙,是个叫幼安的小丫头子,比震哥儿小了四岁。孩子们给她取了个诨号叫“豆腐脑儿”,本来也跟着大伙儿疯,但是一个不留神她就喘得跟拉风箱似的,做父母的就让她的玩伴们别让她玩得太忘乎所以,结果大家都玩不尽兴,一而再再而三,没人原意跟她玩了。
家里人虽然成功地把安丫头圈在了屋里,可她依然是一到晚上就拼命咳嗽,咳得只能坐在床上,要是躺下,她就连气也喘不过来了,去医院也看不出什么关目山来。晚上睡不成,那白天她就得补补觉,好死不死震哥儿要练琴。一个困得眼皮直打架,一个在隔壁吱吱呀呀地拉琴,把个安丫头气得眼泪都下来了。小安丫头也不是个没人疼的,她家老爷子就去找隔壁老爷子商量怎么办,但是来来去去好几次都没个结果。终于小病猫儿忍无可忍,趁着两个老头儿出去遛鸟的当儿,自己去找那个拉琴的讨厌鬼理论去了。
本来呢,那一个怪这一个大白天睡懒觉,这一个怪那一个不让人好好睡觉,都讨厌对方耽误自己正事儿,这一见面两个都成了乌眼鸡,拉好架势要把面前这个讨厌鬼啄趴下。可是小安一着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好看着这个大块头干瞪眼。小震呢,等着对方出招,等了半天也没个动静,自己倒先没主意了,只好讪讪地开了腔:“你——说句话呀?”小安本来是来叫阵的,结果还是人家先开口,这个脸可不是丢到外国去了么!她想赶紧说点儿硬气话,好把面子找补回来,可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急得她哇的一声就哭了。这下小震更不知如何是好了——明明是她先找的茬儿,怎么弄得像是自己欺负她似的!这可完了,谁哭谁有理呀,老头回来没法交代了!这会儿他也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了,先哄她不哭再说。他连忙赔不是,左一个好妹妹右一个乖妹妹一叠声儿地叫唤,鞠躬作揖点头哈腰,尽“平生之所学”把大人教的电视上学的所有礼数全施了一遍。小安一开始还哭得抽抽搭搭的,后来就看耍猴儿似的盯着他。突然,小安终于“金口开言”了:
“你这揖作得不对!”
“我这是电视上学来的,怎么不对了?”
“你是男的,应该左手在外嘛。”
“谁说的?”
“我们老爷子告我的。”
“那你们女的是右手在外了?”
“女的不作揖,女的道万福,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是哥哥哪!”说着把头往另一边一扬,一副你不佩服我都不行的模样。
震哥儿也不认怂,抓起他的宝贝小提琴就架上了肩膀:“你会这个吗?你听过的歌,我都会拉,随便点一首吧!”
这时候我们的幼安小朋友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来干嘛的了,真就让他拉了妈妈给自己唱的那首催眠曲,而她的小哥哥心里那股得意劲儿已经快让他飞上天了!
等到两位老爷子遛完鸟回来一看,这两个冤家已经相互拜了师徒,又在互相赔不是,真正是黄鹰儿抓住了鹞子脚,分都分不开了!
志愿
震哥儿的琴,从四分之一换到二分之一,又换到四分之三,又换到了全长,终于在上大学之前拿到了那把家传的小提琴,就这么换来换去,十年的工夫就过去了。这十年里,老宅子给拆了,家搬到了楼上,大院里的小恶魔们也大都不知去向,但是他跟他的小冤家并没有离太远,两家在一前一后两座公寓楼里头,有什么事儿,脖子伸长些儿高声一喊就能应。他也常去对面走动,但是小安却不常过这边来——她这咳嗽的毛病总也没好过。有咳疾的人,心肺功能都不会好,让她这么一来一去爬上爬下,着实是难为她。
尽管从小就被寄托了成为演奏家的期望,他最终却选择了医科——原因不用说了。填完志愿,他就过那边去了。
他去的时候,小安面朝里躺在床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像是在哭又不敢出声的样子。
“又发傻了?”他走过去坐到床沿上,想把她扳过来。
她在枕头上蹭蹭脸,吸吸鼻子,好容易坐起来,还装得若无其事似的:“你报完了?看来一个伟大的小提琴家就要横空出世了!”
“我报的是——西医临床。”
她一下子坐正了:“谁叫的?”
“我自己。”
“去改掉,不然你肯定会后悔的。”
“我才不会后悔呢!我告诉你啊,我报的还不是一般的医学院呢,我报的是军医大学,你不就在人家的附属医院看病的吗?你看这多好啊。另外呢,几个月头里就签协议了,没得反悔的!你为什么说我会后悔呀?不会是怕我把手术刀当琴弓子吧?”
“我是怕你还没学成,我就死了,那你可不是要郁闷死……”不等她说完,哥哥就不轻不重给了她一耳刮子:“你再胡吣?小丫头子嘴里越发没个忌讳了!不就是咳嗽几声吗,哪里就由着你死啊活的乱说了?再说你别自作多情了,我哪里是为你的?我是为了我自己能多活几天的!我要是什么都不懂,全听你自己乱猜疑,早晚被你活活吓死!”
“我不过随口开句玩笑,你就夹七夹八扯上这么些,以后我不说话了还不行吗?”
“你不说话才好呢,一张嘴就是些没营养的东西。你随口一说,就不想想听的人心里是不是个滋味儿?”
“我说我自己你也管呢?你怕晦气,你就离我远些,自己长命百岁去,我横竖不关你事,我今儿就死了才好呢,省得这么不死不活的杵在人家眼睛头里,没得讨人厌的!”
“又是谁踩着你尾巴了?你可别在家里大人跟前乱说,就你刚才这几句,听在他们耳朵里那可要命的!”
“他们怕不是要我立时三刻死在他们跟前儿才好呢!”
哥哥忙不迭捂住了她的嘴:“你可再别说这种话了。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你这个小心眼子里那点想头,我不知道?无非是他们抱怨几句,你听着不受用了。说几句怎么着了?衣食药饮也没克扣你的,他们十有八九是着急,是疼你呢!”
“说我是讨债鬼,也是疼我的?一天天的在我跟前儿抱怨药费开销大,老是问大夫哪种药可以蠲了,也是疼我的?你也不用这么教育小孩子似的拿话怄我,我就知道你肯定说我多心,就算是我想多了,可我想也总想得有个缘由,我这么个样子,那也不是我愿意这样的,老是这样,还不如尽早有个了局呢,这叫及时止损,大家干净!”
“你还说滑嘴儿了?行行行!”他顺手拿支笔,在小安手腕子上划了一道:“这是脉搏的位置,切要切到两公分以下才有效果;还有,你家住六楼,从你的窗户跳下去,保证你心想事成,不过跳之前先看看有人没有,别伤及无辜,别吓到小孩子——满意了?”
他没等话说完就一步跨到了书桌旁边,成功地躲开了小安砸过来的枕头。
后来志愿当然没改,于是小安就多了一项爱好——看医学散文,从葛文德看到卡拉尼什,然后把书中探讨的各种问题拿出来问他,他要是答不出来,就被冠以“神医”、“名医”、“国医”等等各种名号。她还时不时跟他说自己出现了哪些异常,让他给诊断诊断,头几次他都信以为真,吓得浑身炸毛,一阵忙乱之后得到的却是她“阴谋得逞”一般的奸笑,后来他就给出“标准答案”:“有问题去看医生,别来刁难医学生!”可这样子她的嘲笑就变本加厉:“大夫,我看你拉琴比看病在行!”
四年以后,选专业这个事情就轮到她自己了。她在医学和文学两大选择面前举棋不定,哥哥给她筹划道:“你就别步我的后尘了。一来你们老爷子一直就指望你们这一辈能有个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去,你几个哥哥一个都没听他的,你是最后一个,别让他失望。二来我们这班学医的腿子,十停人里倒有七停会有疑病症,有的严重的还会有某种程度的癔症,你都不用学医就够叫人烦的了,我看你就让人省省心吧。”她急忙分辩:“我没有疑病症,那些都是我编故事逗你玩儿的!”“那你这么喜欢编故事,为什么不选这个能让你天天编故事的专业?”“我不用学都这么会编故事了,要是再去专门学,你可不得每天被我忽悠得团团转吗?”她不说这话也就罢了,一说到这个,震哥儿立马使出平生气力给了她一个大白眼:“就你在书上看到的几句熟话儿,小鹦鹉似的学舌学给我听,打量我不知道是怎么着?也就是你吧,换了第二个,你看我不把他剥得血淋淋的呢!怕你面子上过不去不给你拆穿了,你倒拿我的客气当你自家本事了!小傻东西,一些儿眼力见儿都没有!你就去仔细学吧,把谎撒圆了再来作弄我!”
“抵债”
震哥儿在本科的时候,最怕别人把他看成“专业人士”,尤其怕小安对他投来“崇拜的眼光”然后拿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来让他自叹无能。可是等到小安被他连哄带骗诓去学文学之后,他就把小安当成了无所不能的文案高手。他本身是没有什么要写的东西,但他高中时代的铁哥们儿是做新传的,小安上大学的那一年,这个“新传哥们”已经考上硕士,并且有一个相当严厉的校外导师,次次作业都被老师训话,所以经常找小震倒苦水儿。震哥儿不忍心好朋友次次灰头土脸铩羽而归,就大包大揽道:“我妹妹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就你这点小文案,我家那位保证手到病除!”哥们一听感激不尽,连忙拜托令妹多费心。没想到他刚一跟小安说,就把她气得直跳脚:“你答应人家的,那你自己诹去,跟我什么相干?我连我专业的门槛子都没摸到呢,写你个大头鬼!”震哥儿只好对着手机屏幕打躬作揖,百般讨好,还许诺等她放假给她一个惊喜。她一听说有礼物,就在心里暗暗盘算要敲他一竹杠,但还是装作百般为难,只答应试一试。哥哥一听这边松口了,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陪上了几百声好妹妹。
小安写作的手笔都是正儿八经的“老干部风”,这种风格很对那位老师的胃口。震哥儿的兄弟终于不用挨批了,兴奋之下在小震面前把他这位“令妹”大大地夸赞一番,把个震哥儿夸得飘飘忽忽,干脆表示每一篇文案都可以给我们的“枪手安”润色修改。小安得知自己就这么被当成了两个哥们儿之间“联络感情的桥梁”,是又得意又生气。得意的是新传硕士都搞不定的东西,她三下五除二给解决了;生气的是,自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给人做了佃工,然而那个受助者还觉得理所当然!不过一想到哥哥许诺的那个礼物,她又满心期待了。
终于来到了第一个寒假。小安把一应粗重物件都邮寄回去,自己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就回家了。到了家,先问候过老爷子老太太,后又去和几位伯父伯母一一厮见过,互相问了几句寒热话儿,就直奔震哥儿这边来了——一学期下来她经手的文案不下十篇,几乎每一篇她都被那位“鸿硕之士”文不从字不顺的大作气得哭笑不得,然而那个坏哥哥许诺的礼物从来没出现过,她是专门去找那厮算账的。
“大夫好啊,给您请安!”小安一只脚刚进门阴阳怪气地打了个招呼。
震哥儿正鼻子朝墙愣出了神儿,两只手绞过来扭过去,好像很紧张,小安高八度的招呼把他吓了个激灵,不过很快他就定下神儿,脸上不由自主地绽出笑容:“你这么快就过这边来了?”
小安扬扬眉毛:“大夫,我给你下个诊断,你有‘选择性健忘症’!口口声声答应给我的礼物呢?你可是给我画了半年的饼啊,是不是也该给我些饼渣子解解馋哪?”
震哥儿看起来更紧张了,连嘴唇都有些哆嗦。
他这样子倒把小安弄得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笑道:“不至于吧?说话不算数是不对,可我又不吃了你,你看你吓得,脸红得猴屁股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平日里怎么欺负你了呢!没有礼物就没有礼物吧,我就暗暗地生你一个月的气得了!”
震哥儿动动嘴唇但没说话,而是嚯一下跳起来去捧出一个樟木盒子来,拿在手上看了几秒好像想打开,但最后还是把盒子放在了她面前:“你自己打开看吧。”
这个盒子小安见过,所以她都不用看就知道里面是什么。震哥儿从几年前就有意无意地提过他家这两把琴的来历,这半年来更是时时事事都能扯到它们身上去,不过都被她拿话儿混过去了。她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哪里还敢想这些事情。她不但不愿意想,还不想让小震存下这个心思,没想到他今儿直接把这牢什古子请出来了。小安勉强笑道:“怪道刚才那么紧张呢,原来是要拿传家的宝贝来抵我的债了!快别胡闹了,赶明儿你老府君知道了,可不得打折你的狗腿子呢!”
“你真不知道这把琴什么意思?”
“你真不知道我这话什么意思?”
“这东西早晚得交给你,早一天交给你,我早一天放心。”
小安做了个拉琴的动作:“这拉琴的祖师爷没赏我这碗饭吃,你交给我是要让它白放着几十年吗?那这东西可不得毁了?”
“你不是喜欢玩乐器吗?又不要你登台表演,你多玩玩,它就不会坏了。”
“那也配不上,你才多大的人,哪里就发愁找不到这琴的女主人了?何苦在这里拿我醒脾!你要再浑说,以后我可再不敢上你家这门了。”
“你也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这么些年,我要不知道你狗肚子里那二两鸡油,我也是白过了。别的话我也不说了,我就告诉你,这东西给你,也是它们上一任主人的意思,喜欢就带走吧——我知道你不会不喜欢的。太远的事情你也不用去想,因为我都想过。我只有一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我本来就是做医生的,就你这点小问题,我还对付不来?”
小安不置可否地笑笑:“你觉得林妹妹要是没那些个病病灾灾的,还会有宝姐姐的戏份儿吗?”
“可是这里又没有宝姐姐,再说,你还想跟林颦儿比?你也比不上啊,颦儿要像你这么贫嘴儿拔舌的,宝玉只怕早把她的嘴给撕烂了!四年前你跟我说的那一番话,我可是记得刻骨铭心,一想到我就浑身来气,你呀,就欠一顿好打!”
尾声
那把琴后来是这么处理的:她“代为保管”,如果有一天震哥儿“痛改前非”想要把它送给更合适的人,那她完璧归赵——这个“折中方案”好像很滑稽,却把哥哥心里弄得酸甜苦辣不知道什么滋味儿。
两年过去了,震哥儿做了她主治大夫的学生。老教授几乎是看着小安长大的,但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两个小鬼之间有这么一段公案,后来也只有那么一次,小安去复诊的时候刚好轮到小震去见习,因为对这个“病例”太熟悉了,他就没有全神贯注听老师介绍情况,老太太不满地敲敲桌子,小安忍不住笑了场,悄悄地跟他比口型:“你也有今天呢!”震哥儿当着老师的面不敢造次,只好拿眼瞪她。他们在那儿偷偷地挤眉弄眼,事后老师自然是免不了要来一顿口头教育,他趁机和盘托出,老师既没有很惊奇,也没有很生气,只是告诫他业务上要专心,训诫两句就放他走了。
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师特意安排的,总之他们再也没在诊室里打过照面,但是老太太私下里会让小震给安丫头转告一些注意事项。
这所大学有个传统,就是会分批派遣医生跟随维和部队一起,去非洲进行人道主义卫生援助,特别是在当地有疫情或者战事的时候。
还没到她去复诊的日子,大夫就传了口信叫她去一趟,还说不用挂号直接进去。
上次她听见大夫悄悄地跟学生说,她的心室比正常的要大一些。从严重咳喘到心肺病——她最终没能逃得脱。久病成医,她早就知道这一步意味着什么了,只是她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现在不过是捱日子罢了,她对死亡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那么害怕——要不然她也不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说出那么一番诛心的话来。但她当时对亲人的误解已经消除了,现在她考虑更多的是,这件事要怎么说才能不那么突兀,不吓到年高的老祖母,也不要让父母对未来过于绝望,他们还要生活下去的呀。
诊室里的气氛跟她想象的差不多——大夫表情严肃地等着她,这跟平常不一样,这位老教授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平时相当活泼,见了她总有一段轻松的开场白,完全不是今天这副模样。震哥儿居然也在,而且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看起来很焦灼。难道她的情况比她想的还要坏吗?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夫跟前的椅子上,却觉得自己的三魂七魄已经飞得影子都找不着了。
“今天叫你来呢——小安?”
老教授清清嗓子唤了她一声,她被吓得浑身一哆嗦。
大夫看看小震,又回过头来:“你哥哥要出趟差,可能这几天就动身。”
“去哪儿?”她习惯性地问了一句,其实并不期待什么不寻常的答案。
老教授顿了一顿,才说:“非洲某国发生内战,你哥哥被派到那里去,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一共——要去九个月。”
小安半晌没答话,只是狠狠地用指甲抠着桌子边沿掉了漆的木头,抠得木头上的毛刺都出来了。哥哥赶紧去掰开她的手。她出了口长气,好像是缓了一下。她仰起头来,喉咙蠕动了几下,像是有话要说,但只是嘴唇剧烈地颤抖,眼泪一串串地滚下来,一口气却一直憋着。哥哥来抱她,她扑在哥哥怀里,猛烈地抽泣起来,虽然她竭力克制,却一直哭到干呕。
他出发之后,小安的生活节奏倒也没多大变化,上课、下课、看书、练琴。只是她总觉得这琴声似乎比从前更悦耳些,似乎是小提琴自己在歌唱,而这琴声又像是和她自己的心率有着某种和谐之处——穷愁之音易好,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
她就这样过了将近半年。他一共在外面九个月,现在三分之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平安无事,她暗暗庆幸。而她自身也没什么大不妥之处,不过时常有些气闷,捶捶胸口歇上一会子也就过去了。而她每天辛苦练习的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小提琴曲的第二首,准备等他回来跟他炫耀炫耀,也不愧对这把好琴。可是就在一个她一边练琴一边浮想联翩的下午,她的四根琴弦,随弓而断。
那天,有当地村民到小震他们的驻地去求助,说有人突发急病,小震和几个战友就出诊了,回来的路上遇袭。
半个月之后,几位年轻军医的骨灰盒送到家属手上,各路媒体都在大书特书这些年轻人在异国他乡是多么的无私和无畏,还会顺带提到,其中的哪一位还是家中的独子,似乎这样提一下,就能赚取更多的同情或者关注似的。但是,亲人们的悲哀,又有谁去真正关心了呢?
因为病情严重恶化,小安没能参加葬礼,不久之后就被切开喉管插上了呼吸机。她几次偷偷扔掉面罩,结果病房里的各种警报器顿时一起尖叫起来,赶过来的医生护士又七手八脚给她接上,后来干脆把她的手绑在床护栏上省得她作怪。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长褥疮。一开始只是清创,后来又说要截肢。父母明确表态,只要能让她活下去,怎样都行。
她的主治大夫仍然是那位老教授,她不想让这位慈祥的老祖母为难,但这是她最后的求助对象。她不止一次想要开口说出那个请求,却次次都泪如雨下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手术还是在病人家属的授意下照常准备,大夫在手术前一晚带着一支注射器和三支吗啡去了她床前。小安看见大夫和她手里的东西,慢慢地把头偏到了一边。她的两只手都被绑着,大夫默默地给她注射三支吗啡就离开了。
小安下葬之后,那把琴也物归原主,随后,小震那里,做父母的睹物思人,看见两把琴徒增伤悲,加之两个孩子都不在了,后继无人,就把这一双琴一起被卖给了一个乐器行。乐器行的老板视这两把百年老琴不啻珍宝,把它们重新按上弦,摆在店里最醒目的位置并且很快就被人买走。但是很快它们又都被退了回来——小安的那一把,分明是刚按好的新弦,却是只要碰到弓子就四弦齐断,而小震的那把琴,则只会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那是小提琴的悲鸣,为他不幸的爱人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