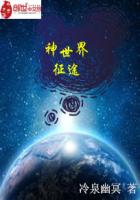这村子没什么特点,说他学贯古今兴是夸大其词了些,纵是学富五车也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可才思敏捷他也是担得起的。这样的他,想夸一夸这村子,也是难了些。不,难得不是一星半点,这村子唯一的特色就是真没什么特色,一个词来叫就是普通,和那大婶同样的普通,这就是那大婶引他来的地方,曾令他抱有极大兴趣的地方。大婶身上的血腥味甚至都失了味道,就在他和他的白马走到这路的尽头时,他似乎对什么失去了兴趣。到底是什么呢?他失去的到底是什么?
它看着男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担忧和恐惧同时攫住它的神经,令那神经随着心脏的调动一下一下紧缩着,甚至有越缩越紧的迹象。路的尽头从来都不是终点,那男人知道吗?那男人是否知道他要走的路?还是他只在这一刻迷失了?容它叹一声老天,不要让它的臆测成真,更不要让它的担心变为现实。老天!
它知道这老天全不了它任何一个梦,可总要有个能让它这样开诚布公的将情绪发泄出来的对象。此刻的它甚至已经看见了它今后的生活,它要死了。男人还活着,就活在那里,可它死了。它甚至想,在它死的时候将男人也杀掉好了。周围聚拢了好些村民,迎在前面的是四五个小孩子,活泼可爱,正是最讨人喜欢的年纪。可它却觉得周围的臭味更重了。它整个身体,整个思维,无论是对过往的追叙还是对未来的延伸,都充斥着臭味,它也要烂掉了似的。
当天夜里,朗月悬于西山之上,周身有星辰闪耀。它望着望着,这心思便被那群星蛊惑,失了对月亮的专注。它想,这月亮被星星困住了。男人悄声的走到它身边,刚放下筷子的手拍了拍它的大马头。
“可能得委屈你几天了,众目睽睽的,也不好一下子让你变成小木马。“男人有一下没一下的摸着它的耳朵,说这歉意的话!
它摆了一下头,似乎是在躲避他的碰触。它想:几天?几天又是几天呢?
男人看着它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只叮嘱道:“不可以调皮,吓坏了村里的人。“它合了眼,显出到此为止的意思。男人捏了一把它的耳朵,沉声道:“记得没?耍什么脾气?“
它迫不得已,打了个响鼻。心想:再不走,它可真的要耍脾气了。
男人叹了口气,隐隐能闻到晚饭的油腻味儿。它看着他转身离开,在他的背后也叹了口气。男人不懂它的惴惴不安,它却懂男人的隐隐动摇。这动摇不是你权衡利弊时的左右摆动,而是迷茫,是那种原地不动的迷茫,是那种仰望过后迷失在一低头的迷茫。它看见了,看的真切,看的无比的真切。真切的它全身发寒,腿也都的快站立不住,承不起它这一身皮肉,这是这么久以来,它第一次产生自我意识,这意识令它抑制不住的想变回小木马的形状。这意识太可怕了,这可怕不在于明日被发现的狼狈,而是它觉得自己在远离这个男人,他们之间缔结的契约快要失效了。这才是它真正怕的原因。
这一晚,它就那样趴在地上,地面泛上的寒气催着它的五脏六腑都要碎了。这一夜出乎寻常的慢,比它曾经独处的那许多日月都慢,比那年漫山凋零的寒冬还慢。那是一种要到尽头的慢,更是一种还不到尽头的慢。它想天亮了,应该就好了。可天还没有亮,人就已经先醒了。
被垂涎是一种什么感觉?它唯一觉得就是恶心,尤其是被母马垂涎,更是令它全身都不舒服。他们的眼睛里有它讨厌的杂质,曾经它被男人看到的那双眼睛,那是爽纯粹的眼睛,也许只有那双眼睛才能看见它。而今,这些围观它的人们,眼里的杂质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落尽它的眼里,成为一切恶心的源泉。
“天什么时候亮啊!“
它知道那些人看不见真正的它,他们唯一能看见的就是它那身月华下泛着银白色光芒的皮毛,他们甚至看不见它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里透彻的寒意,他们唯一想要的兴许不过是让它载着那些人从这出发,穿过自家家门,行到村口再返回,甚或有人不过当它是匹种马,能给他们家带来一匹同样健硕的小马驹。若那是看透了它才有的贪婪,那它也不会如此伤心吧。虽然它也清楚,真正拥有它的人,眼里的光是澄澈而坚毅的,那光同样的绚烂,却是不带任何侵略的感的舒适。可那双眼睛还在,而那眼里的光却不知还在不在。
太阳终于出来了。
当第一缕金色光芒严丝合缝的罩在它身上时,它像一匹穿了金色铠甲的战马,那时它才想起,这铠甲是它为太阳而穿的,太阳出来了,而欢呼的却是周围的村民们,它原就不该这样想的。太阳的光芒不顾让他们眼里的贪婪更甚,令它看的更清而已。这次他连企盼的机会都不再有了。
它看见男人从门内走出来,身上的书生气很浓,那是它不曾见过的曾经的他,闲庭信步的朝着它走来,好像昨日那个心急的男人从来都不是他。他将小白忘了。它真的很想叫喊着问他:“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可它喊不出来,它试了试,甭提悲壮的嘶喊了,就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了。它知道,是男人知道它要说什么,是男人不想听了。它是男人的自由意志幻化的产物,而如今,它被束缚了,或者是他被束缚了。它清楚的知道自己被男人束缚了,而男人呢?男人知不知道它被他束缚了?
他解开木桩上的缰绳,没有在第一时间骑上它的马背,只是这么牵着它,朝着村口走去。它知道这并不是男人想走了,不是因为它懂男人,而是因为没有哪家的待客之道会在客人离开时而不出门相送。相反,这证明男人一时半会离不开了,长久的停留才会造就此时的相安。你看,太阳出来了,却也将它最不想要的推到了它的面前。它的金色铠甲却慢慢失效了,它只有那一身白色毛皮。
“小白,我想,我,我想在这停留一段时间。“
昨夜的几天,几日的一段时间,一张嘴开合间,时间就消失了。随着时间,它也要消失了。它想告诉男人,它要消失了,不是危言耸听。可它依旧不被允许开口。
“小白,你不知道,这里的人没有读过书,他们对知识很向往,他们对有学问的人更是很崇敬。这里的孩子没有书读,他们还这么小,却似乎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将来。“
它知道他要说什么,昨夜,它思绪最乱却也最清晰时就在想,什么能让那个男人放下如今握在手心里的东西呢?那就是再让他拿起另一样东西。而这件东西一定是他在意的,甚至他觉得是同等重要的。可其实,有些事只有他可以,而有些事却是谁都可以的。今日,即便不是他,随便一位先生,在这里都能得到他受的待遇,随便一位先生也都能交这里的孩子。可只有他拥有一匹矫健的白色马儿,只有他闻见了那血腥味儿。如今或许应该说,曾经他有一匹矫健的白马,曾经他闻的见旁人都闻不到的血腥味儿。无论是哪一样,似乎都被那一缕金色光芒所撕裂,站在昨日那个自己的对立面上,却又觉得那个自己与如今的自己只不过咫尺的距离,这真是个骗局,自欺欺人的骗局。而如今他和它便现在这骗局里,兴许再也没了逃脱的机会。
“小白,你,我知道你听懂了。“
它心想,我早在你说之前就已经听懂了。
“小白,你,我想知道你,怎么想?“
怎么想?我怎么想有用吗?
“你这样,令我很不安!“
不安?那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不安?
“你会不会离开?“
离开?究竟是谁要离开谁?
“你倒是说话呀!“
说话?若是你真的想听,我怎么会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那你想我怎么办?“
我不想你怎么办,是你自己要怎么办。
“我,我也没办法,你没见昨晚他们说让我留下时,他们那,那表情,我不知道怎么,我说不清,没法诉诸于口,就是那样的感觉,令人心里沉甸甸的。你懂吗?“
懂?应该是不懂,竟然意外的也不想懂。
“我得留在这!小白!“
你不是已经做了决定吗?说的好像这会儿才决定似的。
“小白?“
它甩开他牵着缰绳的手,独自往回走,它身上金色的光芒退尽了,它的金色铠甲散了,它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正午感到了多年前那群山凋敝的凄惶与凛冽。
“小白?哎,小白!“
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他欣喜的道:“小白,我就知道你是懂我的。“
懂你?我并不想懂你,而你肯定不懂我。
他有些气喘吁吁的追上它,伸手拽过缰绳,并肩和它走在一起。
“等过一段时间,咱们就可以走了,你信我!!“
信?它是不信的!却也是该信的时候!它见过山下谈情说爱的年轻男女,男孩子一旦和其他哪个姑娘走的近些,女孩子总是说我信你,却会在背后像侦探一样将男人的一切活动摸清。它觉得,把相信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已经将怀疑根植在心里了。'我信'不过是为了让你相信我相信而已,就是这样的,如今的它和男人就是这样的。你看男人现在就信了不是!你肯定一件事是为了肯定想肯定这件事的人,而不是这件事本身,而这个肯定本身就是个谎言,是你的,也是被肯定者本身的。从此你们共同拥有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本身却具有最正直的品格,却是人失去他们本自拥有的品格,因为没有哪个品格是被懦弱胆小的人拥有的。
男人在拴着它的门前开了课。小孩子一个个活泼的紧,更拥有可匹敌初升太阳的朝气,除了炫目它唯二能想到的词只有刺眼。它站在他们的后面,看见一种类似希望的东西从那小小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笼罩在不远处站着的孩子的父母身上。然后这希望被太阳光曝晒,变成一丝丝透明的线,将不远处讲台上的他捆绑的匝实极了。然后它们慢慢的像生了根似的,朝着地下生长,想将他绑缚在这里。它看的太分明了,这是太阳的圈套,可那男人却钻的义无反顾。原因?原因自然是因为眼前的这群孩子。这么说似乎也不对,远远不只这些孩子,还有这些孩子的父母,当父母与孩子站在一起时,就像蛹和蝉并在眼前一样,你只,它们将有多想象,或可说孩子完全复制了父母的路。是如今这极端对立却会在将来达到高度统一的落差感令他义无反顾。可他忘了,这片大地上不只这一群孩子,这片大地上更不只这些孩子。
它想要自行找到白,它想或许找到白他就会想通了什么,也或许找到白它和白就不再需要他,若是前者自然皆大欢喜,若是后者,那总是伤感的,却也算各自安好了。于是每当有人从它身前走过时,它就仔仔细细的嗅着他们身上的气味。一次次的,除了臭味它什么都没有闻到。之前它曾肯定过那男人对于嗅到人身上不同寻常的血腥味的唯一性,就像它只能嗅到梦的味道一样,如今它这一次次的,不过是在'必须要做些什么'这样的主观念头的驱使下的悲观选择。
它将思绪稍缓,看着课上唯一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子,他始终低着头,不知道有什么吸引他。它顺着小孩儿的视线望过去,是一群蚂蚁。它记得那里是昨儿傍晚杀鸡的地儿。所有的蚂蚁都聚在那。突然精神为之一振,也许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它一脚将蹄子踏下,想拦下一只蚂蚁,问出心中的疑问。结果却出乎它的意料,那只蚂蚁悠悠然的从它的铁蹄下趴走。它无意识抬起右前蹄,想抓一抓自己的额头,却发现根本办不到。它打了个响鼻,却让那只小蚂蚁做了顺风车。乘着它鼻子里喷出的热气就飘走了,出师不利令它有些着恼。在第二只蚂蚁爬过来时,它用前蹄在蚂蚁的必经之路上划了道深沟。看着对方一失足滑进了它精心设计的陷阱里,惊慌失措的四处游走。在那只蚂蚁将将爬到沟边上时,它精准的控制气息,把它吹回沟里。如此往来数次,蚂蚁终于消停了。仰起那张和身子比显得有些大的头,眼神里是茫然无措,惊惧交加。
“咱们做个朋友吧!“它不确定对方能不能听懂它说的,它更不知道男人加住在它身上的束缚究竟范围有多广。
蚂蚁稳了稳被吹的险些翻了个跟头的身子,抖着声音道:“您,您有什么事吗?“
“唔?“它有些不懂,为什么对方会觉得自己有事呢?虽然它确实是有事。
“我们从来没有过像您这样的朋友,您这样的也不会同我们做朋友的。“
“为什么不会?我们?我们又是谁?“
“就是想您一样威猛高大高高在上的大人们。“
“那你还没说为什么他们不会同你们做朋友呢?“
“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缺,我们什么也给不了他们。“
它有些吃惊,吃惊对方说的那样对。
“所以你觉得我想和你做朋友是因为我有事?“
蚂蚁点着大脑袋,道:“嗯!“
“你说的不对!“
“哪里不对?您是说您没有事?“疑惑不只藏在它的语气里,更藏在它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里,更不要说它那双眼睛,更是透着深深的疑惑。
它有些懊恼的道:“不!我。。。。。。“它确实有事。它有些懊恼,为何最初要找了这样的借口,陷自己于两难的境地。
蚂蚁最初裂开的嘴角又再次恢复成一条线。它默默低下头,眼里的光散尽了,道:“你看!“它缓了缓道:“你是个好人,至少没有骗我们。“
它低声道:“我不骗人的!“
蚂蚁的耳朵很灵,听了它的话,道:“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惯常会骗人的。“
它有些好奇,道:“它们怎么骗人的?“
蚂蚁道:“他们会许愿,然后他们的承诺就变成了流星。“
它没有听的很分明,或者说它听了却没懂。
“那,这是你们的暗号?“它忍不住问道。
它这一问却将蚂蚁问的一愣。道:“什么暗号?“
它道:“不是暗号?“
蚂蚁轻叹了口气,周围连一粒尘的轨迹也没有发生改变。蚂蚁略微艰难的仰头直视它,声音是带着无奈与辛酸。
“你说对着流星许愿愿望会成真吗?“蚂蚁一副过来人的模样道。
它根本不需要任何思考,便道:“当然不会!“
蚂蚁道:“你看,多明白的事。“
它道:“怎么不反抗呢?“
蚂蚁笑着道:“你说我跳起来能打到你的脸吗?“
它一愣,便也懂了对方话里的意思。想了想,却只能含糊道:“那以后不信也就好了,咱们就不信他们了!“
蚂蚁道:“总会有人喜的!“
它道:“为什么?明知道被骗还是要信?“
蚂蚁道:“因为没有比相信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了,而越是渺小如我这般的越是希望在他人看来自己是不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眼里,自信着自己是不同的,或者说在那些如我一样的同类里,我是与众不同的,我会被高高在上者眷顾,我会得到我想要的,而他们会给我想要的。“
它疑惑道:“那,你究竟想要什么呢?“
蚂蚁道:“也许不过是今年过冬的粮食吧!“
它道:“这。。。。。。我可以满足你。“它本意想说这很简单嘛,却硬生生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蚂蚁道:“你看,你是如此轻易就能得到我费尽心力也难得到的东西。其实我知道你想说这其实很容易。你很善良,所以我说你和他们不同。“
它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它的心思被对方看的分明,没得掩藏。
蚂蚁道:“其实那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或者说如今的我也只能有这样的愿望。“
它不明所以,道:“虽然我未必有能力满足你,可我仍能倾听你的愿望。“
蚂蚁道:“若我是你那样高高在上,我的愿望一定不会是这样。“
它道:“如今你仍能有其他愿望呀!“
蚂蚁道:“若是自己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那什么样的愿望都是一样的,不会有大小之分,可若是他人满足自己的愿望,那你便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何况,渺小如我,只为了活着,那这一冬的粮食兴许是最好的。“
它哑口无言,这只小蚂蚁重塑了它的思想。“我。。。。。。“它将一块儿路上未吃净的食物扔给它,却一下将它压倒了。
蚂蚁从食物底下爬起来,道:“你看!即便我们要的再多,即便他人给的再多,可自己却连承受这份重量都做不到。“
它微微偏了偏头,道:“对不起!“声音里是说不出的懊丧。
蚂蚁道:“你不需要说对不起,就像我不会同你说谢谢一样!“
它一瞬的疑惑,而后了悟道:“你说的对!“
蚂蚁道:“报酬我已经收了,现在轮到该你说明的时候了。“
它恢复坦然,道:“我想知道你能闻见血腥味吗?“
蚂蚁虽然不明所以,却诚恳道:“自然是能的!“
它跺了一下前蹄,有些懊恼,不知道怎样才能将事情说的更明白些。
蚂蚁道:“我所回答的并不是你想要的?“
它道:“不,是我说的不对!“
蚂蚁道:“很难说明吗?“
它摇摇头,道:“也不是!“
蚂蚁道:“那是?“
它道:“是我,是我不知道怎么来说明。“
蚂蚁道:“那不如我来问?“
它想也好,这样兴许能知道些其他的信息。于是点头道:“好!“
蚂蚁道:“我想要的是食物,这很明显,那你呢?你想要什么?或者说你再找什么?“
它道:“我,我兴许是在找一个人。“语气是那样的不确定。
蚂蚁道:“你很不确定?是不确定你想找的?还是不确定他是一个人?“
它道:“我不确定他是一个人。“这次的回答简短而快速。
蚂蚁道:“为什么?不是人它还能是什么?“
它道:“我只知道它叫小白或者白,我见过它一次,是在深潭里,不真切,不过确实是人的形体。可人是没办法在那个深潭里生活的。“
蚂蚁道:“那在不确定它的形体时,你本来要怎么确定它就是你要找的它呢?是有什么其他的标记吗?类似胎记之类的?“
它道:“气味,是气味,它身上有着所有人都没有的气味,又有着所有人都有的气味,就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气味。“
蚂蚁道:“那你们来到这里是循着气味来的?“
它道:“是循着气味来的,不过并不是他的气味,而是血腥味。“
蚂蚁道:“血腥味?“
它道:“对,血腥味,我们是随着那个身上有血腥味的大娘来的。你知道那个大娘身上为什么会有血腥味吗?“
蚂蚁道:“不只是那个大娘,这里的所有人除了小孩子,身上都有血腥味。“
它道:“为什么?“
蚂蚁摇摇头道:“不清楚。“
它道:“孩子没有?也就是说不是出生就有的?“
蚂蚁道:“对!而且即便是大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和年龄也无关,就是某一天某个人兴许是从某处回来就有了。很奇怪!“
它道:“很奇怪?“
蚂蚁道:“这样不奇怪吗?“
它摇摇头,道:“自然很奇怪!“它只是惊异于这份奇怪。
蚂蚁道:“只有小孩子不会。“
它道:“你为何如此确定?“
蚂蚁道:“因为我遇见过你!“
它不太理解对方的遇见过是指什么,问道:“怎么遇见?你遇见了这整件事的源头?“
蚂蚁道:“怎么会?只是我见过母亲领着孩子回娘家,结果回来的时候女人身上就带着血腥味,而小孩子身上却没有。“
它一面思索着蚂蚁的话,一面却有些心猿意马,迫不及待想把这会得来的消息一股脑儿的同男人说个详尽。
“对了,有一个小孩子,只有一个小孩子身上有血性味。“蚂蚁突来的一句话,惊了它一跳,险些一脚踩在蚂蚁身上。那蚂蚁却纹丝不动,只仰着脖子道:“你看,即便你是个好人,可渺小如我,同你来往时仍要提防你的漫不经心,因为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可于我而言,却仍无异于与虎谋皮。这就是我的悲哀。“
它嗫嚅道:“对,对不起!“
蚂蚁道:“我觉得你在变的自大,因为我!“
它突然遍体生寒,它在变的自大?这句话是对的,如果先前的对不起是无知,那此刻它确实是自大的,而男人选择留下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大?
它道:“你讲我看的那样清楚。“
蚂蚁道:“不对!我只能看见你朝着地面的那一面,而且我永远看不见我自己。“
它道:“可我看见了你朝向天空的那一面。“
蚂蚁道:“我说过,因为你是好人。你会底下头和我交谈,而他们不会,他们压根看不见我,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帮你的原因。“
它道:“那你身上有血腥味吗?“
蚂蚁道:“我自然是有的,凡是咬过人的蚂蚁身上都有血腥味,就像标记一样。“
它道:“如果我想问那个小孩子是谁,你还会告诉我吗?“
蚂蚁道:“会!“
它道:“为什么?“
蚂蚁道:“因为你给了我食物。我不仅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我还知道你想问我他们去到过哪些相同的地方。“
它惊异于对方的敏锐,道:“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地方?“
蚂蚁道:“确切的说我不清楚那算不算一个地方。或者那是不是你想的地方。“
它沉吟片刻,道:“我想先知道那个孩子是谁。“
蚂蚁道:“你看,看哪个孩子没有来上课就是哪个孩子。“
它道:“全村只有那一个孩子没有上课?“
蚂蚁道:“对!他不回来!“
它好奇道:“为什么?家里人不许?“
蚂蚁道:“不,和家里人无关,他如今也没有家里人了!“
它有种感觉,这兴许是问题的关键。急着道:“孤儿?“
蚂蚁道:“算是吧!“
它更是一头雾水,疑惑道:“什么叫算是?“
蚂蚁道:“他母亲还活着,不过在监狱,而他父亲听说是被他母亲咬死的。“
它道:“听说?“
蚂蚁道:“道听途说还是空穴来风,这我也说不好!“
它道:“那这和上课有什么关系?“
蚂蚁道:“因为希望!“
它懂希望这个词的意思,甚至说没人比他更懂的希望的意思,因为它曾经多次在绝望的边缘。可此时此刻,这个词用在这里,承接它的上一个问题,它便无法理清了。
“我不是很明白。“它直接了道的问道。
蚂蚁回道:“是因为他不在承继任何人的希望。只有大人才觉得学习是出路,小孩子不会这么觉得的。“
它似懂非懂,道:“那他本身呢?还有希望吗?“
蚂蚁道:“血腥味那么重应该是难了吧!毕竟那些大人,他们从来没让我看见过希望。“
它一瞬有些伤感,两人一时无话。良久,蚂蚁道:“你这个样子和那个男人越来越像。“
它全身一个激灵,呼吸都显得急促起来。忙问道:“那,那个地方呢?你说的那个地方!“
蚂蚁道:“这个村子有三个入口,每个入口大约五公里左右会出现第一个岔路口,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地方!“
它道:“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却一定存在。“
蚂蚁道:“对,我可以确定,这个地方一定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在村内染上这种血腥味的。“
它重复道:“染上血腥味?“
蚂蚁道:“染上!在我看来,这就像流感一样,带着传染性!“
它摇摇头,道:“也许本来就病了,不过是遇到了什么诱因,才会显现出来。“当然,这只是它的直觉。
蚂蚁道:“你知道什么人闻不见血腥味吗?“
它再次摇摇头,却与上次在本质上不同。
“什么人?“
蚂蚁道:“同样是一身血腥味的人,所以你刚刚说的也对。若是只有一个人有血性味的时候,别人却仍旧闻不到,证明他们本质是一样的。“
它道:“你,你为什么将所有都告诉我?真的只是因为食物?“
蚂蚁道:“这并不是什么好意,你只要记得这个就好。“
它通体一阵颤栗,喃喃道:“什么?“它是真的不明白对方的意思,或者说它的神经先于它的理智体会到这句话里的恶意。
蚂蚁道:“我想知道,你会不会有一天同我一样,或者说有一天我可以平视你。“
它端详了对方片刻,斩钉截铁道:“不,你没有说实话!“
蚂蚁也是会笑的,这是它看见对方嘴角咧开时的第一想法。
“你。。。。。。“它虽有千言万语,可也都落尽了那个令人惊异的笑里。
蚂蚁道:“你还想知道吗?“
这次它没有在第一时间便给出答案,思索了片刻才道:“好!“
蚂蚁道:“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话落,对方却良久都没有出声。它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丝毫想要催促的想法。或许它也并不如它自己想的那样想知道。它只在默默注视着对方的'拖延'。
这一刻它觉得时间并不是一条笔直的线,你看此刻这时间就划出了一道巨大的弧,令它从这岸到那岸花费的更久更久。你可以说两个时间点之间是直线,可你却不能说你经历的时间是直线。而此刻,这世间于它而言,很慢很慢,慢到它的思绪回到了那个寒冬的山上,直到对方开口,它都栖居在那山上,就那样过了千年。
蚂蚁突然打破这千年的时光,道:“因为你是个好人!“
它一瞬间有些愤怒,没想到它等了千年,等来的却是比之前更模棱两可的一句话。这让它觉得自己有些可笑。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它忍了忍,仍是问出了口。
蚂蚁道:“我想看看,你能不能一直好下去。“
它道:“我不懂,我仍然不懂。“
蚂蚁道:“走的越远,知道的越多,探究的越深,越难保有自己。“
它道:“这于你有什么好处?目前而言,你所做的一切,于我也并没有坏处。“
蚂蚁道:“好处?好处也是有的。“
它问道:“什么好处?“声音里有着说不出的急切。
蚂蚁道:“好处就是让我能更坦然。“
它道:“坦然?你如今又有什么不坦然的?“
蚂蚁道:“我想证明没有人可以完全保有自己。“
它道:“证明了你就坦然了?“
蚂蚁毫不犹豫的道:“对!“
它笑了,一副马脸带着笑意,有着令人捧腹的效果,此刻唯二的两位当事人却谁也不是真正的心情愉悦。
“不对!你说的不对!“
这是蚂蚁第二次惊讶,拔高声音道:“什么?你知道什么?你又见过多少人事?“
它道:“你有那样的想法,不正说明你仍旧不信吗?“
蚂蚁道:“不,我又这样的想法恰恰证明我信了!“
它瞬间的茫然恰好落尽蚂蚁的眼里,这令它更坚定自己的想法。若是这样一个原本就和自己站在对立面的人,在走过一段漫长的路后仍能保有它今日的模样,那自己还有什么怨言呢;若连这样的它也不能跳脱这凡事俗例,那自己又有何羞惭的呢。
“你呀,一定要记得,给予你越多的人兴许是好人却未必对你好,兴许是坏人却一定对你不好。什么东西多了都会养成贪婪,什么都不例外。即便是发呆,也会让你在饿肚子的前一刻而想要不劳而获。“
它摇晃了一下相对而言硕大无比的头颅,蚂蚁看着它那颗硕大的头颅像要被它的主人摇晃下来似的,出于同是弱者而产生的同情,蚂蚁对那颗头颅产生一种悲悯感情。有一刻甚至在想,摇吧摇吧,掉下来砸死自己,那弱者和弱者就同归于尽了,而且还杀死了自己眼前的这个高高在上的庞然大物。这是一种嫉妒,不同于对于先前的那些带着世俗权威的人,这种嫉妒更混杂着一种同情,这同情不是源于此刻的它,这同情在此刻产生,却是源自于对将来的必然的一种同情。所以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情感。蚂蚁甚至不想对对方说清楚,不仅是因为没有必要,更是因为自己没办法同对方说清,而且自己也知道,对方不会懂这样的感情的。这是一种无知的本能,甚至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本领。于自己却是一种矛盾的折磨,真真是令人讨厌到极点,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方。
“我还是不能理解。“蚂蚁的思绪被对方强行拽了回来,没有任何恼意,甚至带着感谢。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之后自己会陷落到哪里。
“你也不需要理解。“蚂蚁幽幽的道。
它仍是不懂,追问道:“为什么?“
蚂蚁没有给它想要的答案,只道:“你如今很危险。“
它不懂,它似乎什么都不懂,接连追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蚂蚁道:“因为你想要的太多。“
它不懂,怎么自己想要的就多了?“
蚂蚁看着它仍旧带着希冀的眼神,道:“你在要一个答案,不对,这么说不对,你是在要很多问题的答案,一个问题本身就有很多答案,而你问了那么多问题,答案又怎么会少?你现在已经贪心了。“
它疑惑道:“这就是贪心?“
蚂蚁道:“这不只是贪心,而是大大的贪心。“
它道:“贪心了,就很危险?“
蚂蚁道:“没有比贪心更危险的了。“
它道:“为什么?“
蚂蚁道:“因为贪心会撑死的。“
它突然发现,其实它对这个人事了解的太少了。它在山上驻足了太久,久到它看的出一颗果子的喜怒哀乐,却看不见世人崎岖的心。
“我想你可以离开了。“它沙哑着嗓子道。
蚂蚁扛起自己的来的食物,也并未因对方的话而感到意外。走了很久,在自己的认知里蚂蚁走了很久,终于走出了它的阴影。
“哦,关于那个孩子,还有另一个故事,为表我最后的谢意,我决定将那个故事也告诉你。“
蚂蚁的声音从稍远的地方传来,幽幽的令人遍体生寒。它侧过头,直直的看着对方黑色的脊背,只那么一小点的黑色脊背。
“你说,我会听,而且会认认真真的听着。“
蚂蚁没有往下它,只是侧了侧身体,确保自己完全处在阴影之外。蚂蚁没有它的良好视野,而它则没有蚂蚁的那份心思,所以他们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影子被蚂蚁背着的那块食物连接在一起。
“那孩子的爸爸是个杀鸡,那家媳妇每天的活计就是给鸡拔毛。听说这个男人杀鸡从来都不用刀,那个孩子和他一样,是个狠戾的主儿,杀鸡的时候也从来不用刀。“话落,显然还有未尽的故事,可对方却像抛了个饵似的,不动声色的住了口。
它声音平稳,听不出意思急切的道:“说完。“
蚂蚁道:“其实这个故事你完全没有必要听,更不需要听完。你现在就像个小孩子,你的友善,你的纯真,包括你的好奇心,都像个小孩子一样。“
它越发的声音平稳起来,道:“所以?这和那个故事又有什么关系?“
蚂蚁道:“也许不是这个和故事有关系,而是故事和它有关系。“
它略一思索,道:“你是说,你在骗我?“
蚂蚁道:“也不尽然。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如今在长大。“
它道:“你在用一个不真不假的故事来告诉我我在长大?“
蚂蚁道:“不,这个故事是真的传言,传言中那个孩子同他父亲一样,可以一把拧断母鸡的脖子,离得近了,你能听见他家院子里总是传来骨骼错位的声音。传言中有一天下午,那家院子传来一声不同往日的清脆声响,远非鸡的脖子可比。“
它道:“你不会想说是那孩子杀了他父亲吧?“
蚂蚁道:“不,我不想这么说,我只是想告诉你,那家男人是被扭断脖子死的。“
它强自镇定,虽然之前它问出了口,却并不代表它真的这样觉得。或者说它在等待对方的否定。而对方也确实否定了,它猜想自己那会儿的嘴角兴许有些上扬,甚至令蚂蚁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如果对方有看在看它的话。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大人都是一身的血腥味,怎么也洗不掉的原因。“
这是蚂蚁留给它的最后一句话,除了那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这句话是确确实实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它与对方的交谈也不过一个钟头而已,可此时它却异常的疲惫,自然不是因为它四蹄着地站了许久,更不是因为它的大脑袋一直低垂着,那是一种心理上的疲惫,并带动了整个身体,让它的四肢头颅无处安放,让它的心脏跳动迟缓血液流速变慢,让它耳不能听眼不能视。一瞬间的意兴阑珊,令它整个将自己冰封起来,它想与外界隔绝开,它甚至想回到山上,就这么冲开缰绳,撒开它的四蹄,朝着它曾经的那座山疾驰而去。只要想到这里,似乎体内的一切都在回流,心脏有力的跳动,血脉在皮肉下奔腾,耳朵听见周围呼啸的风,眼睛的落处就是那座它山,而山上仍是它离开时的模样。那里有什么好吗?那里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那里只有一点最好,那便是它熟悉那里的一切,即便是那个那个苦寒的冬日,它也早已熟悉。一颗黄色的落叶从树尖尖上落下需要几秒钟,一颗红色的果子在熟到什么程度就会自然落地,一颗小草在第一抹绿叶抽出后的第几个小时会看到另一抹绿叶的踪迹,蝴蝶颤抖翅膀的声音告诉它对方要去到哪里,雄鹰的鸣叫声告知它对方是在搏击长空还是在朝着猎物俯冲,这些,才是它所熟识的。兔子被太阳宠惯着忘了它那身皮毛敌不过老虎的厉爪,狐狸自作聪明的令乌鸦开口说话,却不知乌鸦早已倒向猴子的肩膀,鸟儿的歌唱不是歌唱,是它们对食物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