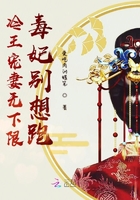晨霜已过,入了夏的阳光很是和暖。高高的宫墙的颜色本来就是单调灰亚的,浸润在晨曦中便突然多了几分俏丽,反倒是那朱红大漆的宫门,在这朝阳里却收敛了颜色,变得沉着了许多。墙根下站了两列卫卒,在阴影里仿佛并不存在一般。
两尊大轿离宫门远远的便停在了那里,下人撩开了帘子,杜晟风迈腿下了轿子,便看见了对面的当朝首辅齐哈儿齐老爷子也刚好探出了轿子。他连忙几步抢了过去,躬身施了一礼,说道:“下官杜晟风见过齐相。”
齐哈儿齐老爷子,担任首辅已超过十个年头,三朝元老,已然年界花甲,精气神各方面还算可以。皇帝虽有恩旨,让他不必每日在政事堂当值,可是他依然每日必到。
他淡淡地看了杜晟风一眼,说道:“来啦,真难得,你昨儿个居然没喝醉!比我那小儿子出息。”
杜晟风知道他说的是昨晚宣王府的宴会,齐家的三爷也在场,便微笑着将齐哈儿扶出轿来,说道:“不过是一帮子人在那里风雅赋颂,意气相合兴致难抑许是有的,这等杂事不想竟也劳齐相挂怀。”
齐哈儿扶住了他的手,也没撒开,就一路向着宫门里走去,一边问道:“知道为何宣咱们进宫吧?”
杜晟风说道:“下官不知,不敢揣摩圣意。”
齐哈儿又看了他一眼,脚下没停。他当然知道这不是实话,只是年轻人要装一下深沉,自己又何必戳穿他。便说道:“洛家那位诰命夫人今日一早也被宣进宫见皇后去了。”
这么明显的提示,杜晟风可就装不下去了,抬起头,正好见到这位老宰辅垂下了眼皮收回他的目光,陪笑道:“这样说来,该不会就是为了曲家的那位少公爷吧。”
齐哈儿问道:“你们家是什么态度?”
杜晟风沉默了倾晌,才说道:“很为难。”
齐哈儿听了,呵呵地低笑起来:“这句话算是实诚。”
“照我自个儿的想法吧,嫁不嫁他曲家倒是无所谓,几年前就想给妹妹重新配户好人家,谁知这丫头偏就耿直了脖子不乐意。不怕您笑话,真是绝食上吊跟我硬扛着。”杜晟风叹着气说道,“您是知道的,家父去得早,祖父又告老回了祖籍,就我兄妹俩相依为命,我这当哥的真怕她出点什么事,将来可怎么去见家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吃错了什么药……也罢,家里多她一张口我也养得起。”
“我家那小丫头片子亦是如此啊。”齐哈儿仿佛有些无奈,说完这句话,便低垂着眼皮,扶着他的手沉默地走进了宫门里。
脚底下铺彻着一块块青灰色的方石,层层叠叠的向着远处高高的台阶延伸着,台阶的尽头是一座金顶红柱的恢宏殿阙,但静悄悄空落落的。侧边,一个宫里的内侍正踩着碎步向他们小跑过来。
齐哈儿看着那个内侍,似乎是走得有些累了,便站住了歇歇脚,才又说道:“听说有一年你们家也遭了曲少公爷的祸害,被惊天动地地拆了半栋楼?”
杜晟风听得一怔,眼底下掠过了一缕复杂的神色,更多的是无奈,苦笑道:“这京都之内遭此祸患者不知凡几。”
齐哈儿又抬脚朝那内侍迎去,一边淡淡地说道:“我们家也曾遭此一劫……内宅。”
杜晟风皱起了眉头,此事他也曾听说过,只是他听不懂这位老宰辅要说些什么。
然后,就听齐哈儿叹了口气,又说道:“一栋楼换一条命……想来是不亏的……只是,终究还是便宜了他曲家。”
杜晟风思索着,终于明白了老大人的意思,尤自狐疑地问道:“齐相的意思是说,彼时家中有妖邪盘踞蛊惑人心图谋害命,是这曲少公爷闯宅降妖?”
话是如此,只不过他还是不明白,这位老大人此时说这话是何意。
“小孩子顽劣定然是有的,”齐哈儿仿佛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放开了他的手,站直了说道,“妖邪入户也是有的。”
杜晟风心中一下清晰了许多,也没说话,只是跟在齐哈儿身后缓步走着。这几年以来,齐杜洛这几家人虽说并不曾公然争斗,但底下暗潮澎湃,都憋着一口气呢。不说是权贵门第吧,至少亦是官宦世家,到底也都是要面子的。更何况自己的妹妹在这三女中年纪最长,已经满二十了,是个老姑娘了,不论从何说起,自己都不可能后退一步。
只是据说这洛家四姑娘和皇后很是相得……但是若是相得便可,又何须挑三家绣像,直接指婚便是……不过昨夜里宣王瞧着自己和齐家三爷的神色颇有些暧昧,眼神里竟隐约有点戏谑的意思,当时只以为是因了曲少公爷回京,大家都抱了看热闹的心思,现在想来并非如此——洛家那位夫人可是单独去见的皇后!所以陛下要见自己和齐相莫非是……
正胡思乱想间,这边的内侍已跑到两人跟前,给他俩施了一礼,说道:“小的童承贵,请两位大人安,陛下正在德光殿。”
齐哈儿只略抬了抬眼皮,微微点了点头,一付云淡风轻的模样。当然了,若不是他家的小千金执拗,要争上一争,就那年岁,就是再配一户人家也来得及。所以心境自然与别不同。
杜晟风按下胸口翻涌的血气,收敛了心神,说道:“烦劳您前头引路。”
拐过了两道门廊,就见到身形魁梧的理亲王和靖安侯正相偕而出,想来是向陛下奏禀昨夜神都细况的。天子御前,不敢喧哗,几人只拱手一礼便默然错身而过。
错身之间杜晟风却瞟见了靖安侯向他送来了一道宽慰的眼神,袖下的大拇指向上微微一振,他不由得心中一动——莫非是有戏?
靖安侯和他父亲曾一同随侍先帝御驾西征,相交甚深,料是不会骗自己的。心头略微一松,脚下便也不自觉地轻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