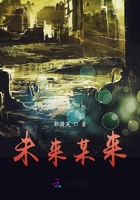严家庄不像山南省的D城,在D城,过了腊月二十三就算是进入年了,一直到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严家庄不一样,严家庄到了腊月二十六才开始过年,到了二月二年才算结束。但农村的年比城里热闹多了,家家户户早早就贴上新对联儿,门口挂上大红灯笼,街道上到处弥漫着鞭炮的火药香,平时节俭的农民这时候也非常的大方,大门上的灯笼常常是昼夜通明,照的街道如同城里的大马路一样明亮。这时候,大街上到处是小孩儿跑来跑去的放鞭炮,还有穿着新衣服喜气洋洋拎着礼盒走亲访友的人们。满街都是鞭炮爆响后留下的碎屑,道路上的结冰都开始融化,微微润湿的路面让人感受到一种春的气息。
这些天基本都是三虎陪着严华在村里头转,他俩一起去看往日的同学,一起去广场上跟村里的老人聊天儿,还一起去看望他们小学时候的王老师。王老师头发都白了,佝偻着身子,走路都要拄着拐杖,说一句话就要喘会儿气儿。王老师家以前是村里头的大地主,他们家的四合院是当时村里最好的建筑,但是因为王老师是老师,村子里老的少的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王老师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严华和三虎找到王老师家的时候,王老师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虽然不是状元,但是却教出了状元,现在这个状元又来到家里登门拜访,他感到非常的高兴,当然也免不了有几分得意。不过相比于对严华,王老师对三虎没那么热情。虽然三虎也故作热情地跟王老师套近乎,但王老师是个不会做作的老学究,三虎不停地说:“王老师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我不就在村里吗?我随叫随到。”王老师也就不再客气,严肃地对三虎说:“三虎,你要是还认我这个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看你把咱村的河挖成啥样子了?连河坝都挖得东缺一块西缺一片的,河坝上的树都死了那么多,这万一上游发大水,村后面的地都要被淹不说,咱们村儿不也很危险吗?”王老师一席话说的三虎脸红脖子粗,心里真后悔带严华来这儿,心想王老师你这么大岁数了,懂什么呀?小时候你教我,还真以为一辈子能教我?我就给你个面子罢了。心里不满意,但碍于严华的面子也不敢说什么,就连连点头称“是”,然后再不吭声。
从王老师家出来,三虎问严华:“哥,你啥时候回D城啊?”严华说:“过了节吧,那边儿几个战友也在催我回去聚会呢!还有工作上有些事情也得早点回去安排。”严华说的是实情,D城的战友和陆豪这几天都问他何时返回,但他确实委决不下。倒不是因为母亲这边儿有多大的事儿,而是这两天他得到了一个特别的信息:邻村康庄的臧老回来了。
说起来臧老曾经是严华的老上司,如今早已是权重一方的人物。严华心里有点儿小纠结:于理来说,严家庄和康庄相距不过二里路,早年间差点儿划成一个大队。说是两个村儿,其实跟一个村儿差不多,两村的人彼此都比较熟。臧老回老家过年,自己也回老家过年,按说自己应该登门拜访。可是因为今年的那个小小波折,严华总觉得自己没脸去见臧老,他知道臧老是一个铁面无私的老头,在他那儿只有原则,只有纪律,他跟谁都不会客气。现在去见他,严华不由有点儿心虚,可是,拜望臧老是必须的!
严华在心里思量着,是带思群一块去拜望臧老合适?还是带着三虎去合适?带着三虎去应当应份,毕竟三虎是现管,可是万一臧老不给面子,当着三虎给自己两句,那也太有点儿掉份儿;带着思群去,有思群舅舅的这层关系,可能臧老多少会给一点面子……臧老虽说再有两三年就退休,但是虎威尚在,自己真不能掉以轻心。这样一番掂量,严华决定把思群和三虎都带上,一来想着臧老不会当众给自己难堪,二来有三虎在,也有个开车拎包的人。三虎现在也不是普通村民,这样的事情他相信三虎一定也很乐意去做!
严华没有猜错,当他把这个想法跟三虎说了之后,三虎喜不自胜,臧老的大名远近十里八乡谁不知道,但三虎只见过臧家的老二,跟臧老都没照过面。现在既然有这机会,他三虎在这一带也算小小名人,何况他还有着更上层楼的雄心壮志,能去见臧老一面,当然是天赐良机。
看三虎答应得如此爽快,严华也挺高兴,他告诉三虎不要买什么贵重礼品,只需要把当地的土特产拿一些过去就可以。三虎高兴的连连点头说:“哥,你就放心吧!”
严华和三虎约好了时间,到了日子就带着思群一起去康庄看臧老。康庄在严家庄的东边儿。两个村只隔着一道叫沙坡的土坡。沙坡曾经也是严华和三虎他们小时候的乐园,那时候康庄和严家庄的小孩儿经常打仗。严家庄的小孩儿在沙坡的西头,康庄的小孩儿在沙坡的东头,互相投掷石子儿瓦片等对打,有时候还免不了肉搏。沙坡上沙子松软,小孩们经常故意在沙坡上打滚儿。一路上严华和三虎免不了说些小时候的趣事,思群听着怪有意思,没想到一向严肃的严华还有这样有趣的童年。
不一会儿康庄就到了,三虎知道臧家院子的位置,直接把车开到了一座灰色院墙的院落门口。
跟农村所有人家一样,臧家的院门儿敞开着,院子里是一幢看上去很普通的二层小楼。三虎把车上的东西搬了下来放到一进门的门洞,是一蛇皮袋粉条,一袋莜面,一袋黄米面,一只早上新宰的羊,还有一副猪排骨、猪头猪蹄。然后三虎就去找地方停车。这时,院子里有个妇女迎了出来,看到严华思群,一个也不认识,不由一脸讶异。看看门洞摆放的东西,妇女急忙说:“你们快走吧!大哥不让外人来看他,更不让要东西。”严华和思群有些尴尬,正在这时,三虎停好车走了过来,笑着跟妇女打招呼:“二嫂,是我,我是严家庄的三虎。”
听三虎自报家门,妇女脸上讶异的神色才消失了。毕竟是邻村,虽然见了面不一定说话,但总是看着眼熟。妇女以前也见过三虎,只是不知道眼前这人就是严家庄大名鼎鼎的三虎村长。
既然是邻村的村长,那就不是外人了,二嫂就领着他们三个进了一楼的客厅。三虎跟二嫂介绍了严华,严华心说这应该是臧家老二的媳妇了,也就跟着三虎喊“二嫂”。二嫂微笑着看严华一眼,心说原来这就是严家庄的严华,他跟大哥可是这一带的名人呢!对严华和思群就热情了一些。
严华客气地问道:“二嫂,臧老呢?”二嫂指了指楼梯,说:“在二楼打牌呢!”听说臧老在打牌,三虎和严华对视一眼,臧老难得有这闲工夫在家打会儿牌,他们要这么贸然上去了,会不会惊扰到了臧老,惹臧老不高兴?可如果不上去,这牌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难道就这么干巴巴地坐等?如果不见一面,连句话都没说上就走,那这一趟不是白来了吗?以后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会再有这机会呢!想到这儿,严华对三虎说:“这样,我跟你嫂子先上去看看?”然后就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三虎。
三虎虽是粗人,但也知道臧老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见的,自己再怎么着不过是个村长,见臧老还是差着好大好大一截儿,虽说他精心准备一番,就是为了能一瞻臧老的丰采,但现在这情形,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上去,他可不敢冲撞了臧老。
严华说了声“二嫂,那我们就先上去”,然后就带着思群蹑手蹑脚地上了二楼。
上了楼梯拐个弯,看到二楼有三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的门虚掩着,严华轻轻走上前推开门,见四人正在打麻将。臧老背对着门,他的对面是一个长相跟臧老极其相似的人,应该是臧老二,另外两个男的一看也是有身份的,但是严华不认识。
屋里静悄悄的。臧老二第一个到严华和思群,看了一眼没说话,他不认识这夫妻俩。严华看到臧老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快掉地上了,连忙蹲下身轻手轻脚地把衣服捡起来,又轻手轻脚地挂好。那份小心,简直就像怕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恰好这时臧老回身,严华赶紧恭敬地喊了声“臧老”。
臧老看到是严华,没有说话,眼神中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厌恶,连思群这么不敏感的人都看出臧老对严华的不喜欢。她不由地替丈夫尴尬,同时也心疼丈夫,——堂堂七尺男儿,此时竟然如此卑躬屈膝!却还惹人家这么讨厌!做男人真难,没想到他有这么低声下气的时候!
臧老看见思群,面色稍微和缓了些。一边继续打牌,一边问道:“没事吧?”严华一听臧老开口,赶紧回答:“没事没事,就是知道您回来了,过来看看您。”怕臧老又给个冷脸,严华又急忙说:“那您玩吧!我们就走了。”
臧老连头也没有回,似乎嘴里“唔”了一声,又似乎没有。严华也顾不了那么多,拉思群一把,两人就下楼了。
三虎还在一楼客厅等着,见严华和思群下来,他兴奋地站起身迎上去:“华哥,怎样?我能上去吗?”严华笑着对三虎说:“别上去了!臧老打牌正兴头着呢!刚才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出牌,把自摸的牌都打出去了,可是奇怪,转一圈又摸回来了。臧老说咱们的心意他知道了,以后好好工作,需要什么支持和帮助就来找他!”
三虎不由地有些失望,白张罗了半天,连臧老的面都没见着,不过,既然臧老说知道了他们的心意,还说需要帮助和支持就去找他,那这一趟也不算白来。
二嫂客气地把三人送出院门,三虎去开车,严华和思群在门口等着。思群有些迷惑地望着严华,心里有许多疑问,严华却一直望着三虎取车的方向,好像在急切地等待着三虎,并不拿眼神对着她。
三人返回严家庄的时候,似乎不如来的时候那样兴致勃勃。三虎憋了半天,才闷声闷气地说:“唉,臧老这架子可真够大的!”严华笑了笑,未置可否。三虎一边开车,一边指着沙坡说:“华哥,看到了吗?这是咱村和康庄共同的坟地。甭管多能耐的人,早晚总得埋骨故乡吧?”严华知道三虎不高兴,有意岔开话题:“三虎,咱村的坟地不是在南皮岭吗?啥时候沙坡也成了坟地了?”
“哦,华哥可能还不知道,”虽然三虎心里不舒服,但他也不愿意得罪严华,耐心地解释着,“修那条旅游线路的时候,征了南皮岭一些土地,有耕地,有坟滩,户主们不大乐意,最后除了补偿土地损失,又在沙坡划出些荒地来让他们迁坟。这样咱村坟地就跟康庄的坟地相邻了。”
思群无心听他俩说话,她看着车窗外掠过的一棵棵白杨树,在上午太阳光的照耀下,是那样地挺拔!她不由想起一位文豪对白杨树的描写,那是高中时学过的一篇课文:“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思群特别喜欢这两段,多少年过去了,她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这一段来。曾经,严华在她心目中就是那高大挺拔的白杨树,虽然他出身平凡,但他有坚强的意志,有伟岸的品格,有不屈不饶的精神!可是,现在的严华怎么了?他那挺拔的脊梁哪去了?他那铮铮傲骨哪去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丈夫能屈能伸?”严华不是韩信,他也更不是勾践,倒是他的作为颇有韩信从别人胯下钻过、勾践尝吴王粪便的勇气!他为什么就不能坦坦荡荡做好自己,为什么非要如此卑微呢?
还有,从二楼下来以后,严华神色泰然地跟三虎转述臧老的话,真是天衣无缝啊!如果自己不是亲眼所见,差点就全都相信了!这个人,原来还会撒谎!而且撒谎不用打腹稿,不用眨眼睛!
她觉得有些不认识严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