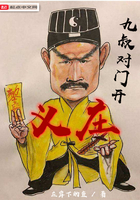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命运之地。当踏上那片土地之时,你会发现,是它在召唤着你。你和它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命中注定。而后,你“真正的人生”也将从此开始。
“我透过云层俯瞰,看到了一片美丽的群岛,那是一种无上的,令人神往的地理之美。我感觉冲绳县正张开双臂,等待着我投入她的怀抱。”
李鸣在飞机上,于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现在的他已下了飞机,第一次踏上了这块不久后即将改变他整个命运的土地。“这里的空气似乎比日本更加清新呢!”行进在冲绳的街道上,李鸣一边感受着这里独特的南国气息,一边说道。“说什么呢!这里还不一样是日本吗?”在李鸣身后推着轮椅的万里泊文笑道。“啊,是埃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同呢。”李鸣看着街道上人们的言谈举止、口音神韵,总觉得和他在神户或京都等日本其他地区所见的略有区别。多么微妙的不协感埃“始终是不同的民族嘛,多少都会有些不一样的。”泊文解释道。“是埃。。琉球族和大和族是不同的呢!”李鸣略有所思的点点头,继续用他那目光如炬的眼睛观察着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他的新小说里需要论及冲绳问题,明天在琉球大学的社会学演讲中也或多或少要讲到一些本地的风土人情。所以,李鸣认为他有必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城市,现在的每一秒钟对他来说都是珍贵的取材时间。
“到了,今天你就住在这里。”不多时,二人来到了他们所下榻酒店的房间前。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从窗户望出去甚至能看到海,对于一个外出取材的作家而言,这确是再合适不过的居所了。“觉得怎么样,还习惯么?”泊文问。“恩,还不错。”李鸣摇着轮椅把房间的每一处都逛遍后,满意地说道。“不过,泊文,在光即将要来日本的时候,我却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好像刻意不想见他一样,这是不是有些不好?”“这也是李先生‘工作’的一部分嘛,只是时间不凑巧的碰到一起了。相信来栖先生会理解的。”泊文微笑着答道。“别想那么多了,李先生你先休息一下,有什么要求就叫客房服务。我现在得去琉球大学和他们谈一下明天讲座的相关事宜。”“恩,那就有劳你去联络了。”二人闲聊了两句后,泊文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李鸣坐到写字桌前,拿起纸笔,整理着他一路上所做的一些记录,认真的为明天的演讲做准备。但没过多久,皱纹就爬上了他的眉头。很显然,他对这一点零星的记录并不满意。如果从现在开始的大半天都只是窝在房间里休息,单靠手头上的这点资料想将好明天的课是不可能的。“恩,我得到外面去多取一些材。”李鸣决定后,便带上笔纸离开了房间。
李鸣认为在闹市或大街上看到的东西都大同小异,无非是现代生活下盲目的人群而已。要想更深的去挖掘一个地区的神髓,就得把着眼点放在边远的乡下或郊区。于是,李鸣来到了一个临海的地方。这似乎是一个城中村,木头建起的平房零散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一些戴斗笠的渔民正在朝海里撒网,空地上则有几个孩子一边拍手球一边唱着带有浓厚乡音的儿歌。毫无杂质的淳朴之风扑面而来,李鸣感到一股洗净身心的愉悦。但紧接着,他却看到了一个无法融于眼前风景的东西——那是一片用三米以上高的铁丝网重重包围的区域,其内有宽阔的操尝巨大的仓库和一些像是宿舍的矮楼。整个区域的占地之广令人惊叹,它的面积几乎比旁边的小村还大出三倍。这似乎是某个机构的用地,已有一定历史的铁丝网将其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使人难以猜透到底是什么人占据着这块土地。“乔,你上次欠我钱什么时候还啊?”“哈哈,你还记得啊?那就用来抵你今天即将输给我的债吧!”正在李鸣狐疑之际,三个用粗犷嗓音操着满口美式英语的白种人从一栋建筑物里走了出来,他们嘴里叼着烟,手中拿着啤酒瓶。三个人选了一块地,大大咧咧地坐下,一边用粗俗的言语大声谈论着与性有关的事,一边就地打起扑克牌来。透过铁丝网的洞,看着他们的穿着,再看看建筑物上的英文字母,李鸣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美军基地啊!”
李鸣并不十分了解冲绳的历史,故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美军基地。但此刻他想起了早前时候在飞机上俯视到的冲绳地理位置,他忽然意识到这冲绳县的坐标于整个太平洋而言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美军在这里建起基地似蕴含着高超的战略考量。“看来,我果然尚未看清冲绳的全部啊!”李鸣心中感叹着。正在这时,一个小孩的手球突然滚了过来,美军基地这个方向的铁丝网上正好有较大的破洞,手球不偏不倚的滚了进去,正压在三个美国兵打牌的“赌桌”上。“哎呀,球滚过去了,我去捡!”失手把球弄丢的孩子像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跑到铁丝网边,对内喊道:“大哥哥,能帮我把球扔过来吗?”美国兵却并未听到他的喊声,似正在争执着什么。“喂,刚才是我赢了,没看到我开牌了吗?”“谁知道啊!现在这个球滚了过来,把牌都弄乱了,谁说得清哪张牌是你的!”“怎么能这样?你这不是作弊吗?”三个人互相推搡,全然没注意到那个孩子从铁丝网的破洞里钻了进来。显然,他已喊过很多声,见没人理他,所以自己进来捡球了。“喂!小孩,你干什么?”一个美国兵突然发现孩子,冲他怒吼道。孩子被吓得直哆嗦,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可恶,这球是你的吧?就是你触我眉头吧?”美国兵看看孩子,又看看仍压在牌面上的脏球,不知触动了他哪根神经,竟随手举起一把枪对准了面前的孩子。“喂,你开玩笑的吧?他只是想过来捡球!你今天喝多了!”“谁说我喝多了!今天还没喝多少呢!”三人又开始争执起来,拿枪者在醉意和愤怒之下抠动了扳机,一颗子弹迸出,射进了孩子的腹部。“埃。。怎么办,你打到他了!”“什么怎么办?又不是第一次杀人了!我是按规矩办事,一切侵入基地的非相关人员都可以当场击毙,这不是上头的规矩吗?”“你疯了吗?那只是个孩子啊!”“哼!我没疯!”拿枪的美国兵向前走了几步,对准孩子的胸口又是一枪,刚才还在痛苦的低吟的孩子此刻终停止了呼吸。“如果不让他死透,等他家里人找上门来,我们就都麻烦了!快,把这尸体埋了吧!”
几分钟过后,那片场地已被清空。三个美国兵离开了,孩子的尸体已被处理掉,地上只剩下一片没人理睬的血迹,明明死了一个人,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身为残疾人,又手无寸铁的李鸣当然无法对这件事做些什么,为了防止被美国兵发现,他躲在了一栋平房后。“我。。。居然亲眼看着他被杀死,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李鸣的手攒成拳头,牙齿紧咬着嘴唇,刚才那残忍的一幕宛如还回放在眼前。“哎呀,又死了一个么?”这时,一个渔民走了过来,表情平淡地说道。“啊?您说什么?”李鸣这才回过神来,抬起头看着渔民。“小哥,无论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可都别放在心上。这,是我们这儿常有的事。或许可以叫做‘特产’了吧。”渔民的嘴里叼着一根牙签,唠家常一般的说着刚才的事。“常有的事?”“是啊,前几年每年都会有人被他们喂枪呢。也就近两年好转了点,还以为他们转性了呢。没想到还是发生了啊,哎呀呀!”渔民苦笑着用手去挠头发。“这。。。这难道都没人管的吗?”李鸣惊讶地问。“呵,谁来管?我们这里可是美国爷和日本爷的地盘,琉球人说话,人家听都不会听。何况,美国人也不是滥杀无辜的魔头,人家也是履行公事嘛,是那些孩子自己不好,干嘛要跑进去惹他们呢?谁家的孩子死了,谁就认倒霉吧,那地方是靠近不得的!”渔民牢骚了几句,朝地上吐了一口痰,便悠悠然离去了。
李鸣仍呆呆的坐在轮椅上,他此刻才知道什么叫麻木不仁,原来这片土地远无他想象的那般美好。后来他又向一些村民打听过,回去后也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终于,他知道了掩埋在平和假象下的某些现实。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便以战胜国的身份在战败国日本大量驻军。近几十年美日关系亲密,大部分美军都撤出了日本,但在日本最南边的这个冲绳县却依旧存留着许多美国的军事基地。冲绳在亚洲和整个太平洋而言,都有着绝佳的战略位置,被人称为“亚洲之眼”。美国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到手的宝贝。它将冲绳、关岛和夏威夷三地平等的作为控制亚洲局势的三角点,如自家后院一般自由出入。近年来,坊间常有冲绳原住民被美军“误杀”和强奸的传闻,但这些事的真相都被日本最大限度的掩盖了下来。为了维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对于几条琉球人的性命,日本人丝毫也不会在意。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冲绳!血淋淋的冲绳!
回酒店的路上,李鸣一直魂不守舍。一场个别现象的命案,其实算不上什么。并非全体美军都如今日所见的这般残暴,被美国侵害到实际利益的琉球人毕竟只是少数。但正是这沧海一粟揭示了整个琉球民族的悲哀——他们,是没有主权的。美国人能对他们呼来喝去,日本人又对他们不闻不问,各种歧视像牢笼一样死死的锁在这个民族的关节上,使他们不得超生。或许在某些政策上,日本也能一视同仁的对待琉球人,甚至给他们一些优惠,但不可否认的,琉球人在日本的统治下是受到压迫的,他们无法享受到全面的平等。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有一处被笼罩在类似殖民主义的阴影下,于两大国之间的夹缝中苟且偷生。“如果是爸爸看到这些,会怎么做呢?”李鸣想起了他的父亲,那个穷尽一生,也在追求着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父亲。复杂的思绪,在李鸣心头炸裂。
“混蛋,什么琉球人!我们大家都是日本人!”这时,又一个刺耳的声音进入了李鸣耳帘。他正路过一个警察局的****办,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围着一个上访者大吼大叫。李鸣猜测着:这个****者可能是琉球族,他因为在某些事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想来警察局伸冤。大概因为情绪激切,一不小心说出了“我是琉球人”之类的错话,惹得警察生气了。“你再说一遍!刚才你说你是什么人?琉球人?你想分裂国家吗?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日本!稳定压倒一切,谁也别想制造分裂言论!”警察们破口大骂着,对那个可怜的****者拳打脚踢。李鸣已经再也看不下去,再也听不下去了。原来冲绳还有如此之多的,他未能体会到的黑暗。而放眼世界,正在痛苦的承受着这种黑暗的,又岂止冲绳一地呢?
很多事,在李鸣的脑海中一一浮现。有他本国的事,有中东和美国的事,也有[爱神]常挂在嘴边的事。“也许,我该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去审视某些问题了。”李鸣继续思索着,孤独的轮椅逐渐消失在了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