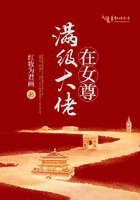第二天我是被闹铃声吵醒的,一缕光线从深色的窗帘缝隙挤了进来,房间还是灰暗的。这是我手机的闹铃声,手机在申尚风那边的床头柜上,我翻身过去按停了,12:30。
“你的闹钟真多呀。”他懒懒的说了一句。
“还好吧,你都按停了?”这是工作日里的第五个闹钟,前四个分别是7:00,7:30,8:00,8:20,这个闹钟是提醒自己要记得去吃午餐的,13:29还有个提醒午休结束了的闹钟。
“嗯。”他坐了起来。
“我抓的?”灯亮了,我才看清他后背上的几道淡红色抓痕,那像是指甲抓出来的。
“不然呢?”
“那你怎么不阻止我呀?”手指贴着他后背的抓痕滑动,是我短钝的指甲抓出这些痕印?我想不起来了,我短钝的指甲里没有皮屑、也没有一点血迹,他后背上有道抓痕是结着点点血痂的。
“你不相信我?”
“什么?”
“你觉得我跟其他女人做过?”
这个可能我觉得并非不可能,我在心里说着,唇却印在了他后背的一条痕上,“没有。今天什么安排?我们还去工厂吧?”
“去。明天去缅甸,你去吗?”
“我没带护照过来。”
“有带身份证就行。”
“真的可以吗?”我在深圳时就听说过有些云南人有特殊通道能绕过海关。
“嗯。游哥会在那边接应我们。”
“去哪里呀?”我看着他站起来,走向洗手间的背影问。
“帕岗场区,可能要待几天,你带几套方便走路的衣服过去。”他的声音跟身影一起消失在半透明的洗手间里。
尚风集团瑞丽工厂是一栋独立的六层楼房,坐立在两米高砖墙叠加半米高刀片铁丝网的院子中央,院子有五面墙,六条青灰、淡黄褐、黑背的犬在院子的各个角度拴着,咧着狰狞的牙齿,我在一些视频里看过这种犬,这应该是种警犬。每层楼有500多平方,一楼专门堆放未加工的玉石毛料,开了口子的,没开口子的,大的小的,裸露着石皮的,被深色油布盖着的。其他五层是加工区跟成品存放区,手镯、戒指、耳环、吊坠、腰牌、如意、平安扣、手玩件、摆件、十二生肖、观音,放在木质的或玻璃架子上,还有的应该是放在了那一个个深色的保险箱里。工厂有八十多个玉石加工匠,听说全是从腾冲、保山、瑞丽的琢玉高手,在30至65岁之间。我们在三楼见到了杨师傅,杨师傅快六十岁了,尚风集团玉石首席设计师,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给一座满绿翡翠麒麟摆件抛光。
“上官小姐,我们上次见面是在上海吧?”杨师傅在擦着手说道。
“对的!Wo+发布会上。您叫我小薇就好!”
“我还是擅长做这些摆件,吉祥物、生肖呀,发布会的那些配饰我还真不擅长,说真的,那些衣服也配不起更贵的玉。”看来他对那次被Wo+设计团队评价没有时尚感的事还记怀在心。
“是他们不懂欣赏,玉石做成吉祥物这些才更符合好的寓意。”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我对玉石、翡翠的了解还处于半桶水,我内心是认同Wo+设计团队评价的,能高调穿戴在身上带出去的时尚感产品会让产品溢价更高,让品牌更值钱,也会让股票上涨,但是那些低调的顶级富豪们可能更喜欢出自杨师傅手中的产品。
“哼。”杨师傅笑着哼了一声,我不确定他是在哼我,还是哼Wo+设计团队,没有回应。
“尚风你这次去缅甸,会去公盘吗?”杨师傅坐了下来,打开保温杯喝了一口,他的座位是单人皮沙发,坐垫折叠着两层,这是一张可折叠的沙发床,就安排在抛光工作台不远处。我在想,他会不会经常躺在这张可移动的沙发床上看着工作台,思考产品的设计。
“不去,这次带几个朋友去帕岗场口看看。”申尚风说道,我跟他坐在杨师傅旁边两张临时安置的折叠椅上。
“嗯,这样。”杨师傅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申总这段子怎么样?”
“他挺好的,上个月还跟思凯去了趟美国。”
“那就好,两年多没见他了。”
“你时间可以的话,我来安排,去加拿大、缅甸都行的。”
“下次他回缅甸,我再过去吧,加拿大远,就不去了。”杨师傅放下手中的保温杯,“那件事还没处理好吗?这么多年了。”
“差不多了。”申尚风说道。
“那就好。我还是想在瑞丽,在家里跟他见面呀。”
“嗯。”申尚风应了一句。
杨师傅口中的申总是指申尚风的父亲,申正义,现在是加拿大籍,尚风集团最大的股东。听说2007年他去了加拿大后,在加拿大做起了房地产生意,他的房地产生意是不纳入尚风集团财报的,也不知道做得有多大。申正义军人出身,听说还做到了少将等级,他卸下军衔那年正式下海,做翡翠原石贸易,据说跟中缅双方的军队都保有关系,甚至和中缅边界的武装势力也有联系。2007年申正义为什么把董事长位置等转交申尚风后一直没回国内,尚风集团内部决口不谈,我想尚风集团估计也没几个人真正了解个中原因。
“快十年了。”杨师傅说了一句,他眼中是淡淡的悲伤。
“嗯,我们在努力处理。”申尚风接过杨师傅的保温杯,往里面倒入新烧开的开水。
“我们为什么不去缅甸公盘呀?”叶师傅开着车,刚开出工厂大门,后视镜两个穿迷彩服的男子在后面招手,车窗还没关上,狗吠声一声声清晰地传入车内。
“有必要去的时候就去。”申尚风说道,“可以这么说,缅甸公盘、云南拍卖会的毛料都是我们挑剩的,或者说我们没兴趣的。”
“那有必要是指什么时候?有必要去制造话题的时候吗?”刘琳说过,话题会影响股票,制造就像Wo+发布会那种话题,还是一块原石毛料卖出五亿元那种话题。
“差不多。你还是挺聪明的。”申尚风看了我一眼,又把脸转回去,闭着眼。一般他不想回我话,或者在思考时就会是这个闭眼动作。我把脸转开,看着车窗外,叶师傅没有说话,他很少在车内说话,车内是一片平静,看了一会窗外,我靠着座椅也闭起了眼睛。
我们从银井村过到缅甸后,叶师傅便认出了游哥派来接应我们的人员,姜钰、台湾王哥、北京陈总、香港李哥和我们一起过境的,游哥没有来,派来了五辆军绿色的SUV,除了北京陈总带了两个人,其他三人都是带一个,不用说那都是他们各自的保镖。我们上了其中一辆,叶师傅坐在副驾位,我跟申尚风坐在后座。
我对缅甸的交通地理信息一点也不熟悉,对帕岗场口的认知也仅仅是以往查看过的一些资料,想跟申尚风搭话,他也是心不在焉地说了几句,昨天从工厂回来后,他就时不时沉入思考,或变得心不在焉回复我。叶师傅跟司机用缅甸语交流,司机听不懂汉语,我也听不懂缅甸语。司机从后视镜中瞄了我几次,然后跟叶师傅说话,叶师傅回复了他几句,我猜他是在问我是谁。
下午一点多,车队在一处饭店停下了,饭店是用铁皮搭建的棚子,像国内的工地房,又有点像国内的农家乐餐厅。六月底的缅甸差不多三十度的天气,棚内没有空调,几架落地大风扇呼啦啦地吹着。李哥首先受不了了,香港人习惯了常年的室内低温,他把一架风扇固定对着自己,不停地擦汗。
游哥笑着从一个房间里出来,他身边是一个看起来四十多的男人,穿着迷彩T桖,寸头,黝黑发亮的皮肤,五官倒是挺立体的,一米八左右高。
“辛苦你们啦!”游哥笑着说,“李哥等会我让饭店老板再给你搬个风扇过来。对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吴桐先生,这是台湾的王哥,北京的陈总,香港的李哥,申总跟姜钰都是老朋友了,就不用介绍啦,这位是上官小姐,申总的......女朋友。”
“那我们该叫桐先生,还是吴先生呢?”台湾王哥问道。
吴桐笑了,游哥也跟着笑了,“我是华人后裔,吴是本姓,桐是梧桐的桐。”吴桐说道。
我以前查资料,有了解过缅甸人的姓氏文化,缅甸人有名无姓,从名字上无法判断一个人的家族或家庭归属,他们只在每个人的名字前附加一个表示性别、辈分或社会地位的词。如果是男人,未成年时那个词叫“貌”,成年后叫“哥”,等到年长或者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后,便被尊称为“吴”。要说吴桐年长也不为过,能跟游哥、申尚风聚在一起的,估计社会地位也不低,就是如果他一出生就叫吴桐的话,那就真的是占了姓氏的便宜了。
“梧桐树上引凤凰,好名字。”北京陈总赞说道。
“哈哈,过奖了!陈总是北京本地人吗?您的北京腔很地道。”
“是的,吴先生经常来北京吗?”陈总问道。
“这倒没有,好多年前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
“陈总你还别说,吴桐先生还真是引得凤凰来了,他岳父是缅甸的莫那上将。”游哥插了一句。
“幸会幸会,也恭喜恭喜。”陈总笑着说道。
“就游哥你话多。”吴桐也笑了。
缅甸在2015年还是名正言顺的军权政府,大将、副大将下来就到上将了,今年才2016年啊,看来吴桐是真的配得起他名字里的“吴”了。
午餐过后,吴桐、游哥也加入车队,一行八辆军绿色的车,游哥的车带队,走在缅甸的公路上。我是被雨声吵醒的,睁开眼,车已离开了水泥公路,走在泥路上,天昏暗昏暗的。
“你睡醒了。”申尚风说了一句。
“雨下多久了?”
“半个钟左右。”
我看了一下手机屏幕,17:16。“这雨不会下到晚上吧?”
“不会,七八月份才是雨季。”
现在离七月也就剩几天了,我心里说道。
“我们今天在酒店住一晚,明天再出发。”申尚风说道。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酒店了。”叶师傅说了一句。
晚上住的酒店是五层小平房,酒店名字叫“一家亲”,老板是华人,姓顾,我们一行人刚进到大门,顾老板就迎上来,笑得很亲切,叫得也亲切,申总、游哥、吴先生的,这应该是他们以往行程里的固定住宿地。晚饭时,老板娘也被叫来了,丰盛的晚餐加酒水,大家都以明天要赶早路为由,没有多喝。
酒店不大,摆设也朴素,可是有着自己的桑拿房。晚饭过后,申尚风跟我说他要去蒸桑拿,问我要不要去,我们俩坐在一间狭小的桑拿房,赤裸着身体,围着白浴巾。我们已坐在里面一个小时了,蒸汽水雾弥漫着,我看不清申尚风的脸,他好像在闭着眼,我们没有说话,室内是静谧一片。
“砰砰!”有人敲门,一个女人用蹩脚普通话在外面问:“请问先生,要小姐服务吗?缅甸小妹,越南小妹,还有洋妞!”
我看了申尚风一眼,他依然闭着眼,身子动都没动。
女人又问了一次,“砰砰!”敲了两下,说的应该是缅甸语。
“我们不用!”我提高声音喊了一句。
“不好意思!”女人说了一句,然后嘴里嘟嘟嚷嚷着走了。
“你们以前经常住这家酒店吧?”我决定打破这里面的沉默。
“对。”
“也经常光顾她们吗?”
“她们指谁?”
“小姐们啊!”
他闭着的眼睁开了,“这重要吗?”
“不重要。”我怕也只是你经历过众多女人、小姐中的一个,这当然不重要。心里闪过一丝伤感,可身上的每个毛孔都被蒸开了,全身都舒展着,我伤感不起来。
“你从瑞丽工厂出来后,开始很少跟我说话。”
“你想说些什么呢?”他挪了位置,贴着我坐下,伸手要扯下浴巾。
我站了起来,套上内裤,换上浴衣,走了出去。刚刚女人在门外叫卖小姐服务的场景还清晰地盘在脑里,我还无法接受成为一个在桑拿房里给他提供服务的小姐。桑拿区在一楼,走出门口没几步被姜钰叫住了,他那标志性的沙哑烟嗓识别度很高。
“小薇,你一个人下来的?”
“你猜!”我假装俏皮地回了一句。
“哈哈!这也要猜吗?”他笑着说,“你知道这家酒店住的基本都是男人吗?”
“为什么?”他下半身裹着浴巾,白色浴衣套在两只手臂上,没有系带,敞露着胸怀,那是一个有着四块腹肌的胸怀。
“这条路是去帕岗场区的,亲自去场区的都是胆大的男赌石客,要不就是去开矿的。这些酒店就是为男人准备的。”他挤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当然,酒店里也不是没有女人。”
“是指在桑拿房服务的小姐们吗?”我说道,脸上挤出一个不以为意的笑。
“差不多。你不应该一个人去桑拿区的,是有可能被人当成是小姐拉走的。”
我笑了,看着他,他虽剃着平头,却是一个比申尚风好看、有趣的中年男人。
“申总没下来?”
“我跟他一起下来的,他还在桑拿房里,我有点不舒服,先回来了。”
“这样。你住几楼?”
“五楼。”
“这么巧!我也住五楼。”他按下电梯键。“你跟申总什么时候认识的?”
“2012年。”
“哦!以前没见过你。”
“你跟申总认识很久了吗?”我问道。
“认识几十年啦,我爸跟他父亲是战友。”
“原来这样。”
电梯门在五楼开了。
“我先回房啦!你记得尽快进房间,不要在走廊里晃悠!”他笑着说,脸上是两个酒窝,“明天见!”
我笑着向他的背影挥了挥手,滴了卡,进浴室里清洗湿蒸出来的汗珠。
车队开了大半天,下午三点多在一条河边停下了,这条河便是乌龙河,整个缅甸最宝贵的河流。
“新场口就在河那边。车就放在这里,我们坐船过去,到了那边坐大象。”游哥说道。
车辆停在一个用迷彩网搭起的停车篷里,不远处是三个迷彩帐篷,附近是穿着迷彩服的人在走来走去,像是在巡逻,他们背着枪在巡逻。
“明天一早再过去吧!现在过到那边也晚了,看不了什么东西。”吴桐说道,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子走上来,右手抬到了太阳穴位置。
这应该是一个军礼,这些穿迷彩服的都是军人么,我在心里吓了一惊。看样子这里有好几十个军人,申尚风第一次告诉我他做翡翠生意时,我就去搜索了翡翠相关资料,今天算是亲眼看到军队控制着翡翠矿场这点实情了。
“今晚委屈大家在小帐篷睡一晚,就当是是露营。”吴桐脸上挂着笑,“迟点会有专人帮忙大家搭一下帐篷的,不睡小帐篷的话,我们那几个帐篷里也有上下床铺可以睡。”
“床铺是士兵睡的吗?”北京陈总问道。
“对。”
我看着申尚风,让他来选。
“我们睡帐篷。”申尚风说道。
“我也睡帐篷。”李哥、王哥说道。
“可以选睡车上吗?”陈总问了一句。
“可以,但是车不能开着空调,只能敞开车窗。”吴桐说道。
“那我选小帐篷。”陈总说道。
“我还是老样子,床铺就好。”姜钰说了一句。
晚饭是在临时军营解决的,把它称为军营,因为在那三个大迷彩帐篷走了一圈出来,我看到里面堆着的更多枪支、弹药,这些以前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过。晚餐上了三个用酸笋一起混着煮的菜,上了一个汤,汤里还是用酸笋混合着鱼虾,主食是椰浆饭,可能是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大家的胃口都特别好,碗筷撤去后,围坐在一起聊天。
我们坐在矮脚小板凳上,同样矮脚的桌子上放着啤酒、香蕉、椰子、芒果,还有槟榔。啤酒被喝完了,吴桐示意人又搬来了一箱。
“有白酒吗?啤酒喝着不过瘾,喝醉了今晚才好睡觉。”陈总手中的啤酒瓶口凑近嘴巴,说道。
“这个还真是不好意思了,没有白酒。”吴桐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喝醉。”
“怎么说?”
“不瞒你说,这个地方偶尔会有克钦军来光顾。”吴桐说道,“那个场口是新开的,有不少人在盯着呢。”
“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吗?这么危险。”陈总说。
“应该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不是申总的话,还不一定有机会入股。”吴桐笑着说,咧着他的血盆大口,他刚嚼槟榔了。
我看了一眼申尚风,他笑着举起酒瓶,“来,喝酒吧。”
“富贵险中求啊!”李哥边碰酒瓶边说。
酒又喝了几轮,王哥开始打呵欠,围坐的七个男人当中,他年纪看着最大,我看了一眼手机,已过9点,这个军营是临时搭起的,没有拉电线,整个营里只有一台柴油发电机,供给着营里几盏灰暗的灯,吴桐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小手电筒,“这是申总公司的产品”,他笑着说。手电筒是强光LED,可以切换白光、紫光。
“我先回去睡了,还是申总好福气啊!今晚有美女作伴。”王哥说道。
我笑了,没有说话,作为男人堆里的一个女人,我最好少说话多笑。
“这也不是申总才有的特权,要是有女人愿意跟着来,陈总你下次也可以带着来的。”姜钰说道,我看到他的脸在灰暗的光线下从陈总那边转向了我。
陈总笑了,桌边的六个男人也笑了,我想他们可能多少会把眼光往我瞄一眼,低着头吃芒果。
散场后我跟申尚风说我要去洗澡,说是洗澡,其实仅是用湿毛巾擦身体,洗手间是临时搭起的棚子,我猜这群男人大部分时候应该都是就地解决,水是经过过滤的乌江河河水,老申用缅甸语让人帮忙烧开了,开水被装在一个塑料盆中,申尚风站在帐篷外面,我在里面脱下衣服,用滚烫的毛巾捂在用卸妆水卸去素颜霜的脸上,擦了一遍身上的汗迹,换上干净的内衣裤、上衣。
“你要洗一下吗?”我拿着换下来的衣物和毛巾走出门帘。
“男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讲究。”他说道,走过来翻找我手中换下的衣物。“这个不用带回去了,女人的衣物也不要在军营里挂晾。”他点亮打火机,点燃了手中拿着的衣物,那是我换下的内裤。
“你睡着了吗?”躺在帐篷里,我问道。我喝了三瓶啤酒,不知道是啤酒浓度不够,还是我的酒量变好了,酒精不能帮到我入睡。
“没有。”申尚风说道。
我摸起旁边的手机,手机是进入到帐篷里才开始补充电的,我带的两个移动充电宝快没有余粮了。“凌晨1点多了。”我说道。
“嗯。”
“你们这次来是要合伙买下场口吗?”
“准确来说,是他们要入股。”
他们应该是指李哥他们了,“公司有股份了吗?”我在尚风集团的财报里可没看到这点。
“公司不需要有股份,我们有就好。”
“我们是指谁呢?”我想到了佛爷、姜钰。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你最近问题有点多。”他把腿翘了过来,缠在我的腿间,左手挽在身上,“早点睡吧,睡不着也闭着眼休息。”
第二天醒来后,我用瓶装矿泉水擦了一下脸,涂了层水乳,补画了一下眉毛。“你倒还是挺爱美的。”申尚风站在帐篷外看着在帐篷里的我完成了这一系列操作。
“可我黑眼圈还是很明显的!”我笑着说,昨晚在朦朦胧胧中眯着眼,然后迷迷糊糊地就醒了。
说是坐船过河,所谓的船其实仅是木制的简陋船身,没有桅杆、帆桁、帆,船上装着一个马达,船板上还放着两根撑船用的竹竿,在木板搭建的简易码头登船后,我跟李哥他们一样坐了下来,船开动了,在河面划开一道道浑浊的波纹,申尚风、姜钰、游哥、吴桐他们四人和其他人一样站着。
过来接我们的是两辆摩托车,六头大象,大象背上拴着铁棒焊成的椅子,椅子上放着塑料包坐垫,摩托车跟大象的大半身一样都沾着黄色的泥土,其中一条象腿拴着一米多的铁链,拖在地上沾着泥土,每头大象各有一名男子跟着,手里拿着带钩子的棍棒。
“这个象背上能坐吗?”陈总说了一句,把我心里想说的说了出来。
“去泰国旅游不都这样子坐吗。”李哥说了一句。
“下了雨,这边又靠近河床,车子不好走。坐大象走一段路到结实点的地面,会有车辆过来接我们的。”游哥说道。
申尚风驾轻就熟地坐上象背后,伸手拉着我上去了。姜钰、吴桐、游哥三人分别和李哥、陈总、王哥坐一起,还有两头被申李陈王的保镖两两坐了上去。驯象师,申尚风跟我说那几个手拿带钩棍棒的男子叫驯象师,驯象师拍了拍象头,大象迈开了步子。这是我第一次坐在象背上,我坐上去时好像是踩到它背上什么地方了,它把鼻子往上仰了一下,不过很快仰起的鼻子被驯象师钩住了,坐稳后我才看清它背上的一道结痂,混着泥土和毛发,我刚可能是踩在这道结痂上了。大象走得很慢,走得很吃力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下去走路可能都比它快,驯象师是在地面和大象一并走着的,他们拍着象身,用我听不懂的缅甸语在催促。
我把下去自己走路的想法告诉了申尚风,他摇了摇头,“怜悯在这里不适用,还是听吴桐安排吧。这些大象常年在场区走动,慢点走,不会有事的。”
“嗯。”我点着头说道。怜悯在这里不适用,我琢磨着申尚风的这句话,这话无疑是对的,跟商人讲怜悯是可笑的,这还是一群赌石的商人,“一刀富一刀穷”,他们比谁都清楚当他们“一刀穷”时不会有几个人出来怜悯他们,这不仅是场关于钱财的生意,这还是场关于人命的生意,“富贵险中求”,李哥的话也盘旋在脑中,大象又算什么,只不过是做这场生意的工具。
走到一个斜坡,我们坐的这头大象好像是滑了一下,我坐着的屁股被抛空了半个。大象停住了,驯象师拉了拉大象腿上的铁链,大象还是没动。后面的驯象师喊了一句缅语,驯象师随即拿起带钩的棍棒,朝大象脑袋砸了一下,大象还是没往前走动,头却开始晃动,申尚风朝驯象师喊了一句缅语,又朝我喊了一句“你抓紧扶手!”驯象师像是又砸了一下大象的耳朵,大象头晃得更厉害了,腿也开始动起来,往斜坡上奔走起来,跳了一下,它这一奔一跳,我只感觉整个身体被上下颠簸着--我被抛离座位了,跌落在泥泞的地面。
在我们后面的叶师傅已经跳了下来,“上官小姐,你没事吧?”
“没事。”我只感觉到手掌、手臂在胀痛,意识到被抛离座位那一刻,我伸出手掌撑在在地面,还好地面是湿土。
“你没事吧?”申尚风从前面折返过来,问到。
“没事。”
“真没事?”
“就是手掌、手臂有点痛。”我笑着说,眼角湿润着没忍住的泪花,痛倒不是很痛,被吓出了眼泪是真的,跌落在地面后,看到我们后面那头大象也要往前奔走,幸好被及时止住了,不然我可能就被它踩在脚底了。
“还敢坐上去吗?”申尚风伸手擦了一下我眼角的泪,说道。
“听你安排。”我想伸手去擦眼泪,他拉住了我的手。
“手上有泥。”他转向一边的叶师傅,“你去开辆摩托车过来吧,跟游哥他们说没事,让他们先过去。”
“好。”
申尚风扶着我站了起来,手上是泥土,我屁股上也沾着泥土。他过去问后面两头大象的人拿了瓶饮用水,我伸手往后扒下裤上成块的泥土,张开手掌,他把饮用水倒在上面,大半瓶饮用水被我洗手用完了。
叶师傅开着摩拖车“嘟嘟”停下了。
“你载着小薇开车,我坐你的位置。”申尚风说道,“我不会在这些泥路上开摩托。”我知道他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
“好的。”叶师傅应了一句。
摩托车轮跟象腿一样沾着泥土,我把沾着泥土的屁股坐上了摩托车后座,手却不知该往哪儿放,手捉住了后座架,我的身体往后倾斜着。
“坐好了吗?”叶师傅问了一句。
“好了。”
“那我开了。”话音刚落,摩托车就往前开了出去,我只觉得我的身体又往后抛了一下。
摩托车开得不快,却也赶在了大象前面,扭头往后看,可坐在摩托车上可扭转的角度有限,我没有看到申尚风,他坐上了叶师傅的座位,跟李哥的保镖坐在了一起。
“申总还在我们后面,你不用担心。”叶师傅说道,他大概是从摩托车后视镜看到我扭头往后看了。
“我没有担心啊。”他笑了,我从后视镜看到他脸上笑了一下。
“上官小姐,其实这次你真不该过来的。”
我迟疑了一下,“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我,“你去过矿区吗?像山西那种煤矿矿区。”
“没去过。”
“那你对缅甸翡翠场口了解多少。”
“不了解。”我了解到翡翠开采方法是十分落后的,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需要有经验的挑拣工守在挖掘机旁边,挖掘机倒下一车泥土石后,再上去挑拣,把翡翠玉石挑选出来。
“像你这样的女人是不应该去场口的。”
“我这样的女人是怎么样的呀?”我嘻嘻地笑了出来,问道。
“我跟申总十几年了......你不算最漂亮的,但算是特别的一个了。”他说道。
“是吗?怎么就特别了?”我笑着说。
他笑了,没回答。“前面就到了,他们在前面接我们。”
前面是几辆沾着泥土的轿车,吴桐、游哥他们站在车旁边,吞吐着烟雾等我们。
“申总在后面,很快就到。”叶师傅汇报似的说了一句。
“上官小姐你没事吧?”姜钰看着我问到。
“没事,谢谢姜哥。”我说道,眼睛看着申尚风将要过来的路,他们那三头大象正在翻越一个泥泞的坡路。
车辆行走的路坑坑洼洼,黄色的泥土混着石子,树木的残枝,开了不到半个钟,是成片成片裸露的泥土和石头,倾倒出一个个坡度,推造出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平地。偶尔才会看到一点绿色,那点绿色被一堆泥石挤压着,部分身体已被泥石覆盖了,剩下的部分身体在歪着。我挪腾了一下身体,才看清车窗外的砾石坡上那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坡最上面是一辆挖掘机,挖掘机在上面在准备倾倒泥土。
下了车,吴桐在前面领着我们走,和我们一起走还有十个背着枪的穿迷彩服或军绿色套装的男子,申尚风和吴桐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吴桐和申尚风在回复着李哥他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笑声不时响起,我听不清他们的交谈,也无暇去听他们的交谈,我的眼睛已被眼前的一切吸引住了,跟着队伍的脚步往前走,目光在两边不停地扫看。
到处是被翻出来的泥土,裸露着上身、全身衣服脏脏兮兮的人,弯着腰在敲敲打打着石头,往这边丢过去,或往那边丢过去,或跟身边的同伴对着石头说几句。队伍在一个坑边停住了,一个裸着上身、穿着短裤的男子抱着碗口粗的水喉,冲刷着旁边的岩层,坑里还有四个人,穿长裤的腿站在泥水里,双手拿着铁锹在泥水中翻找。矿沟、砾石坡、沟壑、积水、破旧的帐篷,还有成堆的垃圾,三五只裂开了的针筒,还有几个看到我们后匆忙躲进破帐篷里的女人。
我看了旁边的叶师傅一眼,他和我一样走在队伍的后面。“场口里也有女人?她们在这里做什么?”
“你能想到的她们都做。”他平静地说了一句。
我瞪大了眼睛看他,这里几乎清一色的男人,就这几个女人也敢......还是说还有更多女人?那些针筒是做什么用的......
“在这里少问这些。”叶师傅在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我看了看他,没说话。申尚风他们已在前面的棚子里坐下了,“这个场口还挺大的......”“毛料到时我会安排人运出,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先挑了,剩下的再弄去公盘......”
“你在看什么?”申尚风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我正在看着窗外往后退的泥石坡、不时出现的帐篷、人群,我们坐上车在回程中了,我在想还会不会有机会再来看看这里。
“看窗外啊,太震撼了。”我说道。
“说说你都看到些什么。”
“你看到的我应该都看到了。”我说道。
“哦!那你说说我看到了些什么。”
“原石,毛料,和财富,一大笔的财富!”我感觉自己声音里带着点不忿的激昂。
“就这些?”
“对啊。”还有随处可见的泥石地面,随时可能被石头、泥土压死的矿工,毒品和做***的女人,你要我一一说给你听吗,你会感兴趣吗?你不早就都知道了。
“你还有话憋着没说。”
“场口的那些针筒,跟帐篷里的女人,”我跟他说了我在场口见到的针筒和女人,发觉叶师傅正从后视镜看着我,他估计在屏着气认真听,“一定要做到那样子吗?残忍的压榨。”犹豫再三,我才把“残忍的压榨”说出口,他一定不喜欢听到这样的形容吧?
“毛料被拍卖前的事情我们干预不了,我们有股份,可以收益,至于场口,没有经营权。”
“经营权在吴桐先生那边?”吴桐后面还有谁,我在想,游哥是缅甸人,他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差不多。”他的手伸到我的后脑勺轻拍了一下,落在我的脖子上。“过来缅甸,你没有被吓到吧?”他在转换话题。
“我胆子没这么小,”我说道,拿下了他欲继续往后背里探索的手,叶师傅跟缅甸司机还在前面坐着,“我觉得挺好玩的,跟在深圳完全不一样的经历。”
“你喜欢深圳,还是这边?”
“当然是更喜欢深圳。这边也说不上不喜欢,我觉得像两个世界。”血腥的鹿酒,野蛮的开采,目无法纪的毒品和***,这边像是在文明边缘游走的世界,我没法想象自己长期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我觉得自己会活不下去,活不长命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世界,我都习惯了。”他说道。
我看了看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车内陷入了沉默,我发觉他被我拿下的手掌已盖在我的手背上,手指已扣进我的指缝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