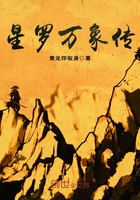常言说的好:“头三脚难踢”,建立镖局的头三脚便是争镖帖,亮镖会和跑这头一趟镖。
争镖帖为了获得官方许可,亮镖会则是给江湖上的朋友,买卖主顾看的。
看什么呢?自然是镖局如何气派,兵刃如何锋利,人脉如何广,财力如何雄厚,镖师如何厉害。
只有关系够硬,自身本领扎实,亮镖办的风风光光的,才会有人找你做生意。
所以亮镖也有了一层打架的意思在内:只有真刀真枪打赢了几场,见了血,才算是真有能耐,让人佩服。
所以江湖上有个规矩——今日若有争斗不算是结仇,而是给你捧场,让你显显本领,是帮你。便是之前释门镖局开业,道家也要派人登场,输上那么两场,给足面子。
而与镖行要好的生意人,甚至是入股的东家,都会出钱找几个当地有名的武术家来碰一碰——当然,花了银子就是买你输,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这镖行的买卖能开住。
此时的镖局牌匾已经立上,上写泰一镖局四个金漆字,乃是名家笔迹;四周悬有红花彩牌,各有“陶朱事业”,“四方来财”等吉祥话,前设有高大席棚,坐定其上都是士农工商中的头面人物。
席棚左侧是三排兵器架,摆定刀枪剑戟各色兵刃,又有骡车马车几头在一边拴着,轿夫车夫也一身短打扮,紧扎绑带束腿,精神漂亮;右侧则有几张八仙桌子盖着红绸,上摆金银元宝成山——这是头躺镖要保的货物,按规矩,只能是金银。
再朝前看,是一片空场,用夯土垫出小腿高矮,若是比武,便在其上较量。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能见到贺果和一干俗家武人也在其中。
只是今日镖局开业,这镖行的人却都不见喜色,都绷着脸,只有镖主孟方在席棚上强作欢颜,与众位名流绅董交谈。
先有几位镖师走到台前亮了几手绝活,或是刀或是剑,着实有些本领,引来一片喝彩声,等他们下去,才到了真正比试的时间。
这亮镖的规矩是有人登台,镖局负责接下,打不过接不下或者压根没人登台,便是丢了大人,这镖局便基本算是开不成了。
若是强开,走在十三州大路之上,便是随便一毛贼都要取笑一番。
这泰一镖局倒是不担心没人打擂,没待这头趟镖的雇主找的人上去,便呼呼跳上两个壮年汉子,两人怒目而视,都要争着第一个登台,差点就先动起手来。
泰一镖局这边的武事由张乐主持,观察二人身法动作,倒没有什么高明本领,只不过是乡下把式。便让镖师登台,三五下连胜了二人,却又有人抢着登台,便是真正有功夫的把式匠了。
在张乐的指挥下自有岳呈的门人弟子将其一一胜过不必细表。今日倒也奇怪,不见了一干僧侣,眼见着就剩了贺果、程连几人了。
程连今日登台,手中拿定的是一对龙头金挝,也不搭话,就摆定架势等着泰一这边来人。
张乐知道此人难斗,众位师弟恐怕不是对手,也上得台来,仓啷啷宝剑出鞘,与程连战在一起。
这刚一交手,张乐就觉出不对,按说此人还要高过何其多一线,实在是劲敌。但今日却似乎心不在焉,架势里透出一股犹豫和不安。
眼见短兵相接,程连却悄声开口,“何其多回来了吗?”
“这倒要问你们,”张乐也压低嗓音,剑式花哨,却不往人身上招呼,“我师叔他去哪了?”
“他......”程连话语滞住,不知如何开口,“我只知道师哥没擒住他。”
张乐冷笑一声,并不相信。
“是真的,”程连急忙辩解,却知道自己理亏,难以取得信任,只得说道:“贺果还有高手相随,你们小心。”
留下这剑头一吷,也不管张乐听懂没有,自己在下盘故意留出个破绽,显然是不想再打了。
张乐自然会意,探腿横扫,实际用的却是推送之力,将程连“请”下擂台。
他拱手抱拳,朗言向诸位乡亲说道:“方才这位公子真是英雄少年,前途不可限量,鄙人也是侥幸得胜,惭愧得紧,惭愧得紧啊。”
四面作揖,却不按规矩下台,打定的主意是要替受伤的师父挡下恶仗。
这回上来的人却不是贺果,而是一个壮汉,两眼通红,青筋泵动,竟然与之前和岳呈交手的那人有八九分想象。手拿一独脚铜人娃娃槊,和那六牙白象的形制也是十分接近。
见到此人,张乐脑海中立时有了一个猜测,终于知道那堪敌老师的人是谁了。
他开口问道:“来者可是交州的响马,岭南双虎之一么?”
“没什么双虎啦!”那人声音沙哑,眼神充斥着仇恨,“你们把我哥哥打死了。”
张乐冷笑出声:“却不知何时这山中的大王也改信了佛法,替小人卖命。”眼神看得却是台下的贺果。
贺果面色不变,微笑点头向张乐致意。
“这你可管不着。”
岭南独虎的心中充斥着仇恨,口中喝骂,扬起巨槊,便向张乐砸来。
槊是最古老的兵器之一,形制多变,但皆非巨力猛士不可使用。独脚铜人娃娃槊,便是说这槊头是婴儿头颅那么大的实心锤,槊脚则带钩藏刃,使用起来不仅要有巨力,还富有技巧,不然难免自伤。
这猛汉力大无穷,又是报仇心切,将一柄巨槊舞得是虎虎生风,便是砸在夯土之上,也要溅起一片烟尘。
张乐擎剑苦苦支撑,几个杀招使出却都被猛汉轻松化解,仅凭轻功过人才未受伤害,却也是险像迭生,始终挣扎于成为一滩肉泥的宿命之上。
他这才知道自己说到底还是本领不行,强要出头,不仅一条性命怕是不保,这镖行的买卖,门户的声誉怕是也完了。心中生出悲意,自伤自叹。
但听得身后有声音入耳:“攻他胸口。”
张乐不及细想,手中便是青芒一抖,如花蕾绽开,罩向猛汉前心。猛汉挥槊急挡,却终归是慢了一步,被划开了尺余长的一条口子。
猛汉连声怒吼,受伤更是激起了他的凶性,兵刃武动愈急,夹裹风声仇恨,一齐砸向张乐。
张乐连连躲闪,重新陷入了被动。没了声音指引,反倒让他一下子不知如何对敌。
“你这娃娃太笨了!”那声音再此传来,显得无奈,“让你刺胸口,你便一直刺他胸口就是了,那是罩门所在。”
张乐又听见声音,就如遇到救星一般,也不管他怎么调侃自己,便依着照做。
只见他剑法接连变换,从格挡游斗变成了刺击撩挑,招招不离前心方寸之地。
猛汉还真就被这简单的破解之法整得无计可施,显出狼狈笨拙。就如同大姑娘遇到了流子混混,扭扭捏捏再挥舞不开大槊,而是竭力招架。
眼见着场上攻守的形式互换,一团银光裹定黑云,煞是好看。看热闹的百姓大气都不敢长出,为这白衣的侠客捏了一把汗。
眼看几十招过去,二人都不复初时灵便,突然猛汉不再闪避,而是低头主动迎了上去。
宝剑轻而易举穿过了喉咙,那大汉却恍若未觉,手里的娃娃铜头猛然摆回,直接砸到张乐胯骨轴上,将他打飞出去。
他似乎还想要说什么,咧了咧嘴,但胸口和嘴里都堵满了血,只是咕咕冒出了几个气泡。
壮汉索性闭口不言,蒲扇般的大手拍了拍胸口,如山崩般轰然倒地,再无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