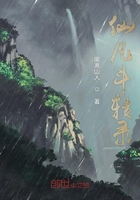我们原先也不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老霸着一个地方,告示下来了全县都要迁走,去往东海之滨,富庶而美丽的乡土。
不要讲故土难离背井离乡也不必说破家值万贯要装几个大车小辆,造福一方,免了,县衙不是不走要先走一部分中间走一部分,最后走一部分。最后的时候,府里和京城委派的人手一样要押解着所有滞后的人员一样流离失所,算走运了是古鲁国所在地礼仪之邦,他乡堪行,到了新土哪里合适就在哪里安居,这不好规定,三户一村十户一落,那时候有了自由。
洪洞县老鸹窝大槐树底下有一口老井,从这里离开的人们已经记不清井的年岁了,水甘水清水涌就是好水,再怎么旱这井里的水都不会掉下三尺。学究们憋着不知道哪股子气讳莫如深,那口井的来历就成了秘密,也成了自由的土壤谁都可以来刨上一锄头和挖上一掀土,各种传说都有也都有人信,最后只有一个象形的井字裸露着,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中原。
故乡的人故乡的路故乡的山和故乡的野花杂树和故乡的井,人都要陆陆续续地走,他乡或者相见已经是他乡之人,或者不再相见俱成了异乡之鬼;路都褶皱到了田野和山岭中,是荒路也是新路,是空穴就要来风,或许有和我们迁徙一样迁徙过来的人,路是老路但也成了新路;山水润人,这是一层亲密的关系,远不得近不得互相照顾得很好,土地是中间善于说话的人,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孬,好了一次会受到十次的詈怨,两次的不好一次的丰足就感恩戴德了;风景到处都有,漫长的路程中更会一曝一寒,它们只在眼里进入不到心里,有些年轻人会为爱情哭泣,但更多的人会为贫穷而蹙眉;井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就是个精灵,这个精灵把自己养大养成符合它的现在,现在却要拱手作别。
背井离乡,再见了我的井,我的灵魂,没有说背山离乡和背树离乡的,认识了井和更多要认识井,井的面目就模糊了。没有井就没有真实地生活过,搬了数次家的人都知道每一次搬家都是一层蜕皮,抱怨是随口就来的情绪,若不是还有子孙还有物质这两样东西烘托着自己,自己已经把自己丢了。
临行前总要再喝一碗家乡的井水,喝不完就泼在老槐树底下,所以几百年过去了那个场景还记忆深刻,水还是甘甜的清水,喝着喝着就哭了或者喝完了把碗让给别人自己抱着老槐树痛哭开了,树不再是当年的那棵树,井也是新的井,但总是认为它们还存在,一直存在。
前车之鉴,才开始上路的几家没走半个月就跑没了人影,现在要栓起来,只栓男人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中间是一根长长的绳子,两侧是随着绳子走的一家老小。开始时也许是爹娘妻子涕泪见,尘埃不见干壕桥,后来就寂静无声,绳子就像命运一样把人带到远方。内急了就要求官差大哥松掉绳子就近方便,解手,就是这么来的。
走走停停,自身带的粮食不够,途径村庄小镇的粮食也不够,有时候就在春天住下来,借来了种子种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秋后收成了再上路。一条路走十几二十年的都有,有的老了或者病死了,没耽误生育更多的孩儿们生下来被母亲抱在怀里风里和雨里。大部分人都达到了目的地,死掉的不少逃跑的依旧存在,迷了路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就偶然进入了某些结界之内的,成了世外桃源。
大部分官差成了行路人,和迁徙者分不出彼此来了,后来就在民众中指点那些素有威望和热心公益的人负责,再后来迁徙成了一种信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那时候很纯粹,一心一意在路上在行路,真到了的时候反而怀念那段岁月,后来不再有一根绳子拴着却拴在了心上。
现在谁还有那根绳子呢?
凿壁偷光也像是一次迁移,路程更长时间更久跨度更大,投入更多的身心,这是仅就这方面来说的。从另方面来说也不是偷渡而是两厢情愿,要不你就不知道光认识不到光或者想凿壁偷光也凿不了,早就印证了心照没有宣,这是第八步的艰难,深入内里了,顺风顺水了,扬鞭起航就可以到客栈到码头,不是这样。
从我这边看,还在很深的郊野,到那座城池还有不少的距离。我不知道,从你那边看已经到了光芒的芒上,撒射出来的一些光条光段,就要接近了的。真正的相信是活在身上,我做的事我说的话都不出你的格你的范畴,常在身边常在心头,可现在这只是一种感觉,即便这感觉有了根底。我想的是有个地方,这对于意识和感觉是一种不确信,是没有在腠理之中的空虚。
有时候感觉太大了碎成云块拼凑不起来,一个一个自己看着自己,身体说那要通泰清爽松静自然,接近黑暗黑暗对自己形不成压力,我的污秽只是颜色不是质地内里,自由自在。就如智慧不是智力,它其实是一种道德。
心要紧一点维系在一个某处,这时候却又产生了两个情况,一是这个某处又成了身体或者叫凡心,莲花一样守着的,可在高处还有一双眼睛那才是守护,那个眼睛的主人很娴熟的功夫是连线,什么都可以连成线,上中下左中右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时间心情物质意识牵挂你我他源头过程和流向人神园子,诸天诸界和人界。一是已经贫瘠和疲惫,步步把自己赶到角落或者那是巨石和巨石之间的一道缝隙或者只好装进瓶子里。而瓶子还是世界,我在你里面好呢还是在外面好,打不定注意。小的时候也为此犯愁,都有自由都有风都有距离,随性在细微而虚空的地方任意走失,没有走不动走到后来就一定是深渊。或者看着瓶子继续小,在所有记忆的深海它是其中的星空最后的一个点。
这需要一根线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这需要心里的一个殿堂想到它它就是我的光,光是千万方向的折返,这其实说的是灵,当然还可以更细微,就是一双眼睛,给与自由以自由空间的不变,给与明灯不灭的放心安然厅堂。我从来不是一个人,我何时何地都会有他,这才是根基,根是线基是光,圣灵和己灵的交融相合,嫁进了门和娶进了门,都在我的门里面。
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我的界壁已经有城墙那么宏伟,现在破障是破除的自己,有些观念越往里面走越坚硬,几句话或者几个线条几个光点就分成了两个界。意识是一口深井,从最深处咕嘟咕嘟能感觉出那水的情感色泽来,却无法靠近。我们用得着的意识有时而穷,和我们相信底下一定有甜美的清水之间有深深的距离,这是不被意识到的很多意识而每一个意识明晰通达之后或者将颠覆已经有的意识。
如果扁压成一线,也许就是尘内尘外之分。把身心看成一个(身)灵看成一个(心),如果它们各自找安处(对应的自己的安处就是态度),还就意识来说是身在尘外心在尘外或都在尘内或哪一个放在哪一方为好呢?都是滚滚世界之内的,安顺没有渴想日子稍可也许是可以的,很多人也这么过,但无不有焦灼和浑浊的气味,走过的风里明显闻得出没有安宁和顺遂。或者就悲剧来说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也不知道什么是悲剧更多的是按着自己的见解妄加分析而那往往并不是主要原因和原因的主要方面,蒙在鼓里和闭在一座黑房子都是一个意思。
远走高飞了和避世而居了只是形式,真正的尘外是所有美好的实现和永久,美好只是一个底线,类乎是托着的大地,真正的不可思议。要知道包含所有美好的世界,建造这个世界的胸怀是怎么样的大能量是何等的丰足智慧是无比的周彻运行是何等的合理而顺理成章。也品尝了真正的自由,身心灵是一个灵,光明温暖。自由是指的自己就是原因就是对自己的说明,就像我深深的知道你不用再自我介绍了,你的存在早就存在在我的存在之中,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你的那个样子,彼此不用说明心思泉涌中是我们的一切。自在指的是自就是在,在就是自,你不但是心意你也是环境,自在也就是永在也就是用在;终于有明朗的一天,我就是你的环境是你的呼吸,现在你就是我了,没有朝思暮想而是清新如意,时间已经是忘掉的水,不渴不饿,所有的就是劳动和吟唱,在就是用用也是在,也没有了秘密和追求,生活就是实现。
这个地方就在墙后面就在我所以凿墙的光中,夜已深,从月牙儿初上到现在横斜在西天际已经很多时间过去了,没有出门也没有打听,隔壁通常都是灯火通明的,这次凿开也不会例外。
还有薄薄的一层土,我甚至已经感觉亮光已经裹住了我,万不可大意,免得被对方发现,一针一针的挑土,不发出任何动静。不很多求,只要光能撒在我的书本上就够了。
就可以彻夜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