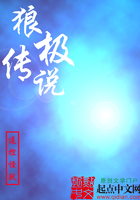有山有水有人就是好地方,乐山乐水乐的是人。
众山被承受,一些人在那里居住,众水的泉源行驶在梦境之中,人们不知道逃往到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没有山也没有水,只有一座风雨如晦的大城。风雨飘摇,颜色苍灰,好像是灰尘粘起来的,吹一口气或者被一只长尾的巨兽的尾巴扫到一丁点,甚至披着战甲的神人的一声嘶吼都会让这座城坍塌下来,灰尘浓烟一样扑向虚虚的尘土。
传说中的未成城是最后的决战之地,就算是天开了人们也看不到这个地方,决不允许千宫万殿云霞金碧却围绕着一个废墟这种情况出现,所有的生灵在有知之年没有例外地都在准备着这场战争。
不同的是有些生灵知道,有些生灵不知道,不管知道不知道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没有人可以远走高飞。
知道的只是少数,不知道的是全部减去少数的大多数。
人类这个物种也被计算了进去,人类参与其中的力量就是他们的死亡。
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这是用时间来分割的。如若一百年不够那就二百年五千年,现在活着的人五千年之后大约全都死掉了,新生的充斥在现在的时代,新生的五千年之后又换了新生的,如果把这个时间延长,或者是用某些星系的调整造成一种闭区,万万亿兆的成长年限年轮,收集起来的死亡就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死亡有力量在于他们的灵魂,灵魂上有记号,终其一生是怎么活着的,这被做了标记,这时候不用哄抢了,该去哪里去哪里,进入不同的阵营。
哄抢是在生前,不同的观念信仰和态度都说我是最好的,你要这么活你要那么活,不在于你想怎么活这几乎没有什么参考分量而在于你究竟是怎么样的活法,我种了庄稼却都被虫子咬了,这使我很伤心,我不想种庄稼了,我后悔我种了庄稼。
每一个庄稼,不管高粱大豆葡萄杨树,我都有一粒种子种在你生命的开始,以为你们可以觉醒这粒种子,那才是我的庄稼,但你们却成了别人的庄稼。
什么叫饮鸩止渴和为祸欲烈,那就是我,你最早的先念在我这里,种了千世万世,我想让你成长为我喜欢的模样,但没有一次成功,这让我无比的愤怒。
大战在即的时候,当世人的人觉醒,不在当世的是最接近当世的那一生觉醒,我种了你千百世,那不能觉醒的九百九十九世和九十九世成了灰,要命的是这灰,是灰组成了劫和僵,成了对立阵营不可不重视的力量。
我期望你的觉醒,我也有大能让你唯一的一次觉醒可以觉醒起九百九十九世和九十九世的光和明的力量来,可以对抗无数倍无数倍的劫和僵。
但总是得不偿失,流动到我这一方的力量总是太少太少。
伤心之余我立了一个榜样,竖起了一个标杆,算是取巧吧开通了简易的觉醒之道,然而腥风血雨泥泞蹉跎来到我身边的人还是不多。
一则是有法无渡一则是有渡无法,渡和法不能珠联璧合。我给了你法你却不想觉醒,或者是想觉醒的找不到法,其实渡和法都在你的身边,我化身百亿就住在你的心里,我甚至是那一粒种子。
我是你的种子,我是你的光。
光可以燃烧。
贵雷妆顺手一挥,七座顶天立地的门一字排开,门挨着门,中间八个不同的门柱相连,有的木有的石有的滚着黑烟有的蓝莹莹有的光闪闪,还有一个是活着的生灵,不知道是怎么极度的变形挤了进去变得又高又细。
这是敌方的必经之地。
潮水般的魔军阴军天军冥军人军混杂在一起形成七道黑锁链,疯狂着呐喊着冲进七门,在门的边缘,巫师助阵,不停地打出一道又一道污光和荒光,去污染和扩大门户。
嘟嘟嘟,怪异的号角声让生灵血脉贲发,从后方传来。
天技族从长在胸口的皮口袋里不停地掏出手机似的镜子抛到门里面,冥木族门上开窗,一扇一扇不同形状的窗户镶嵌在门上,敌方的天地人魔冥纷纷穿窗跳户奋勇向前。
一扇门是拉,把进入门内的敌军拉长拉细,像是绳子一样,根本无法同时看到头和脚,一条胳膊就有几公里长。一扇门善于缩,把敌人化形为芝麻一样大小,就好像突然一脸盆芝麻从门里面倾洒了出来。一扇门在于复,门内还有门,门内还有门,无穷无尽。或者门后是血池或者门后是幻境,某一个场景一场又一场上演,没有止息。其中一个是光明门,似乎所有的太阳都来到了这里,吵吵嚷嚷,进了门先是眼黑后是脑袋嗡嗡叫。
魔王第七把刀站在平常门后面,作为留手,魔王第七护法化身为他脑后的一根白发目不转瞬的守护着他。魔王第七把刀也让七护法把戒指戴在了手上,虽然持有不同,但发挥出来的威力还是一样的大,没有隔没有阂就是最快速的到达。
战争开始魔王第七把刀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小人物,就好像芸芸红尘中的一个组成,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重要,有时非常重要,看着委实渺小,但又连接着天地之心。断去了外也切断了内,把不重要的重要,把重要的不重要,好像与别人并无区别,但这个区别却非常之大。
一句话的交代也是交代,他在那场战争中英勇就义,或者看着他一路走来,艰难跋涉,但在众多的同盟战友中战力却非常低微,气血和不是气血根本是两码事。一个人的身后可以有繁杂无计的壮阔波澜,但在一场战争中,每个人都只是很微小的一个小点,有什么作用和发挥了什么作用。
战争始伊,我们都知道的,一是天不开,未成城的战争不是地面可以窥测得到的,地面也有地面的战争;一是火约,突然就进入了冷兵器时代,天上如是,地下也如是。地上的战争储备非常火爆,岌岌可危,但只是一个储备,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将全部化为乌有,一点威力也发挥不出来;一是刻记,没有人没有生灵可以左右逢源,盖棺论定提前到来,依据着某些标准,你是哪边的就是哪边的,泾渭分明。
为了什么做比做更重要,做重要是在知道为何做的前提下。我生养儿女,我勤勉工作,我要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贡献是我拿得出来的东西,有时这很朴素,我种植和收获庄稼,我教育孩儿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我力图使她们知道磨难真的必不可少。
贡献的不一定是力量,我们的力量都是赊来的,不能从东家那里赊欠了东西再拿到东家面前前恭后倨,看,这是我的土产,看,这是我的群羊。
而是心意,我们有的也只是这心意。
一旦进入战场,在没有冷静思考的前提下,战争中的生灵使用的都是本能。就是赊欠来的东西,这时候不过是近乎完美地抵还回去,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些技能。这些技能,杀的技巧,是进入身体记忆之中的,在动念之间就水泄而出,从念头到身体又到了念头,念头的天空一片晴朗。
这和言出法随还有些区别,只有在使用一种语言的时候,并且任何环境和生灵也都知悉和生活在这种语言下,绝对的谦卑和柔顺,言出法随才有用武之地。
此刻魔王第七把刀正在使用本能,人已经感觉不存在了,人进入了刀光的空间,在刀光中消除投影和意外,维护空间的清平和和平。
我的任务就是杀死拦下抵挡进入这一道门的生灵,我微乎其微,但我在尽力尽心尽意。诸天诸世界都是一个平衡,战争就是要破除这个平衡,我每杀掉拦截住一个,都是在破除了稳固的某些平衡,使之向有力的方向发展和过渡。
杀得兴起,魔王第七把刀的火凤凰出现,人和凤凰融为一体,人在凤凰里,凤凰在人里。大小修罗刀也喷涌出火光,锃亮的刀面变得无比的艳红,火红的刀光配合着凤凰的鸣唳,一团火光倏来倏去,和几个战友一起把平常门围堵得像雨天郁化不开的心事。
双方各有伤亡,敌方源源不断,自己这方面人数逐渐减少,一时之间险象环生。
或者几人围攻一个,或者一对一殊死拼搏,或者前赴后继,或者队与队之间混战,根本来不及救护也无从救护。这就像人的一生,死才是歇息,不愿意或没有闲暇来疗伤和修养自己,走到这一世的尽头。
一名冥军服饰的中年人门后出现,七把刀首当其中。
中年人使用火,直接手挥口吐,烈焰汹汹重创了七把刀。
“不好理解?是我。”
这是冥王帝释天的声音。“凤凰之火不是真火,也敢拿出来现眼?说到火,除了光明之火、人间烟火,我这无明之火算是排名较靠前了,还在魔火、执火之上,遇到我算是你倒霉的日子到了,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吧。”
不容分说,帝释天飞起头下脚上,双掌无名之火组成一道火墙当头压下,火墙在迅速移动中又变成一个火圈,把七把刀套牢。
“小心!”
可是已经来不及,七把刀似乎看到接山何也山长还有梦浅正腾空而起使出招数击向帝释天,帝释天身后魔王第七护法骤然出现,一枚戒指发出神秘的蓝光,如一段小树枝,带着三五片树叶,扫向帝释天的后脑,还有一团乳白色的光球蓦然出现,攻向帝释天胁下的空门。
火凤凰抬头长唳,声音像是一种呼唤,片片羽毛变得破烂,与自己同体的魔王第七把刀已经变成了影子的影子,他心里说,“我要回到那里去了。”继而灰飞烟灭,平静得犹如温暖。
乳白色的光球、梦浅、何也、七护法阻得一阻,但帝释天实力何等强大,凤凰也濒临死亡的边缘,一头栽下,往天空之下沉重的铅球一样落下,失去了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