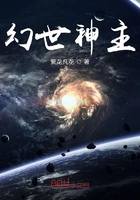“你想告诉我,你也不能给我任何保证?”任心梅沉默了许久,眼中浮起明显的失望之色,“告诉我,是不是这样?”
“假设我现在拍着胸口,信誓旦旦的说,你的手术百分之百的成功,零风险。你觉得这样可信吗?”白正经心里清楚,这句话有可能会彻底激怒任心梅,之前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但是,他不能骗她,只能实话实说。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实话伤人。美丽而动听的话,人人都想听。尤其是女人,面对男人的甜言蜜语,百听不厌,乐此不彼。可他和任心梅不是恋人关系,而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滚蛋!”任心梅的沉默时间不到五秒,发出愤怒尖叫,抓起软枕砸了过去,“什么狗屁信仰,****职业道德,统统的见鬼去吧。”
“怒则伤肝、惊胆损目。”这结局在白正经的预料之中,他一点也不意外,微笑接住软枕,顺手放在单人沙发上,“深呼吸,保持冷静。”
“反正我都癌了,早晚都是一死。伤肝如何?惊胆又如何?还是一死。再说了,我是死是活,关你屁事。立即滚蛋。”任心梅抓起手机,直接飞向白正经的面孔。
“你对我有气,别对手机用刑啊。这是刚上市的苹果五。”白正经高举右手,凌空抓住疾飞而至的白色苹果五代,轻轻放在茶几上,“我走,千万别对你的随身物品用刑了。”
白正经涩笑着一步步后退,慢慢退出病房。到了门口,对她挥了挥手。转身之后,跑步向值班护士室冲去,发现刘小丽不在,给值班护士交代了几句,他匆匆离开了住院部大楼。
白正经灰头土脸的回到办公室,想找杨紫云聊聊。查看杨紫云的日程表,她已经上手术台了。他一个人傻傻的坐在杨紫云的办公室,想了很多。
最迷茫的时候,罗依兰来电话了。任心梅那边的工作任务失败了,和杨紫云的关系,绝不能再弄僵了。要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消除杨紫云对他的“妒嫉”,最好的办法只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而最好的行动就是找谢天鹏“谈判”。希望院方可以取消之前的特别“照顾”,熄灭为他而开的所有绿灯。让他按医院的“游戏”规则进行科室轮转。
真做到了这一步,不但可以降低他对杨紫云的“威胁”,也能消除她内心的“妒嫉”。轮转“游戏”开始了。他会暂时离开妇科,减少和杨紫云碰面的机会,就不会刺激她了。
想到这些,白正经一秒也不敢耽搁,跑步向谢天鹏的办公室赶去。他进了谢天鹏的办公室,还没有开口,谢天鹏主动发话了,“你在医学方面是天才,既然是天才,就不能做废柴。”
“院长大人,你是活活的把我推到刀刃上啊。站的越高,摔的越疼。你不希望我摔的粉身碎骨,拜托你熄灭所有的绿灯,一切按游戏规则来吧。”白正经快崩了,听这口气,这一切似乎全是他安排的。
“我想要的,就是看到你不停的悬崖边缘徘徊。你能挺过这段如履薄冰危险之路,就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天才,否则,你就是华而不实的废柴、烂柴。
不经风雨的幼苗,永远不会成为参天大树。年轻人要成长,必须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压力、挫折、打击、失败。如何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不但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
谢天鹏关了文档,转动椅子面对他,用鼓励眼神看着他,“有人曾经说过,行动证明一切。不管你是天才或是废柴,不用要嘴皮子争辩,用你的行动来证明吧。”
“看样子,我得回去写一份遗书了,以免将来死的太突然,连写遗书的机会都没有了。”白正经竖起右手大拇指对谢天鹏比了比,垂头丧气的离开了办公室。
“怎么了?谈崩了?”罗依兰拽着白正经的胳膊把他拖进了办公室,“我不管谈判的结果如何,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你呢?”
“听真话或是听假话?”白正经从饮水机下抓出纸杯,一口气喝了三大杯,扔了纸杯,抽了纸巾抹嘴,神色灰败的看着她。
“先真听话,后听假话。真话伤人,假话甜心。”罗依兰轻轻关了办公室门,拉他坐下,“别急,坐下慢慢说。”
“说心里话,我现在真没有心情陪别人在饭桌上卖笑了。”白正经从裤袋里掏出钱夹,顺手抽了五张百元大钞放在茶几上,“我的承诺,只能履行一半。现在埋单,却不能陪你了。”
“你钱多,是吧?对付这种混蛋,我有十万种以上的办法。”罗依兰从抽屉里翻出一只红色打火机,右手打火,左手抓钱,火苗蹿起,把钱凑了过去。
“我得罪了你,人民币和你没有仇啊,为何要恨它呢?罪过!”白正经头都大了,赶紧抢了打火机,顺手扔进垃圾桶里,以最快的速度把钱塞回钱夹,“明晚陪你吃饭,这下子可以消气了吧?”
“本小姐不爽,不去了。”罗依兰起身拉开房门,把他轰了出去,“我智商不行,却也不傻。这样的当,只上一次,以后别指望我再帮你了。”
“现在的美女,一个比一个脾气大,这年头,男人真没法混了。”白正经的心又一次“受伤”了。严格的说,他在处理如何与美女相处的关系时,又一次失败了。
想想杨紫云、任心梅、罗依兰三人的态度,再想想谢天鹏刚说的那番话。白正经反举右手轻轻拍着后脑门。觉得谢天鹏的话很有道理,如何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不但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
假设他圆滑一点,世故一点,或是委婉一点,应该不会被任心梅轰出门,更不会被罗依兰扫地出门。这年头,不管什么样的饭局,吃不是主要目的,只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手段。
“亲爱的师父,你的生活圈子像乌托邦一样。任何人事物都可以理想化、甚至是完美化。可你的宝贝徒弟生活的圈子不是乌托邦,而是大染缸。你那一套,真的凹特了。”
白正经坐升降电梯到了楼顶天台,看着火红的烈日,振臂呐喊,“师父,对不起啊!这年头太黑了。你的乖乖徒弟我,无法洁身自好了,只能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