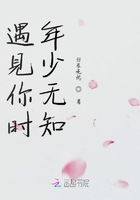安费扬古接了这个差事,心中时时惦记穆贞,此一去的目标是向阿玛求救,如何能够摆开他们的视线,让阿玛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眼下是要好好筹划一番的。
他回到下处,关了门窗,教穆贞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穆贞不知他为何突然要离去,遂诘问,可安费扬古岂肯言明?
“这里不是快活处,与我回到瑚济寨,我会想方设法找到你的父亲,日后咱们一家团聚,共享快乐。”
穆贞只当他是办差不愉快,闹了性子,安慰道:“此次去蔓遮,不要与朝鲜人过多交涉,他们常年联合大明来欺压我们,定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你要将心态放平,不要动不动就与人发生手脚。”
“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女真不是大明子民?”
“我只教你收敛一些脾性,在朝鲜吃了官司,没有门路可要搭进性命的。”
“这些事你无须担心,瞧不起我们的人多了,他朝鲜算得甚么!”
安费扬古套上了重甲,踩上了快靴,又往怀里塞了两个饽饽,细细地审视了她一番,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不在的日子,你要保护好自己,窗户已经被我钉死,夜间就不要再出门了。我从福晋那里借了一个丫头来使唤几天,手脚蛮伶俐的,让她伺候你,记得晚出早归就是。”
“何须外人伺候着我呢,我本就是个沦落人,早可以自力更生。”穆贞抬起头深深地凝视了他一眼,心里一阵火热,上去紧紧抱住他的后腰,将头贴在他的背脊。
安费扬古浑身一震,下意识地握住她的手。
“这次的任务不仅是与朝鲜人做买卖对不对?我听说还要勘察董鄂的地形,那是虎狼之地啊,宁古塔的觉昌安、礼敦当年都是建州的战将,没少吃董鄂的苦头,可想这支部族有多么强悍。”
“这里头的事我自由分晓,记得我的话,等我回来接你。”
“我要你平平安安地回来,答应我好么?”
“我……”安费扬古心里一沉,“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一切均已准备妥当,于日落之时,欲启程蔓遮。
寨门口站满了嘉穆瑚的男女老少,他们均被绑缚手脚,一个连一个地,像是被驱赶的牲畜,衣不蔽体,神情惨淡,他们似乎感到不祥的预感——觉罗寨已经容不下自己了。
当是时,觉罗寨的诸申们渐渐地赶了过来,他们与嘉穆瑚也都是西山的老穆昆了,几代人都居住在此地,有甚者与其联姻,且尚有血缘关系,可谁都不曾想,互伺二主,今日竟沦到战俘行列,大家知道达尔滚要卖掉他们时,故纷纷赶来送别。
千言万语无从说,只能洒泪凝噎,感叹人生无常。
钮祜禄氏情深深地望着他们,悔不该……
众人见到昔日旧主,皆惨然呼唤,“福晋哪……救救我们吧,就把我们当犬也行啊……”
人群之中,她看见了侄子——额亦都。
他亦在悲愤哀怨之情的交织下望着自己。他似乎在向自己埋怨着,不该轻易投降,哪怕是战死,也能够无愧,现在如何去面对死去的固伦达穆通阿?
神情呆滞的穆尔哈齐站在他的身边,战俘的这些日子,他受了出生以来从未受过的苦头,他觉得人生就像炼狱一般,早已对求生失去了希望。
俄而,一伙阿哈冲进人群中揪出穆尔哈齐,一番恐吓威逼之下,将他带走了。众人不解为何单独带走他,原来,达尔滚觉得留下此人来威胁努尔哈赤是最好不过的,这牌需要保留到底。
面对着苦苦哀泣的嘉穆瑚诸申们,金仇赤抄起了牡羊鞭,带领一干古出,三下五除二,每人赏了三鞭,并叱道:“哭哭啼啼地丧气得要死,只是去开采木材为我家贝勒建造宫室罢了,也少不了你们吃喝,搞得像出殡也似,妈的,留着你们的气力到采办场发挥罢!”愈是鞭打,哭喊声便欲大,他们似乎觉得已经到了地狱门口。
金仇赤控制不了场面,强令三百兵士押着嘉穆瑚的诸申缓缓向山下驶去。
安费扬古恋恋不舍地垫在最后,回眸凝望着穆贞,穆贞亦在人群中为其送别。
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依靠,他是自己唯一的亲人,旋即别离的滋味苦涩难咽。
她随着远去的人马奔出了寨门,望眼欲穿,再也寻不到安费扬古的踪影……
安费扬古驾马在前,引了众兵行了几里,天已黑得彻底,当夜在河岸搭起了撮落来就住。
次日晨,乌云笼罩,劲风掠起,见有暴雨之势,安费扬古下令全体疾行,欲趁着雨前赶到瑚济寨外围山下。
可当安费扬古策马奔腾时,却见后头行军依旧缓慢。
“金仇赤!”安费扬古命令一般地叫道。
“在!”只见金仇赤骑着一匹枣红马跟了上来。
“为何还不速行?大雨即来,此处地貌坎坷,我等如何搭撮落?”
“兄弟,后面那位瘸子巴克什不能受颠簸,须慢慢行着。”
“什么巴克什?”
“就是随行记录文字的那个汉人!”
“为何我从来未闻寨中有如是通达文字之人?”
“这个嘛……”金仇赤顿了一顿,笑道:“其实他就是个喂草料的马倌。”
“什么!?”安费扬古顿感受骗的感觉,现下也不好多活什么,只好往肚里生吞,“你前行引路,我去后头看看!”调转马头,回到队伍当中,果有一个苍苍老矣的巴克什坐在独轮木车上就着牛皮袋子咕噜噜地喝个不停。
老巴克什起眼望了望安费扬古,又低下头去,缓缓说道:“人老不中用了,出个远门还得教人推着走,误了你的行程,多有愧疚。”他举目望了望灰沉沉的天,雨水刚好滴在他的脸颊,缓缓开眼,说道:“****将至,少行多益。”
“哼,你以为此行是游山玩水吗?”
老巴克什指着前方,笑道:“你知道我所指的地方是哪里吗?”
安费扬古顺势远望,一片水雾当中隐隐地应现一条长岭,颇似水墨画上勾勒而出。
“那是虎尔岭,穿过那里,没过十几里就是瑚济寨,我如何认得?”
“那其实不叫虎儿岭,而叫仇郎哈岭。”见安费扬古眉头紧锁,老巴克什遂续道:“那里是一座阴涧,骤雨来袭,会有泥石之虞。我们深入斯地,无非是硬闯天险。不如改道,穿行虎拦哈达,去完颜部走一遭。”
“虎拦哈达漫山恶虎拦路,你这老头好有意思,教我舍弃近处,偏偏望虎口去送。就像你,不好好喂马,缘何不务正业地冒充巴克什,来骗取奖赏么?”安费扬古见他不理不睬的态度,便更加厉色,“说!谁给你的胆子,敢轻言篡改我的既定路程,延缓了蔓遮马市,贝勒爷降罪,你来担待?”
老巴克什道:“我这将死之人,还图求什么呢?自古行军,宁走瘴地沼泽,不行死阴之路。如董鄂预知我行军之意是为测其军制地貌,缘何不在途中设险堵截?放汝行,于其何益?”
安费扬古心想此人相貌不扬,但句句在理,故重新审视了他一番,叹道:“你说的不无道理,可我担心的是——粮草。”
老巴克什饶有兴致地听他说完,不禁笑道:“只要你和三百卫兵饿不死、冻不坏,余下的何须记挂呢?”
“你这话……”安费扬古听了这话毫不是滋味,还有嘉穆瑚一百多名战犯难道也不吃粮?饿死途中,如何贩卖?“你这话太不人道,若被嘉穆瑚人听了,便做好被打死的准备罢!”
“我劝说不得你,早晚都会死。”
“你还不该死?你这瘸子,专误我行程!——驾!”安费扬古唾了他一嘴,双腿一夹,快马飞行前头,大声令道:“我寨将士听着!趁雨前穿过仇郎哈岭再行扎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