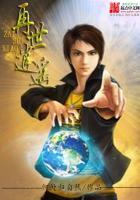“喂,你好啊,”纳斯焦娜打着招呼,小心翼翼地笑笑。
她这时来,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没有听见她的雪橇驶近来,没有听见她匆忙地把马缰往辕杆上一绕,让马留在小河边,然后悄悄地朝过冬小屋走来。他那时正蒙着短皮袄在睡觉。直到纳斯焦娜打开门,他才仿佛被一阵爆炸的气浪从铺板上掀了下来,好容易站住了脚。因此在纳斯焦娜同他打招呼那一刻,他蓬头垢面、呆若木鸡地站在她面前,仍然不敢相信这就是她,同时,为了自己在她面前这么惊慌失措,感到懊恼和不快。
直到这次会面,纳斯焦娜才真正看清他:依旧是当年那样粗壮的、略向右倾斜的体形,依旧是当年那张亚洲人式的扁鼻子、翻鼻孔的宽脸,脸上长满拳曲的黑色络腮胡子。一双眼窝深陷的眼睛像在挑衅似的执拗地瞅着她。脖子上尖削的喉结像只小划子,忽上忽下地浮动着。他瘦了,憔悴了,显得有点佝偻,可是并没有萎靡不振——看得出,还保持着精力和体力,使人觉得,谁要是惹他,他就会作出反击,以牙还牙。他就是纳斯焦娜熟识的、与之相依为命的那个亲人,然而却又显得那么陌生,那么难以捉摸,已不再是她一向知道的该对他说什么、问什么的那个人,不是三年半以前她送走的那个人了。
“瞧,”她抱歉地笑笑,又是她先开口,“我来看看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你别担心,谁也没有看见我。我都已经打卡尔达村赶来了,可你还在这儿睡大觉呢。我给你带来了一点东西,留着给你困难的时候用。”
“现在我没有一天不困难,”他总算接她的话头了。
他穿着棉裤和毛袜子。直到这时,纳斯焦娜才发现他一边的面颊冻伤了,有一块发黑的冻疮。他渐渐镇静下来,套上了毡靴,开始生炉子。纳斯焦娜刚想朝门口走去,他就拦住她,问:
“你上哪儿?”
“嗳,总得把我那些东西搬进来呀,干吗放在露天冻着。”
“等一下,咱们一块儿去。”
他俩只把一罐煤油留在雪橇内,其余的东西全搬进了屋里。随后,他们把卡里卡牵到小河上游河湾后面,给它卸下套,又抱了几捆干草给它吃。他俩谁都不跟谁交谈,如同陌生人一样,只是偶尔讲一两句不得不说的话,像“拿着”或“给我”之类。纳斯焦娜还是不知道怎样去同他亲近,说些什么才好;他呢,不知是因为依旧不能摆脱那种张皇失措的心情而感到恼火呢,还是一时下不了决心立刻去收紧当初把他俩系在一起的那条纽带,——这些年来这条纽带是否完整无损,还不得而知呢。
在他俩摆弄马匹的那会儿,屋子里已经烤得暖烘烘的,纳斯焦娜只得把外衣脱掉。她刚坐到铺着冷杉枝条的铺板上,立刻又站了起来——不,该做点什么事情,想个什么办法使自己和他都定下心来,随便借一件什么小事使他俩亲近起来。于是她走到门角那堆搬进屋来的东西跟前,从翻毛皮袄里掏出一袋用枕套装着的面粉,对他夸耀说:
“瞧,我在卡尔达村给你弄到了面粉。你可以烙饼吃了。”
他没有搭腔,只是稍稍点了点头。
“这算什么呀?”纳斯焦娜生气了。“你怎么这样对待我?连气也不吭一声。可我,深更半夜,马不停蹄往你这儿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兴许我还是回去的好?”
“我不让你走!”
看到他说这话时那副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的样子,那种不加掩饰的自信口吻,纳斯焦娜明白:他不会放她走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她走到他身边,伸出一只手去,无力地抚摩了一下他的头,那样子就像盲人在摸索什么东西似的。
他朝她转过脸来,脸色发白,说:
“你真以为我不高兴你来吗?我可高兴哩,纳斯焦娜,高兴极啦!可是现在我得先看看,人家需要不需要我高兴,可不可以把我心头的高兴流露出来。”
纳斯焦娜把头埋在他胸前说:
“天哪!你在说些什么?我跟你又不是外人。就拿咱俩厮守在一起的日子来说吧,也有四个年头了——难道还少吗?”
他没有回答,轻轻地握了一下她的双手,就放开了。但她已经看出,他马上要对她让步,要退却了——瞧,他连脑袋也支撑不住,歪到一旁耸起的肩膀上去了——只有她一个人才知道这是个可靠的迹象,说明他已经软下心来。从前,她就是根据这个迹象来判断他的心情的。如果他把脑袋歪到一旁,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尽管调笑戏谑,他不但什么都会宽恕,什么都会赞成,甚至会比你闹得更凶,而且要闹上好一阵子才不情不愿地罢休。是的,他身上还保留着昔日安德烈的影子。她朝他莞尔一笑,这是一种乞求得到他的呼应和爱情的蕴藉的微笑。接着她说:
“今天我才头一次看清楚了你。你留着这么一大把胡子,挺古怪的。”
“为什么古怪?”
“嗯,样子有点像……”她吃吃地笑起来,但立刻又咬住嘴唇,忍住了笑,“像妖精。在澡堂里那会儿,我简直弄不明白是谁跟我在一起——是你呢,还是妖精。我想,我为丈夫守着身子,守啊,守啊,结果却在妖精手里失了身。”
“那妖精怎么样?”
“还可以。不过总不如自己丈夫好。”
“你真滑头。谁都不得罪。下次给我带一把剃刀来,我把这堆乱胡子剃掉。”
“为啥?”
“免得像个妖精。”他说完立刻又改变了主意:“哦,不,还是不要剃掉,我不剃。让它长着,免得像我本人。还是像妖精的好。”
“天哪!我怎么不给丈夫吃东西,”纳斯焦娜忽然想起来,“尽顾着闲扯,”兴奋之中她竟忘了其实他俩还没有好好说上两句话呢。“唉,我这个婆娘啊!可见是好久没有人来揍我了。”
他仔细瞧瞧她,哼了一声,问:
“你说,没有人揍你吗?”
“就是嘛。”
“你觉得寂寞了吗?”
“就是嘛,又没有人来开导开导我。得了,你坐下,我这就拿吃的去。”
“至少该煮点茶吧,”他想起来。
“煮吧——你干吗像木头似的站着。难道你这儿水也没有吗?”
她能够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支使他干这干那,即使这只是暂时的,也挺高兴。从前他难得听她支使,今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叫他再听她的。她叫他往炉子里添柴,又叫他到小河边去汲水,然后当着他的面打开自己的小包裹,亮出一只黑麦做的大圆面包和一大块牛油。牛油是谢苗诺芙娜秋天就储存好的,正是预备给他安德烈吃的,那时他们正等着他回来休假。休假的事虽然吹了,但是根据一种古老的迷信风俗,并没有动用为这次团聚所准备的东西,据说要是把这些东西吃掉,就别想再团聚了。大约在一个月以前,纳斯焦娜无意中发现了这块牛油,它给包在一块布里,藏在谷仓的一个偏僻角落的搁板上,昨天她跑去切下了半块。给谁留的,就给谁吃。她知道,在什么地方还藏着一瓶家酿白酒,那酒瓶上大概已落满尘土,只要等到安德烈一踏进父亲的家门,为他——为这个日夜悬念的亲人——举杯祝酒的时刻就到来了。
还在战前,有一次,纳斯焦娜在电影里(这种奇妙的玩意儿她有生以来只看过三次)看到一个城里的女人,不知道该怎样来讨好她疯狂地爱着的丈夫,竟像喂孩子一样,亲手喂东西给他吃。现在纳斯焦娜想起了这件事,忽然产生了一种迫切的、从未有过的奇想,竟也动手要把一片片牛油送进安德烈的嘴里,但是他没让她这样做。她既觉得害臊,又觉得高兴,因为这么一来,她原先还有的一丝羞怯的心情仿佛已一扫而空,现在可以迈开步子向前走了。他们喝茶时只好合用一个盛器——一只军用水壶的壶盖,——两个人轮着喝,等安德烈喝过以后,纳斯焦娜把壶盖接过去喝,然后再递还给他。就这么件事,不知为什么也使纳斯焦娜心荡神摇。
这儿的一切无不使纳斯焦娜心荡神摇,又无不使她心惊肉跳。无论是这间废弃了的过冬小屋,屋内胡乱地铺着劈成两半的原木以代替地板,天花板早已翘棱,板壁发黑,刨得高低不平,布满了陈旧的蜘蛛网;无论是窗外如雪崩般从山上滚下来的积雪,那雪从未被任何人践踏过,正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无论是身旁的安德烈,今天总算在大白天里看清楚了他,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变得易于理解些;无论是她自己,不知道怎样和为何会落到这个久已被人遗忘了的荒山野岭中来的——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既使她激动,又使她害怕。每一次她只消略一分神,就会感到诧异,安德烈怎么会在她跟前,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思之再三,才能想起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只有经过这么一番苦苦的思索,一切才又恢复常态,然而这种状态并不稳定,时有时无,因此必须时时刻刻努力保持住这种状态,否则它会重新消失,——是呀,这一切看上去都显得那么虚假,犹如幻觉,或者梦境。
纳斯焦娜仿佛在跟自己捉迷藏:有时她深信,眼前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否极泰来,只要耐心等待就行,而有时她又觉得眼前的一切忽然坠入了无底深渊,吓得她毛骨悚然。但是她强颜欢笑,没有流露出恐惧。虽然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今天是属于她的,今天是她多年来唯一可以让自己的整个身心得到自由和休息的日子。
吃饭时她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以便多留些给安德烈。吃好饭,她已被烤得浑身软弱无力,不由得打了一个哈欠。
“家里人以为我在卡尔达村,可我却在你这里,”她没头没脑地说。“他们要是知道了,可不得了。”
安德烈没有回答。
她把翻毛皮袄铺在铺板上,甩掉脚上的毡靴,摊开双臂,躺了下来。安德烈在桌旁朝她瞟了一眼,她想撩拨他一下,就闭上眼睛,一声不响,好像已经蒙眬入睡。但是他刚走到跟前,她就猛一翻身,霍地跪了起来,身子朝前弓着,像姑娘家那样活泼地唧唧喳喳说:
“走开,别蒙人,我不认识你。”
“什么,什么?”
“走开,别蒙人,我不认识你。”
“瞧你!”
在她的逗弄下,他朝她扑了过去,她往旁边一闪,接着就嬉闹起来,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头一年那样。嘿,那时他们闹得可欢哩,总要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纳斯焦娜不是个弱者,她从不轻易屈服,往往累得安德烈汗流浃背才求饶。但是,这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不想试探他的力气,一下子就松开了手。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于是就像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似的,急不可耐地手忙脚乱起来。她为了不致使他感到委屈,便小心翼翼地劝阻他说:
“悠着点,安德烈,不要性急,别这样。我的爱情就像一匹干瘪的母马,不知有多久没有给它喂食了,你可别把它弄伤了,不要硬来。”
他顺从了,这可是从未有过的,自从她嫁给他以来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对待她又温柔,又体贴,讨好她,揣摩她的每一点细微的愿望。
纳斯焦娜躺在那里休息,感到又羞涩,又好笑,仿佛她不是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而是跟她无权与之接近的别人的男人待在一起。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睡意渐渐上来。一刹那间,她仿佛觉得,刚才由于一种奇迹,使她窥见了很久以后的自己:那时她待的地方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些不同,而且,也不是单身一个人,但是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看清那个人——她不知道那人是安德烈,还是别的什么人。大概是安德烈吧,除了他,她没有想过别的人。
她竭力想对安德烈说些什么,说些亲热的贴心话,但一时又不知怎样启口才好,就要求说:
“让我看看,你哪儿受了伤……”
他解开衬衣,露出胸前几块淡红色伤疤。纳斯焦娜小心地摸了摸。
“可怜的人……他们这是要把你往死里打……全好了吗,还疼不疼?”
“现在好些了,只不过有点隐痛,特别是在阴雨天。总觉得怪难受的,好像扎着什么东西,还没有习惯。”
刚才,在一小时以前,她还弄不明白,她怎样和为何会到这儿来,现在她却觉得,她生来就是置身在这四壁之间的,而从未在任何其他地方待过。凡是她多少还能记起来的另外那个生活中的事情,都好似颠三倒四的乱梦,若隐若现,似有非有。难道在那边还有人、战争、死亡和灾难吗?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过冬小屋里苦涩的空气,凝重的、并非尘寰所有的那种沉寂,使她昏昏欲睡,忘却了各种各样的忧患和劳累,沉醉在自由自在的清静之中。她那得到慰藉的身体舒坦地伸开四肢,默默地、蒙蒙眬眬地躺着,没有一丝一毫的欲念。
“我要是睡着了,你不会生气吧?”她用微弱的、充满幸福的声音问。
“睡吧,睡吧。”
他用臂肘撑起身子,端详着她——她已经睡着了。她那被冬日的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的圆脸变得柔和了,在睡梦中露出无忧无虑的微笑。这几年来,这张脸有点发黄了,粗糙了,脸上已完全失去了(其实早在他离家之前就已开始消失)那种少女的性急和好奇,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啊,多有意思,后来怎样呢?”的神情。美妙的神话很快就结束了,一切秘密都被揭开,如果偶尔还会对什么东西感到惊奇的话,无非因为早年虽然见过,但当初过于匆忙,未及看清所有的东西,现在它又重新出现在你面前的缘故罢了。
纳斯焦娜的上衣纽扣解开了,双手搁在胸前,随着胸脯的起伏而起伏着,手指微微颤抖。安德烈发现这双手发肿了,变得粗糙了,——这是由于干活的缘故。从她嘴里,随着深沉、平稳的呼吸,散发出一股股温暖的、甜丝丝的热气。
他小心地搂住纳斯焦娜,紧紧贴着她,听见了她的心跳声。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又清晰,又亲切,每跳动一下,就使他增添一分模模糊糊的、揪心的惊慌不安。这种惊慌不安越来越强烈,由于他不知道这种惊慌从何而来,预示着什么,因此就越发感到惊慌。他再也躺不下去了,就坐起身来,悄悄地爬下了铺板,然后偷偷地回过头去望望熟睡的纳斯焦娜。“睡吧,睡吧,”他不知为什么这样低声地说,但是他更希望她能够醒来。待在她身旁,却听不到她的声音,错过了她可能说和可能做的一切,这使他越来越受不了。他的心很快就冷却、空虚、收紧了,渴望有所行动,渴望得到温暖。
他走到屋外,不由得立刻眯起了眼睛——光线亮得出乎意料,直刺他的眼睛。他觉得,那轮正悬在山顶上的太阳,仿佛从山顶上滚到了这里。积雪冒着热气,闪烁着金星,而在背阴的地方则发出蓝色的幽光。这是春天般的温暖,它散发出芳香的气息。屋檐角上的冰凌融化了,一簇水越橘已挺起枝干,树下好些地方的积雪也已融化,露出一块块光秃的地面。
安德烈出声地呼吸着,好像被空气压得喘不上气来。他先跑去饮马,然后再下到安加拉河边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但是惊慌不安的感觉还是没有消失,安德烈觉得似乎恰恰是在现在,恰恰是在这一刻,由于他的愚蠢,正在失去某种重要的、不可复得的东西,而那东西是他所必不可少的,失却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回到屋里,纳斯焦娜仍在沉睡。他觉得坐在哪儿都不是地方,便又挨着她躺下,把头紧贴在她胸前,但是由于贴得太紧,透不过气来,只好又挪开一点。纳斯焦娜在睡梦中用一只手摸到了他的脑袋,抚摩着他的头发,这使他立刻觉得轻松了些。他闭上眼睛,感觉到肩膀上搁着纳斯焦娜那只解救他的手,想象着自己在徐徐旋转,朝着一处柔和的广阔空间飘去,——这种感觉总是能够助他入睡,——不久,果真打起盹儿来了。
他俩同时醒过来。纳斯焦娜睁开眼睛瞧了瞧安德烈,他哆嗦一下,也醒了。她朝他笑笑。
透过窗户投进来的太阳光斑,已远远地移到门口:白天即将结束。
“我睡得好香呀,”纳斯焦娜说。“我简直记不起来,什么时候在大白天这么美美地睡过。都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我看着你,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你。可是在梦里,你瞧,我相信了,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心定啦。”
他们醒来以后,好似又重逢了,彼此惊奇地、期待地望着对方。纳斯焦娜想要起来,但是他拦住了她,这使她高兴得笑起来。
他俩一再推迟,谁也不提起那个话题,尽管知道这场谈话无论如何是避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