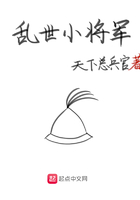项南回到学校,突然想起朋友郑重托他办的一件事情,要他帮忙找个英语家教,说是家教,其实是个美丽的幌子。郑重是想找个女朋友,正儿八经的准备结婚用的女朋友。他并非找不到女人,而是身边的女人太多,他是报社的记者,家里又颇有些权势,他嫌社会上的女人太俗,太势利,就想到了大学里还未被社会玷污的女生。他说要找个大二的女生,谈上两年恋爱,出来工作一两年正好结婚。主意想得十分周全。
项南刚把炮制的家教信息贴了出去,还没回到寝室,就有女生紧跟了上来。项南觉得很奇怪,这还未开学的空旷校园里,怎么一下钻出了那么多嗅觉灵敏的女生,看来,这高出乎时一倍的家教费确实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女如花满春殿,身边只有鹧鸪飞。"项南不由地感叹女生怎么都变成了这样时,有人敲门。
"我可以进来吗?"一个淳朴大方的声音。
"请进。"
进来一个如同其声音的女生,进来之前项南已对她产生了好感,不仅仅是她的声音,更是她的行为,她是在听到"请进"之后才推开的门。而这简单的礼貌却在越来越以为大大咧咧、自视前卫的女生中已消失殆尽。
稍微注意一点的女生仍没有退化举手敲门的手的功能,但却极易省略敲门和推门中间的应有的时间。项南觉得这女生很面熟,肯定在哪儿见过,但一时想不起来。
"My name is Huaje......"女生的自我介绍的第一句,不啻于一声晴空霹雳,落在项南心上的却是巨大的惊喜。他没有听到她接下去的任何语言,只望着她整齐的刘海下的黑眼睛发呆,狂喜的心几乎要冲出打开门的鸟笼,但他压抑着,她显然已不认识他了。
两年了,已经两年了,她居然和他在一个学校两年了,却从未碰到过。可见面却又是以这种为别人作嫁衣的可笑方式。
她走后,项南就陷入后悔之中,他怎么可以把上苍的珍赐拱手相让郑重呢,郑重那决不是狼坑,可在项南的眼中,那竟比狼坑还要险恶百倍。
但反悔已完全成为不可能。第二天,再见到华洁,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声不吭地带她去见郑重。看到郑重欣喜的目光,项南更是懊丧,不得不知趣地告辞。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边是友情,一边是他等待已久的朦胧的爱情,他都无法舍弃。
"公平竞争吧。"一个现代的声音对他说。
"对呀,为什么不公平竞争呢?竞争才公平嘛。"项南一下找到了快乐的答案。
于是,他释然地开始了行随心动,快乐地在各个地方"不期"而遇上她,在食堂,在图书馆,在教育系晚自习的教室。她对他总笑笑,从不惊讶一天中遇上他那么多次。慢慢地,见面多了,招呼打的多了,话语也多了些。但她却从不接受项南的任何邀请,拒绝时也是满脸灿烂的笑容,笑容背后有项南更为心醉的一丝忧郁,像图画中物体的阴影。
项南失眠是从热闹的周末开始的,最热闹的时间总会生出最寂寞的心。一到周末,项南就找不到华洁的身影。他开始品尝相思的苦涩滋味。"当嘴唇不能亲吻时,它才开始歌唱。"这于项南是真真切切的。
唱歌的嘴唇是寂寞的,更寂寞的是唱歌的心。项南寂寞的唇伴着寂寞的吉他在灯火通明却空空荡荡的宿舍寂寞地悠悠而唱:
在那悠远的春色里,我遇到了盛开的她,洋溢着眩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以后夜夜我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地飞.....
又是一个周末,项南怜爱地抱着吉他弹唱到深夜,居然没有一个同学回来。他迷迷糊糊地躺到床上,满脑子是华洁的样子。
感情的手臂搂着华洁的影子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已是下午。项南胡乱地往肚子里倒了包用温水泡出来的硬邦邦的方便面后,就走出了校门。"去理个发,清醒清醒。"他思忖着,不自觉地又走到了"明明发屋"。
明明发屋
"明明发屋"的主人就叫明明,手大脚粗,还不足二十,理发的手艺还不错。项南常常过来理发,混熟了,玩笑乱开,她也不生气,有时碰碰触触,她不但不恼,反而很欢喜的样子。她的欢喜溢于言表,不加掩饰地表露在与项南的接触中,不管是洗头,还是理发,她都贴着靠着,毫不在意地触到项南的背上、肩上。
项南也喜欢这种接触,当他发现她只对他一人才这样亲昵时,他就有些沾沾自喜起来。她甚至不收项南的理发费,还总是问东问西。问他哪个系的,多大了,有没有女朋友。项南每每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地胡诌,对她,他只是装作不经意地碰碰,理发费他是坚决要给的,他可不想和她真正有什么瓜葛。
而明明却明显越来越在意口若悬河的项南。为他刮脸的时候,她的手指像平缓河滩上的旋涡在项南的脸上反反复复地流动。
仔细的眼睛紧紧地凑着,连温暖的呼吸也不均匀地喷在项南的脸上。项南非常喜欢这种感觉,锋利的刀子在脸上轻捷地刮过,割稻草般的声音痒痒地传入耳膜,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双温暧的手,她把女性阴柔的气息抚摩进了他焦躁不安的心,如湿润的山风。
明明喜欢项南更因为有一次项南帮了她,那天,项南刚走到明明发屋,就看见有个男人在对明明动手动脚,而明明显然是在拒绝,但那男子却不依不饶,动作大得很。项南故意咳嗽一声,跨进了发屋。那男子见有人坏了他的事,竞回头叫项南滚出去,还要把门关上。项南没有想到他如此嚣张,心里虽有些害怕,但看到明明那求助的眼神,他勇敢地走向了那男子。那男子原来却只是个孬种,竟吓得跑了,走时,故意虚张声势地吓人,说要项南等着。但后来,却一直没有来。当时,明明非常害怕,项南安慰她,说没事的。其实,项南也非常害怕,但那个下午,却一直守在明明发屋。
发屋里,明明正百无聊赖地斜靠在椅子上拨弄手指。看到项南,她高兴地跳了起来,兴奋地说这说那,嘴巴几乎停不下来。
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校的学生大都还在午睡,而回家的学生总要挨到天黑才返校,没有一点生意。明明索性把店门关了,要项南到她家里去玩。
说是家,其实只是店后租的一个小房间。走进门,屋内一片昏暗,明明几乎是拖着项南往里走,项南仍有些跌跌撞撞,没走几步,明明突然反转身,伸手抱住了项南的腰。项南被她的胸脯、急促的呼吸和房间的黑暗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好热。"项南的眼睛还没适应这房间的黑暗,他对看不清的东西本能地有些不安。
"那我去买两瓶冰镇汽水,你先坐一会。"明明很不情愿地松开了他。
项南的眼睛终于缓了口气,逐渐能适应房里很弱的光线,小屋里陈设简单,一床一凳一张小方桌,非常典型的外来妹租借的房子。所有的一切都很简陋,窗户居然是用白纸糊的,难怪房间那么暗。床也只是搭在砖头上的几块木板而已。
但房间里却漫漫有种女性的香气在弥散,这香气让项南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可耻,"我来干吗,无非是来解解闷,但内心不是也想和她玩玩吗,我从来就没有把她当一回事,甚至把她的身体当作解闷的工具。"项南想想她的不易,有些于心不忍。
她从农村来到省城,一个人独自开一家小店也挺不容易。
来发廊的男人大都有些不经的妄念,动手动脚。为了生存,她会委曲求全。可既要不得罪顾客,又要保护自己,这对毫无背景的外来妹来说是多么地艰难。
她生存在赔着笑脸的夹缝里,只要不太过分,捏捏摸摸的羞辱她就把它强吞到肚子里去。但那种事她是坚决不做的,她凭手艺吃饭。项南多次见过她的那种受了委屈还不能生气的几乎是讨好似的斗争。
对于项南,她一直是一片真心,倒格外喜欢项南碰碰她。一个没怎么上学读书的乡下姑娘很容易倾心于一个似乎什么都懂而又温文尔雅的大学生,而表露的最好方式就是身体的接触,让自己喜欢的人碰触自己的身体对她来说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而这种姑娘的这种美好的感情一旦遭到欺骗,特别是献身以后遭到抛弃,后果是很容易想到的。在这种女孩的眼里,惟有第一次,第一个男人最重要。如果要了她的第一次的第一个男人不要她了,她就会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没有贞洁了,用无所谓的身体去谋取有所谓的生活,就成为了天经地义的事了。
项南站在小屋的昏暗里,灵魂却像暴露在阳光下,他看到了他的卑劣的影子。此时,他又想起阳光般的华洁,于是,他快速地逃出了明明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