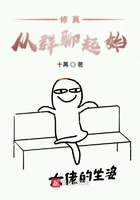煤矿杨队长终于迎来了新来的一批流民,来修复煤矿塌方的。
煤矿的设备老旧,好多以前用机器的干的活都变成了人工来干,人员现在变的很是吃紧,有些熟练的老工人,不可能用在这些危险的现场。
一辆军用卡车上,被撵下来十多个男子,有结实的,有瘦弱的,十七八到四十岁的都有。其中还有两名卷发碧眼的,个子明显比别人要高不少。
一个个目光呆滞,精神紧张,很自觉地站成了一排,不敢抬头。
一位持枪的军人把名单递给杨队长后说:“杨队,现在流民是越来越少了,省着点用。”
说完,开车就离开了。
一名持枪的军人就押来十多名男子,有的身体比他还强壮,这明显就让人不可思议。
好多围观的工人们好像看到了当初的自己,也是这样来到了流民镇煤矿,有的已经结婚生子。
杨队长看了下这排人,沙哑的大嗓门吼了起来:“来到流民镇煤矿,你们以后就有饭吃了,有工资拿。”
这群人终于有人抬起了头,眼中闪现出了光茫。
杨队长继续说道:“不管你们以前是干啥的。来到煤矿你们就是这儿的工人,好好干,咱们的镇上大姑娘,小寡妇多的是,攒上点钱,娶个老婆,生个儿子,换个营生,这辈子也算安顿上了。”
杨队长看看这群人终于有了反应,又阴测测的说道:“谁要是给老子偷奸耍滑,从哪来就回哪去,老子这可不养闲人。”
人群中有几个人,竟然放声痛哭了起来。谁知道他们曾经遭遇了什么,也是些有故事的人啊。
杨队长朝围观人群里一个黑脸龅牙的人喊道:“韩老六,这群人交绐你了,今天回去好好吃一顿,睡一觉,下午开始就给老子清理现场。”
黑脸龅牙的韩老六答应了一声,领着那十多个人就走了。
围观的人群也散了,边走也唏嘘着。这辈子就安顿在这流民镇了,有吃有喝有住房,一辈子也去不了任何地方了。
下午,韩老六领着焕然一新的新工人来到了塌方现场。新工人都换了洗的干干净净的旧工服,戴着崭新的黄安全帽来到了塌方现场。
新的黄安全帽这是新人的标致,你可以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资。
黄安全帽是工人,蓝工作帽是搞技术的,红安全帽是领导们的象征,新的红色安全帽这不用说,你也懂的。
目前,流民镇矿山救援队已有30多人分两组在井下开挖塌方体,在坍塌处两端同时开挖。目前正在以每小时半米的速度推进。
所幸的是,事故现场没有瓦斯气体,没有发生渗水。新人们所做的就是在救援设备用不上的地方,人工顶上去。
说好听点是新工人,其实就是人形工具,好用,危险的地方,工具架不起来的地方就由他们人工支撑。
随着顶部逐渐的加固,下面的废石和煤块,再由其它人用推车运送到前面的皮带上。
随着石块和煤块的减少,一些设备和物质也露了出来。一名新黄安全帽站在上面支撑着顶层,忽然整个人抖动了起来,哆哆嗦嗦的喊道:“人,死人。”
被身后的韩老六一棍子砸在大腿上:“干活,闭嘴。”新黄帽咬着呀,一声也不敢吭。
其实有很多人发现了这个死人,碍于煤矿生涯中不能提这个忌讳,这个死字不能提,只能说“纸马”。所以说那个新黄帽挨这棍子不算冤。
人们都继续干活,整个死人还没露出来时,一名救援队员和韩老六窃窃私语。
“韩哥,这纸马不对劲呀?没听说这次谁没了呀”
韩老六:“没有呀,怎么这货还没有穿鞋?”
“韩哥,你看这是卫生院的住院服,这是怎么回事,也没穿工服。”
韩老六:“是不对劲。不会是大壮吧。”
这时又一张顶被固定住,下面的速度快了,一个面部完挤碎的人被人拉了出来。胸前也是血肉模糊,不知是被什么砸的凹了进去。
韩老六放开嗓子,吼道:“兄弟们,加把劲,干完了,晚上有好酒。”
新黄帽们巳经麻木了,一声不吭,让干啥就干啥。管他死人还是石头让搬啥就搬啥,让干啥就干啥。
很小的榻方,很顺利的维修,没有人员伤亡。不光一个也没少,还多出来一个死的。
血肉模糊的死人就被留在了原地,工人们干了一晚上的活,再有天大的事儿也得等老子先睡上了觉再说。
被挨了一棍子的新黄帽回到了井上,取下帽子,是一个卷发碧眼的男子。一瘸一拐跑到正在吸烟韩老六身旁讨好的说道:“韩哥,韩哥,给一支烟。”
韩老六今天的事故处理的很顺利,心情也美。把剩下的皱巴巴的香烟和火柴都扔绐了他:“都赏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特普。”
朱子怡发现了白小白的存在,整个人都不好了。不知是哪里来的寄生人,寄生在她的手上,让她很不安。
她想起了一种寄生虫特征为在宿主体内,还有许多小动物以寄生的方式生存,依附在比它们更大的动物身上。
虽然它是自己画出来的,谁能保证它有一天会不会把自己也吞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白小白也很害怕,不知道这女孩是怎么想的,害怕这姑娘一刀把自己来个四分五裂,他知道这女孩能干出这样的事儿。
想灭掉我也太容易了,用刀子,用硫酸,用洗液,也许用一瓶卸妆水就能让我魂飞魄散。我要把这姑娘哄好了,等那天我自由了,我躲她远远的。
白小白越想越害怕。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被什么东西消灭,他也不敢试呀。
两个人心怀鬼胎,相对无言。
没有人知道童亦辰对朱子怡说了什么,反正朱子怡和童亦辰交谈之后,整个人就很不对劲。
朱子怡在下学铃声响起的第一时间,就冲出了学校,回到家中。甚至连每天必须的踢球运动都没有做,直接回到家中,坐在了书桌前。
感觉没有人能听到自己说话声了,才悄悄的对着手上的白小白说道:“白小白,你在不在?”
白小白也等着朱子怡和他说话。能沟通就行,就怕一言不合就动刀子的人。
忙用线条摆字:“我在。”
说完之后,想起来这句对话更像是一种智能语音。
朱子怡又问道:“你从哪来?”
白小白心想,这我哪能知道。我知道还用跟你混,我要是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就回哪去。用得着过这种非人的生活
不过,白小白还是乖巧的回答:“我是你画出来的呀。”
朱子怡愣了,这不是废话呀。我画过这多人,这要是都活了的话,我不就成女娲娘娘了。
难道我问的有问题?
于是,问了个更愚蠢的问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白小白不由的反问道:“不是你把画出来的吗?这我怎么能知道?”
这确实是实话。
朱子怡又拿起一支笔,在手上又画了一个白小白二号,和白小白画的几乎一模一样。
又疑惑的问道:“白小白,这个白小白也是活的吗?”
白小白翻了个白眼,说道:“这我哪知道呀?你去问他。”
白小白翻的这个白眼,朱子怡当然看不见了。问的问题也很无语,简直不能正常沟通。
朱子怡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那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哪知道?是你把我画成这样的。”
“那我给你画个红裙子?”
“随便。”
朱子怡终于想起来问正事了。
“为什么,武老师打我不疼呢?是不是你搞的鬼?”
“老大呀,打在你手疼在我身呀。每次那火辣辣的疼都是我在忍受呀。”
“不好意思,我以后会小心点的。”
“喔,那不用。我这人就是贱,一天不挨揍浑身不舒服,全身无力。”
“喔,有一次我拍桌子是不是你干的?”
“是,是我错了。”
“那你为什么能控制住苍蝇?”
“喔,我有两根线,看不见的线捆住的。”
“线是哪来的?”
“挨揍,被揍出来的。”
“被揍出来的?”
“是。”
“那你偷东西呢?”
“那不是偷,那是拿。”
“你是怎么拿东西的呢?”
“用两根线。”
“那么偷的,不对,拿的东西放哪里了?”
“肚子里”
“肚子里,怎么能?”
“我哪知道,你画出来的。”
一段对话。白小白真真假假的回答。
朱子怡又问:“你怕不怕水?”
白小白:“好像不怕,反正泡在水里没死。”
朱子怡又问:“你怕不怕火?”
白小白:“不知道。”
朱子怡又问:“怎么能不知道呢?要不试一下。”
白小白连忙否认:“怕。”
朱子怡又问:“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怕不怕火?”
白小白很诚实:“我怕死。”
朱子怡又问:“你怕不怕刀?”
白小白:“怕。”
朱子怡被逗得“咯,咯”直笑,白小白就没见过她这么高兴过。
朱子怡高兴的说道:“你必须听我的话,否则我拿刀把你杀了。”
朱子怡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笑着的,白小白听着却是万分的恐怖。
不过朱子怡还是比较善解人意的,问道:“你希望我怎么做?”
白小白认真的想了想,答道:“你好好学习,我想和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还有,更重要的是主动找揍,我怕哪一天不挨揍我就会消失了。”
这一次,白小白说的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