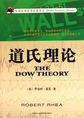“这样过了大概1年左右,大家都分到了点钱,但大部分还在波哥那里,波哥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大伙都信服他,再加上加进来的小混混越来越多,波哥就有了做大生意的想法,于是便开始偷汽车。”
果然是吃大茶饭的!我心里暗叫不妙,原来他们是一伙汽车盗窃团伙。
他察觉到了我手上的冷汗,笑着按了一下我:“大概是一年半之前,波哥遇到了刘小姐。刘小姐是一间学校的音乐老师,每天晚上都在学校附近一家西餐厅弹钢琴,波哥一眼就看中她了,叫我们买来玫瑰送给她,还缠着要了她的电话。”
我说:“当时刘小姐不知道波哥的身份吗?”
他说:“当然不知道,不过后来他们真正来往后,刘小姐隐隐约约知道了一些,她对波哥说,如果波哥再带大家偷车,就分手。为了刘小姐,波哥决定放弃无本生意,真正做个生意人。”
我说:“那后来做什么了?”
彪哥说:“做车。”
我好奇地说:“做车?是卖车么?”
彪哥说:“对,就是卖车,不过卖的不是新车,是旧车。”
我说:“旧车也有人买?没有什么赚头吧?”
彪哥说:“你不懂,这些旧车都是从境外或外地运进来的外国车,经过修理翻新后,完全像刚出厂的样子,每辆车可挣数万元。”
我惊呼:“有这么多?旧车翻新可以上牌照吗?”
彪哥笑笑:“只有愿意给钱,没有办不了的事。”
我说:“原来这样。”
彪哥说:“其实本市做这行生意的,并不只是我们,除了我们这班人外,还有另外一班人,带头大哥叫阿乐。他们比我做得更早,听说早几年很多市领导家属的车都是在他们手上买的,既便宜又漂亮,人们花几万元的钱就可以买到市场价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进口车,多拉风。”
我点头:“那确实是,反正看上去也是新的,别人又不知道是翻新的旧车。”
彪哥说:“刚开始时是相安无事的,但从一年前开始,乐哥开始与我们抢生意,就是通过压价的方式打压我们,比如同一类型的车,本来我们可以赚5万的,但是乐哥知道后,他会通过种种方法找到对方,开出比我们便宜一万或二万的价格,这样人家就会买他的车。”
我说:“这样摆明了是抢生意。有点不厚道。”
他说:“对,接连几单生意都这样让乐哥那伙人搞散了,波哥就开始急了,这时候兄弟们也纷纷要求他花点钱,找个中间人出来说和,或许可以保住原来相安无事的局面,但是波哥不愿意,他说:‘如果我们忍了这口气,以后还怎么在道上走?’”
我说:“那他怎么办?打乐哥一顿?”
他苦笑了一下:“他确实是与人家打,不过打的是价格战。乐哥对人家说可以便宜一万,波哥便说我们可以便宜二万,乐哥可以便宜二万,波哥便说我们可以便宜三万……”
我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生意做成了,却挣不到钱。”
他说:“谁说不是?半年不到,之前挣的钱都花了个七七八八。当时也有兄弟私下里说,不应该这样把钱浪费了。如果波哥之前不是对大家特别好,估计很多人都反水了。”
我说:“嗯,我看得出来你们都很尊重他。”
他说:“我只是敬重他的为人和义气,但我不赞成他的做法。我觉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自作聪明,蠢!如果他不是这么蠢,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我说:“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他带着一班兄弟谋生活,生意最好的时候,手中握着千多万,却不懂得用这些钱去拉关系找靠山,最后落个横尸街头,一分钱也带不走。”
我说:“这个也与那晚的封局有关?”
他肯定地说:“当然有关。大约半年前,乐哥那边实在顶不住了,因为听说他们也亏了很多钱,只好先软了下来,不再主动通过压价来抢我们的生意,我们也就慢慢恢复了正常。”
我说:“那你们呢,有没有受影响?”
他说:“其实我们也快蚀到底了,这半年恢复了正常,才慢慢地又挣了一些钱,但由于波哥习惯了带着兄弟们到处吃喝玩乐,积下来的钱并不多。上个月刘小姐生日你已经看到了,他是用钱很爽快的一个人。”
我点头称是,因为当天我还拿了他五百元的红包。
彪哥接着说:“16天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一班人到夜总会唱歌,因为下半夜,我们有单交易,一共20辆改装好的车即将运过来。每辆车5万元,我们一共准备了20卷钱。因为有正经事要做,波哥让大家尽量少喝酒,但不喝酒不来劲,大伙就赌博。”
我说:“原来是这样。”
彪哥说:“也许是当天的交易走漏了风声,当天晚上我们在夜总会的贵宾一玩时,有人向警方告密,初时警方以为是贩毒,马上如临大敌赶到现场,却发现有人聚赌。”
我说:“如果当天晚上,波哥没有从楼上跳下来,那么他是不是被罚款5000元就可以平安无事?”
彪哥摇头:“不一定,如果当时他没有跳楼,警方就有可能查到这一皮包钱,一定会追究钱的来历,而且,那个躲在背后的举报者,也不会让他就此脱身,估计还是会追究出改装车交易的事。”
我叹了一口气,不管剧情怎样发展,他都难逃一劫,只是可怜了刘小姐,那么一个温柔的女人。
彪哥说:“我今天打探了一下兄弟们的口气,大家都认为是乐哥告的密,外面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当晚交易。后来有兄弟打听到了,当晚波哥出事,一班人被关进去了,那批货,最后也让乐哥接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是一剪双雕,既除掉了敌人,又抢了生意。该有多么缜密的心思,才能想出这么阴毒的招数?
我没有想到,数年之后,这个阴毒的人会成为彪哥的兄弟。这个世界,只有利益出马,便没有永远的敌人。
傍晚时分,彪哥向我道别,说:“在里面没睡过一晚好觉,今晚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他没提钱的事,任由它堆在那桶脏衣服里。眼看他转身要走,我忍不住问他:“这钱怎么办?”
他说:“半个月放在这里都平安无事,以后就让它继续放在这里吧,挺安全。”
我着急地说:“那怎么行!这些天,我门都不敢打开,害得她们以为我屋里收藏了一个男人。”
他笑嘻嘻地回过头来,一把揽过我的头说:“那今晚就收藏我在这里?”说着便要把嘴巴凑过来,作状要吻我。
我大惊,连忙挣扎,连声说不要。
他笑笑,胸有成竹地拍拍我的脸,说:“以后你会愿意的。”
说完大步流星地走出去。
我想不透这个男人,他说在“里面”时天天为这笔钱睡不着,出来却好像完全不把这笔钱放在心上。
后来我才知道,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从他那天晚上把钱交到我手中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决定了相信我。
他现在再次选择相信我,其实也是相信他自己的眼光。
只是苦了我,当晚守着这笔钱,并没有因为他的归来而安心大睡,相反,因为他的出现确认了这笔钱的来历,更加感觉事关重大,提心吊胆地睡不着。
幸亏,他并没有让我担心得太久。
第二天中午一觉醒来,正在寻思到小卖部去买点速食面,电话响了,是他的来电。
“阿冰,我现在过来,你等我。”
我哦的一声,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他算是我的什么人?随便说来便来?难道就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笔钱?
走到外面,阿丽和胜男也起床了,正在厨房里忙活。看见我出来,问我:“要不要给你做早餐?”
我摇头:“不用了,有朋友来找我。”
阿丽疑惑地说:“朋友?男的?”
自从搬到这里来与她们一起住,不要说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没有一个来找过我,因此她诧异。
我装作不在意地说:“在酒吧里认识的朋友,你们也见过的。”
胜男好奇地问:“我们也见过的?是谁?”
我说:“来了你们就认得了。”
正在说话间,外面已响起了拍门声。阿丽笑着跑去开门,边走边说:“我倒要看你这个新男友是谁。”
门打开,正是彪哥,他一张脸被刮得干干净净,经过一晚的休息,整个人神彩奕奕。
见到是他,阿丽与胜男都呆住了。她们整天迎来送往,认人的本事最是厉害,一见彪哥,她们便想起波哥。她们没想到,我的“新男友”竟然是波哥曾经的手下。
而波哥也呆在当场,他知道我与朋友同住,却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就是他的猪朋狗友曾经花钱请去撑场的发廊妹与按摩女。
阿丽是一个容易自来熟的人,她立即说:“我记得你叫彪哥!刘小姐生日那天,你与阿冰唱奸夫的爱!”
时间过了这么久,她竟然还记得他的名字,彪哥向她伸出大拇指:“靓女,你厉害!等我有钱当老板了,请你当秘书,保证没有搞不定的事。”
阿丽说:“秘书倒不敢,我没有什么文化,请我当招待,专门让我倒茶递水就行了。”
这本是一句玩笑话,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阿丽最终会为彪哥“搞定”很多事,甚至“搞定”一些人。
这是我当时想都想不到的事。年轻女人的前途,谁会预料得到呢,但凡有一张好些的面孔,便可不按常理出牌,也能赢个痛快。
与阿丽和胜男打了招呼,彪哥便自顾自地走进我房间,好像他与我已经非常熟悉一样。阿丽与胜男向我翻白眼,意思是说“原来你与这个男人暗渡陈仓”。
我懒得应付她们,忙不迭地跟了进去,他示意我关上门,还跑到门边听了一个动静,才说:“我若早知道你与这些人住在一起,昨晚一定睡不着觉。”
我解释说:“她们不是什么坏人,就算在发廊与按摩场做,都是卖艺不卖身的。”
他忍俊不禁地笑:“你以为是旧社会?现在艺与身还分得开?钱给多了,艺就是身,身就是艺,艺身都是猪肉,喜欢哪块割哪块。”
我也笑,第一次发现他如此有趣,但不得不认为他说得有理。
他说:“我不怀疑她们本质上是好人,但她们在那种品流复杂的地方,你却不得不防范她们。”
我再次笑了:“我有什么好防范的,挣的钱不如她们多,认识的朋友也不如她们多,如果真有什么事,我还得她们打救。”
他低声提醒我:“你现在身家百万呢。”未说完自己倒笑了,显得开心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