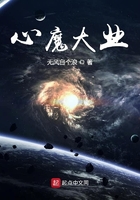翠屏镇春晖医馆,在斜阳的余晖中,匆匆地跑进了一个身着儒袍的十四五岁大的少年,头上满布着细汗,来不及喘口气,就大声的呼叫道:
“大夫,大夫,我爹呢?他怎么样了”
医馆内的人纷纷侧目,只见少年身量大概六尺。一头乌发被一方青灰色布帕包在脑后,衣袖处有一摊墨渍,好似不小心打翻了墨盒,沾染上了墨水,未脱稚气的脸上满是焦急惶恐二色。
还不待医馆医护大声喝止其不要吵闹,堂里蹲在墙角的一个汉子立马站了起来,向着少年走了过来。
“大郎,你终于来了,唉,快去看看你爹吧,你爹怕是……唉。”
少年一看中年汉子的表情,心底冒出一股凉气,爹爹千万千万不要有事。
少年和汉子穿过医馆门堂,进了后院廊下的一个简易木棚里。里面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大夫站在木床边。
看到木床上那个下半身被血糊住,一截带血的骨头从小腿处横刺出来,触目惊心,此等惨状,让少年险些站不稳。这时站在老大夫身边的另一位大汉向着少年走了过来。
“大朗,你们来了,一块听听大夫怎么说吧,唉”大汉摇了摇头,一脸的严肃对着少年说道。
“大夫,我爹他如何了,伤能治吗?”少年向着山羊胡大夫问道。
大夫粗黑的脸上满是岁月刻画的痕迹,倒是显得胡子越发的雪白,看着面前这个俊秀少年一脸焦急的模样,叹了口气说道:
“这位命是保住了,但只怕,只怕,这双腿是保不住了。”
少年听到前半句,先是一喜,可随之听到后一句,顿时一惊,便上前抓住大夫的双手大声喊道:
“大夫,求求你,求求你,你一定要保住我爹的双腿啊,我爹还不到四十,这叫他下半辈子咋活啊,大夫,求求你。”
大夫看着少年通红的眼眶,无奈的说道:
“这是真的没办法了,或许在州城还有救,可在咱们镇只能保其一了,实在是拖不得,州城距咋们镇上没有两天的行程到不了,这骨伤又拖不得,只得做选择了,没办法啊。”
少年听到大夫如此说道,知道是没什么希望了,这翠屏镇只此一家春晖医馆,只得向大夫拱了拱手,弯下腰说道:
“请大夫全力施救,小子不胜感激。”
只是那颤抖的身子,诉说着此刻的可怕与不安。
……….
清晨,晨光洒向大地,一个农家小院里坐这个身量单薄的丫头,观其面容似有十一二岁,瘦削的脸庞露出几份娇弱,让人徒生怜惜,一双沉静的眸子,看不出喜忧。
只是那一汪秋水似的眸子,倒映着那吐露晨光的青蓝色天空,让带着病容的面庞,陡然生丽,一下子将姿容提升了几分,让人难以生忘。
春儿,你这丫头,怎么不声不响的坐这儿了,你身子还没有好利索,你别又添了病气,快随奶奶进屋。
大宝那小子还睡的流哈喇子呢,你昨天可把他吓坏了,如今好了,可要看顾好自己的身子,奶奶没福气,留不住自己的儿子儿媳,可是再不能失去你们两个了。
你们要是有个好歹,可让我怎么活哦,让我下去怎么向你爹娘交代,你可要好好的,你爹娘在天之灵会保佑咱们的”
杨氏从堂屋出来,一面走一面说,待走到谢春儿的身前,就要用手搀坐在树墩上的谢春儿。
“奶奶,我昨天睡了一觉,身上发了汗,今早感觉好多了,待在屋子里闷的慌,就想出来透透气,活动活动身子。”
谢春儿看到老人一脸焦急的模样,心里也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只是屋子里实在气闷,便想出来看看,呼吸一下这古代的新鲜空气,不成想,到让老人家担心了。
杨氏看了看谢春儿,见她今天脸色红润了许多,不似昨天那般的苍白,心里稍安,便对谢春儿说道:
“那春儿你在这儿坐着,要是冷了就赶紧回去,奶奶这就给你熬药去,你还别说,镇上春晖医馆的许老大夫医术真好,一副药下去,你就大好了。”
说着去了西厢灶房煎药去了。
谢春儿听到这儿了,暗道一声对不住,真的谢春儿香魂早已远逝,换上了我这21世纪的孤客了。谢春儿依靠着院中的老枣树的树干,欣赏着这古代的纯绿色无污染的美景。
杏花村坐落在一方黄土塬上,不过是一个三十几户的小村落,大概200来人,此时放眼望去,零零散散的有几户人家飘起了炊烟,直直的往上,飘散在青蓝色的晨空中。
杏花村东面紧贴着翠屏山脚,翠屏山不高,自西向东绵延了二十几里,因着夏季浓翠欲滴,宛如一座绿色的屏障,保护着翠屏镇,以及它身周的十几个小村落,是以得名翠屏山。
周围十几个村也辖在翠屏镇下,杏花村就坐落在翠屏山西边脚下,只是现在放眼望去,山上只蒙了一层新绿,树木花草皆在抽芽,自然看不了那苍翠欲滴的盛景。
杏花村北面和西面都是深沟,沟下也长满了树木,村民们柴火都是从沟里捡拾或砍伐来的,倒也应了那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是杏花村民靠沟便就吃沟了。
这一狭长的黄土塬至杏花村五里地之外的地方渐渐宽阔起来,方圆十几里的镇所,翠屏镇便就在此处。
谢春儿他们住在村尾靠近北沟,只有宋谢两家比邻而居。
原来十几年前就只有谢家一家,宋家两口子和谢春儿的娘都是在十几年前河东府发大水,逃荒而来。
乔氏一家死的死,散的散,及至杏花村全家就只有乔氏孤身一人,在村民的撮合下,等荒年过去,就和谢栓子结了连理,算是安稳了下来。
同样宋家两夫妻也是如此,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乡归宗,便就在谢家隔壁扎了根。
太阳又往上升了升,此时整个村子才算醒了过来,炊烟袅袅,子嚎母骂,鸡犬相闻,一番田园生活景象。
村子里各处点缀的十几颗老杏树呼应着翠屏山上,山沟里的水桃花、野杏树鼓起了花苞,隐隐透着桃红色,惹人喜爱,处处透着的生机,也让谢春儿的心里莫名的安稳。
谢春儿将视线转到了自家院子里,三座茅草屋成品字形分布,最大的坐落在南面,自然是自己奶奶和弟弟住着的堂屋,西厢最小,奶奶正在里面熬药,东厢是自己的闺房。
整个院落宽阔干净,西南角有棵老核桃树,自谢春儿生下来就有了,此时未抽新芽的老核桃树和隔壁宋家的杏树枝干交错,核桃树的青白,杏树的黑枯形成鲜明的对比。
核桃树下靠着灶房屋檐的一面,堆着一堆农具。
不远处,还有棵四年树龄的香椿树,立在那儿,这还是谢春儿十岁那年从沟里挖回的幼苗,转眼四年过去,不说如亭盖,但也见其生姿。
村里眼之所及的家里几乎都燃起了炊烟,只是和自家隔一堵矮墙的宋家竟没燃起炊烟。
是了,宋家大郎还在镇上照看自己的父亲,只借他人之口给宋家娘子报了一生平安。
如今家里只剩怀胎十月的宋家娘子一人,眼看即将临产,如今家里撑天的还在镇上,又如何能让宋家娘子安心,这时候没有燃起炊烟,倒也能理解。
只是俩家素来交好,宋猎户还不时的送个野鸡啥的,让家里解解馋,等会还是得让奶奶去宋家看看,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撑着枣树的树干坐起来,透过用几根木头做的栅栏门,距北沟二十米的地方就是谢宋俩家的耕地,俩家合起来也就五六亩地的样子,虽说住的离村子中心远,倒也下地砍柴来的方便。
院门外还长着一棵三人环抱的槐树,树上还有未落尽的槐荚,被微风吹的沙沙作响,门外西面靠近宋家的一端还长着一棵花椒树和一棵桃树,枝干伸过矮墙,插进院子。
“春儿,快来,药熬好了,快进来,趁热喝了。”
杨氏从灶房伸出头来,对着谢春儿喊道。
“哎,知道了,奶。”
谢春儿向着厨房走去,春日带点凉意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落下一道长长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