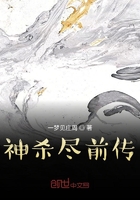安庆市是西部某省的城市。
李一泓是安庆市的名人。
“城市”二字,在中国是一种概念,在别国是另一种概念。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多的国家,故人口百万左右的城市,在我国只能算是中等城市。即使是中等城市中,也只能属于偏小的。而在别国,尤其在西欧各国,除了它们的首都,人口百万左右的城市,毫无疑问该算是大城市了。
百余年前,全世界总人口才十六亿多。那时北京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了,超百万。而现在,连深圳这一座二十几年前才开始形成的城市,仅常住人口就四五百万了,加上流动人口,过七百万。三十年前毁于一旦的唐山,市区人口又达到四五百万了。人口多了,城市占地面积今非昔比。至于西方国家那类二三十万的城市,如今在中国连一座大城市的区都够不上,充其量只能算是县级市,小县城而已。
想想吧,以北京为例,仅海淀一区,人口已多达一百几十万,而朝阳区比海淀区还要大。海淀区的一个街道,比如学院路街道,竟将近二十万人口。
二十年前安庆便是一座小小的县城,有十几万人口。占地面积也很小,但很紧凑。它是一座古城。虽古,却又默默无闻。古城得由古代名人衬托着,方能显出古的历史价值。安庆历史上并没出过什么古代名人,它的古从不曾被任何人任何方面重视过。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二十几年间,“安庆”的人口已经八十余万了。它周边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形形色色的房地产开发商买断,建起了一处处市民小区。而一处处农村随之消失,一批批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人口;那是中国农民们几辈子以来的梦想。于是它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市政府鼓励农民们变成城市人口,只要在城市周边买得起一处商品房,就会获得城市户口。许多农户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家中凡是能出外打工挣钱的人都出去了。房价竟也像大城市一样在持续上涨,只不过不像大城市的房价涨得那么离谱那么疯狂。已经变成为城市人口的农民,自然很是庆幸。举动晚了一步,梦想尚未实现的农民,对房价的上涨难免心急火燎,枉自叹息,更加只争朝夕地挣钱,或迫不及待地借钱。
安庆市周边一环一环的新城区,将老城区围在中央,扩展的情形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如出一辙。然而老城区的面貌,尚没被拆到体无完肤的地步。政府鼓励农民落户城市的政策一如既往。官员们巴望安庆市的人口突破百万。百万人口的市领导,在省里更容易受到重视,自己也觉得有面子。
可以这么说,如今安庆市的人口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十几年前的农民,对新的身份特别珍惜,都尽量显出既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又是文明的城市人的觉悟。他们都明白,如果不愿被视为城市里的二等居民甚或差等居民,最好自觉地那样。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老居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新居民们的面前,也都尽量地友善着、谦虚着,那体现为一种明智。他们心里也都明白,如果并不,那么烦恼的将是自己。何况,这一座城市的人口多了,规模大了,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起码,从此消除了区区小县城居民的心理阴影。古今中外,县城居民大抵都有两种心理——其一是小图安,怡然自得,知足常乐;其二是在大城市人面前的自卑。现在他们不怎么自卑了,即使出现在省城,自报家门说是“安庆人”时,那语调,那表情,多少有点神气活现了。而省城里的人们,也每每开始对“安庆人”刮目相看了。尽管摆放在全国一比,安庆的发展速度并不惊人,但在西部省份,却近乎神速了。
总而言之,安庆是一座人心相当稳定的城市。虽然还远谈不上和谐,但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忧的不稳定因素。目前如此。
安庆市稳定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文化馆。
如今,文化馆的文化作用,在许多城市里已若有若无,连文化馆本身,也十之八九名存实亡了。
但安庆市文化馆对安庆市所起到的文化作用却依然责无旁贷而又无可取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市民,对于农村文化娱乐的种种形式仍存眷恋,情有独钟。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老市民在文化娱乐心理上亦多半怀旧,文化馆乃是保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文化故乡”、温馨的“娱乐场景”。一言以蔽之,对于安庆市,文化馆的文化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甚至等同于文化部。
老百姓对文化馆厚爱有加,对文化馆的活动热忱参与,深情支持,使供职于文化馆的人们个个都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只要能使老百姓高兴、快乐,他们任劳任怨。他们自称是群众文化生活的调味者,乐此不疲。在新兴之城市,反而有这么一种过去时的文化现象保留着,令人欣慰。
李一泓这一位安庆市的名人,是文化馆的副馆长。除了正馆长齐家轩,他是馆里唯一的另一位“领导”,副科级。只要带“长”并且管人,便是“领导”。哪怕只管一个人,也是那一个人的“领导”。安庆人对“领导”二字的定位很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一种定位就深入人心了。李一泓和齐家轩管着十二个人呢,自然都是没有争议的“领导”。李一泓除了是文化馆副馆长,还是市“古体诗词爱好者联谊会”的会长、“舞狮爱好者协会”的会长、“收藏爱好者协会”的会长、“书画爱好者协会”的会长……总而言之,民间头衔不少。而使他名人地位最为巩固的民间头衔是——“安庆市太极拳爱好者协会”的终身会长。
李一泓不仅是安庆市的名人,还是安庆市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人。罩在他身上的传奇色彩一多半是从他父亲身上转移过来的,一少半才是他自己生发了的。
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农家子弟。而他的父亲李志达却曾是老安庆县城里威名远扬的太极拳师。当年,安庆县城里最富有的商绅严世鹏极为敬重李志达的武德和人品,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了李志达。但商绅的女儿却没成为李一泓的母亲,她在和他父亲成婚前死于匪患。李志达为了安慰痛不欲生的严世鹏,也为了报答人家对他的垂爱,遂认人家为义父并郑重发誓十年不娶。李志达从此为严世鹏担负起了保家护店之责,同时继续教人习武,收点儿学费,自己养活自己,一点儿也不沾义父的光。本愿做他老丈人却不料做了他义父的严世鹏,越发感到他品行难得,干脆投一笔资,买一处宅院,使他教人习武有了固定的场所。李志达的徒弟成倍地多起来,挂牌势在必行了。而他坚决不以自己的名字挂牌,非以严世鹏的名字挂牌不可。严世鹏又哪里拗得过他呢?最终只得违愿而依。于是择个吉日,邀请小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齐来捧场相庆,设宴、舞狮、放鞭炮、唱戏,热闹之中悬挂起一块体体面面黑漆红字的大牌匾是“世鹏武馆”。这么一段从头到尾的过程,从前的县志里详细记载着。徒弟多了,收入自然也多了。李志达从中扣除少许的生活费用,其余尽数交到严世鹏的老账房那儿。严世鹏不解了,说:“志达你这个人啊,咱俩都是义父子关系了,你还何必在钱财方面和我划得这么清呢?我女儿已死,我又再没有儿女了,将来遗产还不都得归在你名下么?你还年轻,别太省吃俭用亏待自己,该花该用,就花就用吧!我严世鹏虽然身在商道,但毕竟也是个仁义之人,也顾惜名声,也要好口碑。你的做法,我打心里佩服。可传出去,免不了飞短流长,岂不是使我授人以柄了么?”
李志达听罢就给严世鹏跪下了。他说:“义父啊,你对我的恩德,我一辈子铭记在心。你将来的遗产,却绝对不应该属于我……”
严世鹏急了,说:“不应该属于你,那应该属于谁呢?我连至亲的亲人也没一个了,一辈子苦心经营置下的这份家业,若临死前一总儿分散给穷人,我还舍不得。传给你,我不认为会辱没了你的什么清名……”
李志达说:“我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清名不清名的呢?我不是顾虑那个,也根本不配顾虑那个。论清名,义父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灾荒年月,济穷救难也一向慷慨大方,义父才是一个配考虑身后之名的人啊!”
严世鹏问:“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李志达便趁机劝义父重立遗嘱,说:“一份家业,这样那样,其实都不如捐给了社会的好……”
严世鹏又问:“当今时局动荡不安,兵荒马乱,贪官污吏多多,怎么就算捐给社会了呢?倘白白肥了男盗女娼之辈,我在九泉之下多懊恼啊!”
那李志达膝行近前,仰脸望着义父,言恳意切地说:“义父啊,想咱们中国,时运也衰,民心也散,定非仅靠几个仁人志士的努力,便能拯救,便能振兴的。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义子虽识字不多,平日里但凡有闲,书也喜欢看,报也喜欢读的。某些有识之士,在书中报上,主张教育救国。我读了看了,自然也会替咱们中国想一想,便觉得他们的主张不无道理。又联想咱们安庆县,十几万人口,竟连一所中学都没有。义父将来何不将偌大一份遗产托付给县里可信任的人们,要求他们用以办起一所中学呢?果而如此,将来的人们,一定会纪念着您,连我也会觉得光荣。那光荣,就等于是义父留给我的最好遗产了啊!……”
严世鹏说:“即使我依你所言,又为什么非信任别人呢?我在安庆县虽也不乏过从甚密的朋友,可要论及‘信任’二字,非你莫属啊!”
李志达道:“义父啊,我是一个见识短浅、能力有限的人。此等大事,我做不成啊!”
那严世鹏就沉吟起来,良久,慢条斯理地说出一句话:“我本以为我已把你看得很透,今日听了你几番话,还是错看了你。”
李志达不安了,流下泪来,说:“义子感激义父的知遇之恩,自然要经常为义父思考身后之事,所思所想,绝无私利左右。倘义父认为荒唐,还望不生反感。否则义子日后心存惶恐,就不知再该怎样了……”
严世鹏则起身离开座位,将他扶起,说:“你多心了,我的意思是,想不到你不但有一等的仁义,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我以前竟不了解你这一点,所以惭愧啊。来来来,跟我去书房里,咱们父子筹划筹划……”
如此这般,严世鹏的遗嘱当日重写了。他坚持在遗嘱中将李志达列为第一执行人。李志达无奈,只得默认。
翌年,严世鹏去世,那是一九四五年。在病床上得知日本人投降了,精神为之一振,主动要吃一碗鸡汤面。刚吃几口,碗落于地……
第二年,“世鹏中学”在安庆县落成,首批招了二百余名学生。
这一切,县志里也有记载……
至于李志达的武功究竟有多高,老辈人口中传说多多。县志里只记载了一件重要的事——某年有拨土匪扬言要血洗安庆县城,说李志达如果有胆量到他们指定的地点去会他们,也可以开恩,不那么做了。严世鹏给李志达临时凑了一笔钱,劝李志达远走他乡,躲此一劫。武馆的弟子们却聚集起来,发誓非与土匪们血战一场不可。李志达并未逃走,还驱散了弟子们。他对严世鹏说,他心里也明白,土匪们不是真要血洗县城,而是专冲着他个人下帖子的。是劫躲不过。倘若自己逃走了,不但被土匪们耻笑,自己本县的英名也灰飞烟灭了。那自己他日还能再回到安庆县来么?土匪都是欺软怕硬的人,一旦被他们觉得安庆县城里连条汉子都没有,放心大胆地闯入县城胡作非为烧杀奸掠一番是很可能的。所以,自己得去会会他们,以诚相见,或许反能于杀气笼罩之际,为全县人的安危争取到一份转机……
他就去了。
刚在匪巢里的一把宾椅上坐定,背后上来两条大汉,一人伸出一只右手,往他双肩上按将下来。土匪中也有武艺高强的人啊,李志达的双肩感觉到了两股大力的压迫,却不动声色。眨眼间,但听一阵裂响。匪首低头一看,四只椅腿连同李志达的双脚,不但使几块方砖碎了,而且塌陷下去了。匪首顿时抱拳拱手,起身施礼,说是手下人调皮,只不过想跟李师傅开开玩笑,还望李师傅海涵。接着匪首设宴款待他,推杯交盏之间,用短刀挑起一片好肉送至李志达嘴边,请他“尝尝咸淡”。李志达咔嚓一口,连一寸刀尖都咬断在口中了,嚼了几嚼,咽下肚去。还说:“不咸不淡,就是脆骨没剔干净。”
一桌无法无天的猛人目瞪口呆。
结果是,匪首和李志达拜了把兄弟……
小县城的县志,大抵总有些演义成分的。但那一拨土匪,以后再也没怎么滋扰过安庆县城,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
……
新中国成立后,安庆县的第一代执政者们,当年便将“世鹏中学”改为“安庆一中”。他们认为,中学是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摇篮,怎能以全县第一号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资本家的钱是哪儿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劳苦大众获得的吗?生时剥削劳苦大众不算,死了还要用剥削来的钱为自己树碑,企图流芳百世,是可忍,孰不可忍?!校园内严世鹏的一座半身像,也理所当然地被砸了……
那一年,“世鹏中学”,不,“安庆一中”,已有七百余名学生了……
“世鹏武馆”也被认为是一个将可能聚众闹事、给新政权添麻烦的地方。由一队武装人员前去,强行摘牌宣布取缔。
李志达据理力争,一再声明自己是一个从内心里拥护新政权的人,绝对不会将武馆变成使新政权不放心的地方。天下从此太平了,谁也不必再靠武功自我保护了,习武只不过成了一件强身健体之事,对新中国是有益无害的……
因为他与本县头号资本家那种义父子的关系,对方不信任他。他越表白,人家越不信任。何况他还和土匪拜过把兄弟!
武馆解散后,李志达成了一个身无长技、无业可操的人。自思继续在县城里待下去,以后的日子不会太顺心,便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
执掌新政权的众,也不愿让他这么样的一个人再待在县城里了,所谓正中下怀,当即准许。但是呢,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近的村子,考虑到他这一个口碑不倒的人,在县城里的潜在影响仍存,还是有点不放心。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远的村子呢,又等于将他放任到监控视野以外去了,照样不放心。最终,替他确定了一个离县城不远不近的村子,叫“眺安村”。对于一个村子,它的名挺雅的,村里一位曾是说书人的老者给起的。安庆县城南面,八十余里以外便是山区了。那村在山的低坡上,坡下有一片农田,是农户们的命根子土地。山里还有几十个村一万余口人,也在安庆县的管辖范围之内。八十余里,说近它属于较远的村子之一;说远它毕竟并没远到山里边去,似乎正适合李志达这么一个没根据必须警惕却又没前提完全放心的人去落户……
那一年李志达三十六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精壮年龄,仍是一条光棍。五年后他终于在眺安村成了家,媳妇是本村的一个老姑娘,老丈人是那个给本村起了一个雅名的老者。
要说李志达这人,命里还真算挺有隐福的。虽只不过是一武人,却在旧式文化人半文化人们的心目中有好印象,都愿意将女儿(如果有的话)许配给他。
第二年,喜得一子,便是李一泓。
成为农民的李志达,虚心好学,也仗着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渐成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一九五八年农民“社员”化以后,工分册上,他的名字总是名列前茅。
李一泓自幼聪明伶俐,天生热爱纸笔。一点即悟,悟此通彼,所谓响鼓何须重锤。极顺利地读完小学,极轻松地就考上了县一中。当时县里已另外有了两所中学,但一中因为是最早的一所中学,又是当时唯一开有高中班的中学,名气自然大于二中、三中。然而他成为中学生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李一泓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又耐心可嘉地在学校里泡了一年。第二年还看不到一点恢复正常的希望,只得怅怅然夹起铺盖卷儿回家了,从此也成为眺安村的一名“社员”。一家三口,都是能挣工分的人,过起了相依为命、互让温饱的农村日子。
李一泓十九岁那一年,时来运转,县一中教语文的郑讯老师被从学校扫地出门,安置在文化馆当了一名馆员。郑老师的出身在当年倒是没什么问题,属于贫下中农子弟。但他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杂文,是令在党的人们十分恼火的,几乎被打成右派。大学母校的领导们念他出身还好,没正式给他戴帽子,属于“沾边”右派一类人。这样的人,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的中学做教师,实属幸运了。“文革”中又被“扫地出门”,却是自然而然之事。他颇有文艺才华,安庆县有文艺才华的人不多。在任何年代,主宰别人命运的优势者中,偶有惜才之人。郑老师幸运就幸运在,既有文艺才华,又被一个惜才之人暗中关照了一下。他档案中有一条结论是“可以利用,不可重用”。某个既主宰他命运又惜才的人,以“可以利用”四个字名正言顺地实行了对他的关照,否则文化馆那种“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沿阵地”,是不会允许他一个“沾边”右派的身影晃悠的。他还是一个书呆子型的人,扔给他一份工作,允许他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那么他就渐渐地心理平定了。到文化馆不久,他百折不挠地搞起了青年文艺爱好者学习班。那正是文艺比油腥对于胃肠还缺少的年代,他的努力获得了各行各业男女青年的响应,连不少外县的青年也闻风而至,他很快就成了青年文艺爱好者们所拥戴的人物。这情形某些人想挡都挡不住,还没有反对的理由,索性任他去搞。从中学教师变成青年文艺活动的率领者,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越搞越有声色,越搞劲头越足……
李一泓曾是安庆一中学生会的文艺委员,给郑老师留下过深刻印象。郑老师写了一封信,言词恳切而又不失师道尊严地要求李一泓务必参加到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活动中来。李一泓接信后,第二天就出现在郑老师的面前了。郑老师已苦心经营起了文学、戏剧表演、绘画、舞蹈等多类培训班。而小学五年级就在报上发表过儿童诗并获过奖的李一泓,竟加入了美术学习班。文学离政治太近了,老师便是前车之鉴。父母就自己这么一个儿子,何况父亲还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他怕自己因文学而惹出政治事端来。一旦落个什么罪名,没谁能替自己孝养父母啊!从此点可以看出,李一泓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个处世相当谨慎的人了。
李一泓在美术方面也很快就令人刮目相看了。这要感激他的母亲,最终要感激他母亲的父亲他的姥爷。曾是说书人的他的姥爷,还曾是一位民间的丹青能手,靠字画换过柴米油盐的。按现在的常识解释,那是隔代基因起了作用。但在当年,人们不晓得什么基因不基因的,只说他是个学什么钻什么的人。他画的一幅毛主席的半身油画像,被县革命委员会收去了,挂在常委会议室里。于是他因画而名,郑老师也跟着得意。出了名的李一泓,兴趣又转移了,热衷起表演来。演过“样板戏”中的杨子荣、郭建光,还演过芭蕾舞剧中的洪常青,连郑老师都评价他演得“神似”。郑老师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允许李一泓成为自己的助手,县革命委员会特批了。因为青年文艺爱好者培训班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确实活跃了本县的群众文艺生活,被省革命委员会树为典型,组织各县前来“取经”。安庆县因而也出名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觉提自己也很光荣。一光荣,就高兴。一高兴,就什么要求都好说了。
于是李一泓有了双重身份——一年三百六十几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是农民,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是县文化馆的编外人员。在那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生产队遵照县革委会的指示,给李一泓记队里的平均工分。而文化馆,每月发给他十二元的补贴……
爱情不期而至。舞蹈培训班有一个好看的姑娘爱上了他。人家是县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宁肯为了爱情放弃县城户口,下嫁到八十里外的眺安村去……
面临如此真挚的爱情,李一泓起初诚惶诚恐,完全发懵,不知如何是好。郑老师知道了,跟他谈了一次话,说自己很了解那姑娘,她的坚定不移是靠得住的。说李一泓如果错过了真爱,就是“二百五”了。
他自然不愿是“二百五”。于是由郑老师做证婚人,欢天喜地将姑娘娶回了眺安村的家。
新婚之夜,他问妻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妻子回答:“更是对我自己好。”
“更是对你自己好?”——他不解了,又问,“怎么就更是对你自己好?”
妻子回答:“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会很幸福。”
他凝视着妻子,忍不住接着问:“你是不是对幸福是什么还不太明白啊?”
妻子回答:“幸福是快乐。”
他说:“你把幸福理解得太简单了吧?”
妻子回答:“只要有了快乐,幸福就简单了。连快乐都没有,幸福才复杂。”
他沉思良久,轻叹道:“除了快乐,我也再没别的。那么我保证,以后尽量让你快快乐乐的。”
说罢,捧住妻子的脸,深情地吻了她一番。
李一泓说到也做到了——尽管生活是那么清贫,但妻子经常被他逗得咯咯嘎嘎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