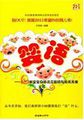诗云:
从来廉吏最难为,不似贪官病可医。
执法法中生弊窦,矢公公里受奸欺。
怒棋响处民情抑,铁笔摇时生命危。
莫道狱成无可改,好将山案自翻移。
这首诗是劝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虚衷舍己,体贴民情,切不可说我无愧于天,无怍于人,就审错几桩词讼,百姓也怨不得我。这句话,那些有守无才的官府,个个拿来塞责,不知误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怪不得近来的风俗,偏是贪官起身有人脱靴,清官去后没人尸祝,只因贪官的毛病有药可医,清官的过失无人敢谏的缘故。说便是这等说,叫那做官的也难。百姓在私下做事,他又没有千里眼、顺风耳,哪里晓得其中的曲直?自古道“无谎不成状”。要告张状词,少不得无中生有、以虚为实才骗得准。官府若照状词审起来,被告没有一个不输的了。只得要审口供。那口供比状词更不足信,原、被告未审之先,两边都接了讼师,请了干证,就像梨园子弟串戏的一般,做官的做官,做吏的做吏,盘了又盘,驳了又驳,直说得一些破绽也没有,方才来听审。及至官府问的时节,又像秀才在明伦堂上讲书的一般,哪一个不有条有理,就要把官府骗死也不难。那官府未审之先,也在后堂与幕宾串过一次戏了出来的。此时只看两家造化,造化高的合着后堂的生旦,自然赢了;造化低的合着后堂的净丑,自然输了,这是一定的道理。难道造化高的里面就没有几个侥幸的、造化低的里面就没有几个冤屈的不成?所以做官的人,切不可使百姓撞造化。我如今先说一个至公至明、造化撞不去的,做个引子。
崇祯年间,浙江有个知县,忘其姓名,性极聪察,惯会审无头公事。一日在街上经过,有对门两家百姓争嚷。一家是开糖店的,一家是开米店的,只因开米店的取出一个巴斗量米,开糖店的认出是他的巴斗,开米店的又说他冤民做贼,两下争闹起来。见知县抬过,截住轿子齐禀。知县先问卖糖的道:“你怎么讲?”卖糖的道:“这个巴斗是小的家里的,不见了一年,他今日取来量米,小的走去认出来,他不肯还小的,所以禀告老爷。”知县道:“巴斗人家都有,焉知不是他自置的?”卖糖的道:“巴斗虽多,各有记认。这是小的用熟的,难道不认得?”说完,知县又叫卖米的审问。卖米的道:“这巴斗是小的自己办的,放在家中用了几年,今日取出来量米,他无故走来冒认。巴斗事小,小的怎肯认个贼来?求老爷详察。”知县道:“既是你自己置的,可有什么凭据?”卖米的道:“上面现有字号。”知县取上来看,果然有“某店置用”四字。又问他道:“这字是买来就写的,还是用过几时了写的?”卖米的应道:“买来就写的。”知县道:“这桩事叫我也不明白,只得问巴斗了。巴斗,你毕竟是哪家的?”一连问了几声,看的人笑道:“这个老爷是痴的,巴斗哪里会说话?”知县道:“你若再不讲,我就要打了!”果然丢下两根签,叫皂隶重打。皂隶当真行起杖来,一街两巷的人几乎笑倒。打完了,知县对手下人道:“取起来,看下面可有什么东西?”皂隶取过巴斗,朝下一看,回复道:“地下有许多芝麻。”知县笑道:“有了干证了。”叫那卖米的过来:“你卖米的人家,怎么有芝麻藏在里面?这分明是糖坊里的家伙,你为何徒赖他的?”卖米的还支吾不认,知县道:“还有个姓水的干证,我一发叫来审一审。这字若是买来就写的,过了这几年,自然洗刷不去;若是后来添上去的,只怕就见不得水面了。”即取一盆水,一把筅帚,叫皂隶一顿洗刷,果然字都不见了。知县对卖米的道:“论理该打几板,只是怕结你两下的冤仇。以后要财上分明,切不可如此。”又对卖糖的道:“料他不是偷你的,或者对门对户借去用用,因你忘记取讨,他便久假不归。又怕你认得,所以写上几个字。这不过是贪爱小利,与逾墙挖壁的不同,你不可疑他作贼。”说完,两家齐叫青天,磕头礼拜,送知县起轿去了。那看的人没有一个不张牙吐舌道:“这样的人,才不枉叫他做官。”至今传颂以为奇事。
看官,要晓得这事虽奇,也还是小聪小察,只当与百姓讲个笑话一般,无关大体。做官的人,既要聪明,又要持重。凡遇斗殴相争的小事,还可以随意判断;只有人命、奸情二事,一关生死,一关名节,须要静气虚心,详审复谳,就是审得九分九厘九毫是实,只有一毫可疑,也还要留些余地,切不可草草下笔,做个铁案如山,使人无可出入。如今的官府只晓得人命事大,说到审奸情,就像看戏文的一般,巴不得借他来燥脾胃。不知奸情审屈,常常弄出人命来,一事而成两害,起初哪里知道?如今听在下说一个来,便知其中利害。
正德初年,四川成都府华阳县有个童生,姓蒋名瑜,原是旧家子弟。父母在日,曾聘过陆氏之女,只因丧亲之后,屡遇荒年,家无生计,弄得衣食不周。陆家颇有悔亲之意,因受聘在先,不好启齿。蒋瑜长陆氏三年,一来因手头乏钞,二来因妻子还小,故此十八岁上,还不曾娶妻过门。
他隔壁有个开缎铺的,叫做赵玉吾,为人天性刻薄,惯要在外人面前卖弄家私,及至问他借贷,又分毫不肯。更有一桩不好,极喜谈人闺阃之事。坐下地来,不是说张家扒灰,就是说李家偷汉,所以乡党之内,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年纪四十多岁,只生一子,名唤旭郎。相貌甚不济,又不肯长,十五六岁,只像十二三岁的一般。性子痴痴呆呆,不知天晓日夜。有个姓何的木客,家资甚富。妻生一子,妾生一女,女比赵旭郎大两岁。玉吾因贪他殷实,两个就做了亲家。不多几时,何氏夫妻双双病故。彼时女儿十八岁了,玉吾要娶过门,怎奈儿子尚小,不知人事;欲待不娶,又怕他兄妹年相仿佛,况不是一母生的,同居不便。玉吾是要谈论别人的,只愁弄些话靶出来,把与别人谈论。就央媒人去说,先接过门,待儿子略大一大,即便完亲,何家也就许了。及至接过门来,见媳妇容貌又标致,性子又聪明,玉吾甚是欢喜。只怕嫌他儿子痴呆,把媳妇顶在头上过日,任其所欲,求无不与。哪晓得何氏是个贞淑女子,嫁鸡随鸡,全没有憎嫌之意。
玉吾家中有两个扇坠,一个是汉玉的,一个是迦楠香的,玉吾用了十余年,不住地吊在扇上,今日用这一个,明日用那一个。其实两件合来值不上十两之数,他在人前骋富,说值五十两银子。一日要买媳妇的欢心,叫妻子拿去,任她拣个中意的用。何氏拿了,看不释手,要取这个,又丢不得那个;要取那个,又丢不得这个。玉吾之妻道:“既然两个都爱,你一总拿去罢了。公公要用,他自会买。”何氏果然两个都收了去,一般轮流吊在扇上。若有不用的时节,就将两个结在一处,藏在纸匣之中。玉吾的扇坠被媳妇取去,终日捏着一把光光的扇子,邻舍家问道:“你那五十两头如今哪里去了?”玉吾道:“一向是房下收在那边,被媳妇看见,讨去用了。”众人都笑了一笑。内中也有疑他扒灰,送与媳妇做表记的;也有知道他儿子不中媳妇之意,借死宝去代活宝的。口中不好说出,只得付之一笑。玉吾自悔失言,也只得罢了。
却说蒋瑜因家贫,不能从师,终日在家苦读。书房隔壁就是何氏的卧房,每夜书声不到四更不住。一日何氏问婆道:“隔壁读书的是个秀才,还是个童生?”婆答应道:“是个老童生,你问他怎的?”何氏道:“看他读书这等用心,将来必定有些好处。”她这句话是无心说的,谁想婆竟认为有意。当晚与玉吾商量道:“媳妇的卧房与蒋家书房隔壁,日间的话无论有心无心,到底不是一件好事,不如我和你搬到后面去,叫媳妇搬到前面来,使他朝夕不闻书声,就不动怜才之念了。”玉吾道:“也说得是。”拣了一日,就把两个房换转来。
不想又有凑巧的事,换不上三日,那蒋瑜又移到何氏隔壁,咿咿唔唔读起书来。这是什么缘故?只因蒋瑜是个至诚君子,一向书房做在后面的,此时闻得何氏在他隔壁做房,瓜李之嫌,不得不避,所以移到前面来。赵家搬房之事,又不曾知会他,他哪里晓得?本意要避嫌,谁想反惹出嫌来。何氏是个聪明的人,明晓得公婆疑她有邪念,此时听见书声,愈加没趣,只说蒋瑜有意随着他,又愧又恨。玉吾夫妻正在惊疑之际,又见媳妇面带惭色,一发疑上加疑。玉吾道:“看这样光景,难道做出来了不成?”其妻道:“虽有形迹,没有凭据,不好说破她,且再留心察访。”看官,你道蒋瑜、何氏两个搬来搬去弄在一处,无心做出有心的事来,可谓极奇极怪了;谁想还有怪事在后,比这桩事更奇十倍,真令人解说不来。
一日蒋瑜在架上取书来读,忽然书面上有一件东西,像个石子一般。取来细看,只见:
形如鸡蛋而略扁,润似密蜡而不黄。手摸似无痕,眼看始知纹路密;远观疑有玷,近觇才识土斑生。做手堪夸,雕斫浑如生就巧;玉情可爱,温柔却似美人肤。历时何止数千年,阅人不知几百辈。
原来是个旧玉的扇坠。蒋瑜大骇道:“我家向无此物,是从哪里来的?我闻得本境五圣极灵,难道是他摄来富我的不成?既然神道会摄东西,为什么不摄些银子与我?这些玩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要他怎的?”又想一想道:“玩器也卖得银子出来。不要管他,将来吊在扇上,有人看见要买,就卖与他。但不知价值几何,遇着识货的人,先央他估一估。”就将线穿好了,吊在扇上,走进走出,再不见有人问起。
这一日合该有事,许多邻舍坐在树下乘凉,蒋瑜偶然经过。邻舍道:“蒋大官读书忒煞用心,这样热天,便在这边凉凉了去。”蒋瑜只得坐下。口里与人闲谈,手中倒拿着扇子,将玉坠掉来掉去,好启众人的问端。就有个邻舍道:“蒋大官,好个玉坠,是哪里来的?”蒋瑜道:“是个朋友送的,我如今要卖,不知价值几何?列位替我估一估。”众人接过去一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作声。蒋瑜道:“何如?可有个定价?”众人道:“玩器我们不识,不好乱估,改日寻个识货的来替你看。”蒋瑜坐了一会,先回去了。众人中有几个道:“这个扇坠明明是赵玉吾的,他说把与媳妇了,为什么到他手里来?莫非小蒋与他媳妇有些勾而搭之,送与他做表记的么?”有几个道:“他方才说是人送的。这个穷鬼,哪有人把这样好东西送他?不消说是赵家媳妇嫌丈夫丑陋,爱他标致,两个弄上手,送他的了,还有什么疑得?”有一个尖酸的道:“可恨那老王八平日轻嘴薄舌,惯要说人家隐情,我们偏要把这桩事塞他的口。”又有几个老成的道:“天下的物件相同的多,知是不是?明日只说蒋家有个玉坠,央我们估价,我们不识货,叫他来估,看他认不认,就知道了。若果然是他的,我们就刻薄他几句,燥燥脾胃,也不为过。”算计定了。
到第二日,等玉吾走出来,众人招揽他在店中,坐了一会,就把昨日看扇坠估不出价来的话说了一遍,玉吾道:“这等何不待我去看看?”有几个后生的,竟要同他去,又有几个老成的,朝后生摇摇头道:“叫他拿来就是了,何须去得?”看官,你道他为什么不叫玉吾去?他只怕蒋瑜见了对头,不肯拿出扇坠来,没有凭据,不好取笑他,故此只叫一两个去,好骗他的出来。这也是虑得到的去处。谁知蒋瑜心无愧怍,见说有人要看,就交与他,自己也跟出来。见玉吾高声问道:“老伯,这样东西是你用惯的,自然瞒你不得,你道价值多少?”玉吾把坠子捏了,仔细一看,登时换了形,脸上胀得通红,眼里急得火出。众人的眼睛相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相在蒋瑜脸上,蒋瑜的眼睛没处相得,只得笑起来道:“老伯莫非疑我寒儒家里,不该有这件玩器么?老实对你说,是人送与我的。”玉吾听见这两句话,一发火上添油,只说蒋瑜睡了他的媳妇,还当面讥诮他,竟要咆哮起来。仔细想一想道:“众人在面前,我若动了声色,就不好开交,这样丑事扬开来,不成体面。”只得收了怒色,换做笑容,朝蒋瑜道:“府上是旧家,玩器尽有,何必定要人送?只因舍下也有一个,式样与此相同,心上踌躇,要买去凑成一对,恐足下要索高价,故此察言观色,才敢启口。”蒋瑜道:“若是老伯要,但凭见赐就是,怎敢论价?”众人看见玉吾的光景,都晓得是了,到背后商量道:“他若拼几两银子,依旧买回去灭了迹,我们把什么塞他的嘴?”就生个计较,走过来道:“你两个不好论价,待我们替你们作中。赵老爹家那一个,与迦楠坠子共是五十两银子买的,除去一半,该二十五两。如今这个待我们拿了,赵老爹去取出那一个来比一比好歹。若是那个好似这个,就要减几两;若是这个好似那个,就要增几两;若是两个一样,就照当初的价钱,再没得说。”玉吾道:“那一个是妇人家拿去了,哪里还讨得出来?”众人道:“岂有此理,公公问媳妇要,怕她不肯?你只进去讨,只除非不在家里就罢了,若是在家里,自然一讨就拿出来的。”一面说,一面把玉坠取来藏在袖中了。玉吾被众人逼不过,只得假应道:“这等且别,待我去讨;肯不肯明日回话。”众人做眼做势地作别。蒋瑜把扇坠放在众人身边,也回去了。
却说玉吾怒气冲冲回到家中,对妻子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说完,捶胸拍桌,气个不了。妻子道:“物件相同的尽多,或者另是一个也不可知。待我去讨讨看。”就往媳妇房中,说:“公公要讨玉坠做样,好去另买,快拿出来。”何氏把纸匣揭开一看,莫说玉坠,连迦楠香的都不见了,只得把各箱各笼倒翻了寻。还不曾寻得完,玉吾之妻就骂起来道:“好淫妇,我一向如何待你?你做出这样丑事来!扇坠送与野老公去了,还故意东寻西寻,何不寻到隔壁人家去!”何氏道:“婆婆说差了,媳妇又不曾到隔壁人家去,隔壁的人又不曾到我家来,有什么丑事做得?”玉吾之妻道:“从来偷情的男子,养汉的妇人,个个是会飞的,不须从门里出入。这墙头上,房梁上,哪一处扒不过人来,丢不过东西去?”何氏道:“照这样说来,分明是我与人有什么私情,把扇坠送他去了。这等还我一个凭据!”说完,放声大哭,颠作不了。玉吾之妻道:“好泼妇,你的赃证现被众人拿在那边,还要强嘴!”就把蒋瑜拿与众人看、众人拿与玉吾看的话备细说了一遍。说完,把何氏勒了一顿面光。何氏受气不过,只要寻死。玉吾恐怕邻舍知觉,难于收拾,只得倒叫妻子忍耐,吩咐丫环劝住何氏。
次日走出门去,众人道:“扇坠一定讨出来了!”玉吾道:“不要说起,房下同媳妇要,她说娘家拿去了,一时讨不来,待慢慢去取。”众人道:“他又没有父母,把与哪一个?难道送她令兄不成?”有一个道:“他令兄与我相熟的,待我去讨来。”说完,起身要走。玉吾慌忙止住道:“这是我家的东西,为何要列位这等着急?”众人道:“不是,我们前日看见,明明认得是你家的,为什么在他手里?起先还只说你的度量宽宏,或者明晓得什么缘故把与他的,所以拿来试你。不想你原不晓得,毕竟是个正气的人,如今府上又讨不出那一个,他家又现有这一个,随你什么人,也要疑惑起来了。我们是极有涵养的,尚且替你耐不住,要查个明白;你平素是最喜批评别人的,为何轮到自己身上,就这等厚道起来?”玉吾起先的肚肠,一味要忍耐,恐怕查到实处,要坏体面。坏了体面,媳妇就不好相容。所以只求掩过一时,就可以禁止下次,做个哑妇被奸,朦胧一世也罢了。谁想人住马不住,被众人说到这个地步,难道还好存厚道不成?只得拼着媳妇做事了。就对众人叹一口气道:“若论正理,家丑不可外扬。如今既蒙诸公见爱,我也忍不住。一向疑心我家淫妇与那个畜生有些勾当,只因没有凭据,不好下手。如今有了真赃,怎么还禁得住?只是告起状来,须要几个干证,列位可肯替我出力么?”众人听见,齐声喝彩道:“这才是个男子。我们有一个不到官的,必非人类。你快去写起状子来,切不可中止。”
玉吾别了众人,就寻个讼师,写一张状道:
告状人赵玉吾,为奸拐戕命事:兽恶蒋瑜,欺男幼懦,觊媳姿容,买屋结邻,穴墙窥诱。岂媳憎夫貌劣,苟合从奸,明去暗来,匪朝伊夕。忽于本月某夜,席卷衣玩千金,隔墙抛运,计图挈拐。身觉喊邻围救,遭伤几毙。通里某等参证。窃思受辱被奸,情方切齿,诓财杀命,势更寒心。叩天正法,扶伦斩奸。上告。
却说那时节成都有个知府,做官极其清正,有“一钱太守”之名;又兼不任耳目,不受嘱托。百姓有状告在他手里,他再不批属县,一概亲提。审明白了,也不申上司,罪轻的打一顿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毙诸杖下。他生平极重的是纲常伦理之事,他性子极恼的是伤风败俗之人。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赵玉吾将状子写完,竟奔府里去告,知府阅了状词,当堂批个“准”字,带入后衙。次日检点隔夜的投文,别的都在,只少了一张告奸情的状子。知府道:“必定是衙门人抽去了。”及至升堂,将值日书吏夹了又打,打了又夹,只是不招。只得差人叫赵玉吾另补状来。状子补到,即便差人去拿。
却说蒋瑜因扇坠在邻舍身边,日日去讨,见邻舍只将别话支吾,又听见赵家婆媳之间吵吵闹闹,甚是疑心。及至差人奉票来拘,才知扇坠果是赵家之物。心上思量道:“或者是他媳妇在梁上窥我,把扇坠丢下来,做个潘安掷果的意思。我因读书用心,不曾看见,也不可知。我如今理直气壮,到官府面前照直说去。官府是吃盐米的,料想不好难为我。”故此也不诉状,竟去听审。
不上几日,差人带去投到,挂出牌来,第一起就是奸拐戕命事。知府坐堂,先叫玉吾上去问道:“既是蒋瑜奸你媳妇,为什么儿子不告状,要你做公公的出名?莫非你也与媳妇有私,在房里撞着奸夫,故此争锋告状么?”玉吾磕头道:“青天在上,小的是敦伦重礼之人,怎敢做禽兽聚麀之事?只因儿子年幼,媳妇虽娶过门,还不曾并亲,虽有夫妇之名,尚无唱随之实。况且年轻口讷,不会讲话,所以小的自己出名。”知府道:“这等他奸你媳妇有何凭据,什么人指见,从直讲来。”玉吾知道官府明白,不敢驾言,只将媳妇卧房与蒋瑜书房隔壁,因蒋瑜挑逗媳妇,媳妇移房避他,他又跟随引诱,不想终久被他奸淫上手,后来天理不容,露出赃据,被邻舍拿住的话,从直说去。知府点头道:“你这些话,到也像是真情。”又叫干证去审。只见众人的话,与玉吾句句相同,没有一毫渗漏,又有玉坠做了奸赃,还有什么疑得?就叫蒋瑜上去道:“你为何引诱良家女子,肆意奸淫?又骗了许多财物,要拐她逃走,是何道理?”蒋瑜道:“老爷在上,童生自幼丧父,家贫刻苦,励志功名,终日刺股悬梁,尚博不得一领蓝衫挂体,哪有功夫去钻穴逾墙?只因数日之前,不知什么缘故在书架上捡得玉坠一枚,将来吊在扇上,众人看见,说是赵家之物,所以不察虚实,就告起状来。这玉坠是他的不是他的,童生也不知道,只是与他媳妇并没有一毫奸情。”知府道:“你若与她无奸,这玉坠是飞到你家来的不成?不动刑具,你哪里肯招!”叫皂隶:“夹起来!”皂隶就把夹棍一丢,将蒋瑜鞋袜解去,一双雪白的嫩腿,放在两块檀木之中,用力一收,蒋瑜喊得一声,晕死去了。皂隶把他头发解开,过了一会,方才苏醒。知府问道:“你招不招?”蒋瑜摇头道:“并无奸情,叫小的把什么招得?”知府又叫皂隶重敲。敲了一百,蒋熬不过疼,只得喊道:“小的愿招!”知府就叫松了。皂隶把夹棍一松,蒋瑜又死去一刻,才醒来道:“他媳妇有心到小的是真,这玉坠是她丢过来引诱小的,小的以礼法自守,并不曾敢去奸淫他。老爷不信,只审那妇人就是了。”知府道:“叫何氏上来!”
看官,但是官府审奸情,先要看妇人的容貌。若还容貌丑陋,他还半信半疑;若是遇着标致的,就道她有诲淫之具,不审而自明了。彼时何氏跪在仪门外,被官府叫将上去,不上三丈路,走了一二刻时辰,一来脚小,二来胆怯。及至走到堂上,双膝跪下,好像没有骨头的一般,竟要随风吹倒,那一种软弱之态,先画出一幅美人图了。知府又叫抬起头来,只见她俊脸一抬,娇羞百出,远山如画,秋波欲流,一张似雪的面孔,映出一点似血的朱唇,红者愈红,白者愈白。知府看了,先笑一笑,又大怒起来道:“看你这个模样,就是个淫物了。你今日来听审,尚且脸上搽了粉,嘴上点了胭脂,在本府面前扭扭捏捏,则平日之邪行可知,奸情一定是真了。”看官,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只因知府是个老实人,平日又有些惧内,不曾见过美色,只说天下的妇人毕竟要搽了粉才白,点了胭脂才红,扭捏起来才有风致,不晓得何氏这种姿容态度是天生成的,不但扭捏不来,亦且洗涤不去,他哪里晓得?说完了又道:“你好好把蒋瑜奸你的话从直说来,省得我动刑具。”何氏哭起来道:“小妇人与他并没有奸情,叫我从哪里说起?”知府叫拶起来,皂隶就幺喝一声,将她纤手扯出。可怜四个笋尖样的指头,套在笔管里面,抽将拢来,教她如何熬得?少不得娇啼婉转,有许多可怜的态度做出来。知府道:“他方才说玉坠是你丢去引诱他的,他倒归罪于你,你怎么还替他隐瞒?”何氏对着蒋瑜道:“皇天在上,我何曾丢玉坠与你?起先我在后面做房,你在后面读书引诱我;我搬到前面避你,你又跟到前面来。只为你跟来跟去,起了我公婆疑惑之心,所以陷我至此。我不埋怨你就够了,你倒冤屈我起来!”说完,放声大哭。知府肚里思量道:“看他两边的话渐渐有些合拢来了。这样一个标致后生,与这样一个娇艳女子,隔着一层单壁,干柴烈火,岂不做出事来?如今只看他原夫生得如何,若是原夫之貌好似蒋瑜,还要费一番推敲;倘若相貌庸劣,自然情弊显然了。”就吩咐道:“且把蒋瑜收监,明日带赵玉吾的儿子来,再审一审,就好定案。”
只见蒋瑜被送入监中,十分狼狈。禁子要钱,脚骨要医,又要送饭调理,囊中没有半文,叫他把什么使费?只得央人去问岳丈借贷。陆家一向原有悔亲之心,如今又见他弄出事来,一发是眼中之钉、鼻头之醋了,哪里还有银子借他?就回复道:“要借贷是没有,他若肯退亲,我情愿将财礼送还。”蒋瑜此时性命要紧,哪里顾得体面?只得写了退婚文书,央人送去,方才换得些银子救命。
且说知府因接上司,一连忙了数日,不曾审得这起奸情。及至公务已完,才叫原差带到,各犯都不叫,先叫赵旭郎上来。旭郎走到丹墀,知府把他仔细一看,是怎生一个模样?有《西江月》为证:
面似退光黑漆,发如鬈累金丝。鼻中有涕眼多脂,满脸密麻兼痣。劣相般般俱备,谁知更有微疵。瞳人内有好花枝,睁着把官斜视。
知府看了这副嘴脸,心上已自了然。再问他几句话,一字也答应不来,又知道是个憨物。就道:“不消说了,叫蒋瑜上来。”蒋瑜走到,膝头不曾着地,知府道:“你如今招不招?”蒋瑜仍旧照前说去,只不改口。知府道:“再夹起来!”看官,你道夹棍是件什么东西,可以受两次的?熬得头一次不招,也就是个铁汉子了;临到第二番,莫说苔杖徒流的活罪宁可认了,不来换这个苦吃,就是砍头刖足、凌迟碎剐的极刑,也只得权且认了,捱过一时,这叫做“在生一日,胜死千年”。为民上的要晓得,犯人口里的话,无心中试出来的才是真情,夹棍上逼出来的总非实据。从古来这两块无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官的人少用他一次,积一次阴功,多用他一番,损一番阴德,不是什么家常日用的家伙离他不得的。蒋瑜的脚骨前次夹扁了,此时还不曾复原,怎么再吃得这个苦起?就喊道:“老爷不消夹,小的招就是了!何氏与小的通奸是实,这玉坠是她送的表记。小的家贫留不住,拿出去卖,被人认出来的。所招是实。”知府就丢下签来,打了二十。叫赵玉吾上去问道:“奸情审得是真了,那何氏你还要他做媳妇么?”赵玉吾道:“小的是有体面的人,怎好留失节之妇?情愿叫儿子离婚。”知府一面教画供,一面提起笔来判道:
审得蒋瑜、赵玉吾比邻而居。赵玉吾之媳何氏,长夫数年,虽赋桃夭,未经合卺。蒋瑜书室,与何氏卧榻止隔一墙,怨旷相挑,遂成苟合。何氏以玉坠为赠,蒋瑜贫而售之,为众所获,交相播传。赵玉吾耻蒙墙茨之声,遂有是控。据瑜口供,事事皆实。盗淫处女,拟辟何辞?因属和奸,姑从轻拟。何氏受玷之身,难与良人相匹,应遣大归。赵玉吾家范不严,薄杖示儆。
众人画供之后,各各讨保还家。
却说玉吾虽然赢了官司,心上到底气愤不过,听说蒋瑜之妻陆氏已经退婚,另行择配,心上想道:“他奸我的媳妇,我如今偏要娶他的妻子,一来气死他,二来好在邻舍面前说嘴。”虽然听见陆家女儿容貌不济,只因被那标致媳妇弄怕了,情愿娶个丑妇做良家之宝,就连夜央人说亲。陆家贪他豪富,欣然许了。玉吾要气蒋瑜,分外张其声势,一边大吹大擂,娶亲进门;一边做戏排筵,酬谢邻里:欣欣烘烘,好不热闹。蒋瑜自从夹打回来,怨深刻骨;又听见妻子嫁了仇人,一发咬牙切齿。隔壁打鼓,他在那边捶胸;隔壁吹箫,他在那边叹气。欲待撞死,又因大冤未雪,死了也不瞑目,只得贪生忍耻,过了一月有余。
却说知府审了这桩怪事之后,不想衙里也弄出一桩怪事来。只因他上任之初,公子病故,媳妇一向寡居,甚有节操。知府有时与夫人同寝,有时在书房独宿。忽然一日,知府出门拜客,夫人到他书房闲玩,只见他床头边帐子外有一件东西,塞在壁缝之中。取下来看,却是一只绣鞋。夫人仔细识认,竟像媳妇穿的一般。就藏在袖中,走到媳妇房里,将床底下的鞋子数一数,恰好有一只单头的,把袖中那一只取出来一比,果然是一双。夫人平日原有醋癖,此时哪里忍得住?少不得“千淫妇、万娼妇”将媳妇骂起来。媳妇于心无愧,怎肯受这样郁气?就你一句,我一句,斗个不了。正斗在热闹头上,知府拜客回来,听见婆媳相争,走来劝解,夫人把他一顿“老扒灰、老无耻”骂得口也不开。走到书房,问手下人道:“为什么缘故?”手下人将床头边寻出东西,拿去合着油瓶盖的说话细细说上。知府气得目定口呆,不知哪里说起,正要走去与夫人分辨,忽然丫环来报道:“大娘子吊死了!”知府急得手脚冰冷,去埋怨夫人,说她屈死人命。夫人不由分说,一把揪住,将面上胡须捋去一半。自古道:“蛮妻拗子,无法可治。”知府怕坏官箴,只得忍气吞声,把媳妇殡殓了。一来肚中气闷不过,无心做官,二来面上少了胡须,出堂不便,只得往上司告假一月,在书房静养。终日思量道:“我做官的人,替百姓审明了多少无头公事,偏是我自家的事再审不明。为什么媳妇房里的鞋子会到我房里来?为什么我房里的鞋子又会到壁缝里去?”翻来覆去想了一月,忽然大叫起来道:“是了,是了!”就唤丫环一面请夫人来,一面叫家人伺候。及至夫人请到,知府问前日的鞋子在哪里寻出来的?夫人指了壁洞道:“在这个所在。你藏也藏得好,我寻也寻得巧。”知府对家人道:“你替我依这个壁洞拆将进去。”家人拿了一把薄刀,将砖头撬去了一块,回复道:“里面是精空的。”知府道:“正在空处可疑,替我再拆。”家人又拆去几块砖,只见有许多老鼠跳将出来。知府道:“是了,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只见家人伸手进去,一连扯出许多物件来,布帛菽粟,无所不有。里面还有一张绣纸,展开一看,原来是前日查检不到、疑衙门人抽去的那张奸情状子。知府长叹一声道:“这样冤屈的事,叫人哪里去伸!”夫人也豁然大悟道:“这等看来,前日那只鞋子也是老鼠衔来的。只因前半只尖,后半只秃,他要扯进洞去,扯到半中间,高底碍住扯不进,所以留在洞口了。可惜屈死了媳妇一条性命!”说完,捶胸顿足,悔个不了。
知府睡到半夜,又忽然想起那桩奸情事来,踌躇道:“官府衙里有老鼠,百姓家里也有老鼠,焉知前日那个玉坠不与媳妇的鞋子一般,也是老鼠衔去的?”思量到此,等不到天明,就叫人发梆,一连发了三梆,天也明了。走出堂去,叫前日的原差将赵玉吾、蒋瑜一干人犯带来复审。蒋瑜知道,又不知哪头祸发,冷灰里爆出炒豆来,只得走来伺候。知府叫蒋瑜、赵玉吾上去,都一样问道:“你们家里都养猫么?”两个都应道:“不养。”知府又问道:“你们家里的老鼠多么?”两人都应道:“极多。”知府就吩咐一个差人,押了蒋瑜回去,“凡有鼠洞,可拆进去,里面有什么东西,都取来见我。”差人即将蒋瑜押去。不多时,取了一粪箕的零碎物件来。知府叫他两人细认,不是蒋家的,就是赵家的。内中有一个迦楠香的扇坠,咬去一小半,还剩一大半。赵玉吾道:“这个香坠就是与那个玉坠一起交与媳妇的。”知府道:“是了,想是两个结在一处,老鼠拖到洞口,咬断了线掉下来的。”对蒋瑜道:“这都是本府不明,叫你屈受了许多刑罚,又累何氏冒了不洁之名,惭愧惭愧。”就差人去唤何氏来,当堂吩咐赵玉吾道:“她并不曾失节,你原领回去做媳妇。”赵玉吾磕头道:“小的儿子已另娶了亲事,不能两全,情愿听她别嫁。”知府道:“你娶什么人家女儿,这等成亲得快?”蒋瑜哭诉道:“老爷不问及此,童生也不敢伸冤,如今只得哀告了:他娶的媳妇,就是童生的妻子。”知府问什么缘故,蒋瑜把陆家爱富嫌贫,赵玉吾恃强夺娶的话一一诉上。知府大怒道:“他倒不曾奸你媳妇,你的儿子倒奸了他的发妻,这等可恶!”就丢下签来,赵赵玉吾重打四十,还要问他重罪。玉吾道:“陆氏虽娶过门,还不曾与儿子并亲,送出来还他就是。”知府就差人立取陆氏到官,要思量断还蒋瑜。不想陆氏拘到,知府叫他抬头一看,只见发黄脸黑,脚大身矬,与赵玉吾的儿子却好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知府就对蒋瑜指着陆氏道:“你看她这个模样,岂是你的好逑?”又指着何氏道:“你看她这种姿容,岂是赵旭郎的伉俪?这等看来,分明是造物怜你们错配姻缘,特地着老鼠做个氤氲使者,替你们改正过来的。本府就做了媒人,把何氏配你。”唤库吏取一百两银子,赐与何氏备妆奁。一面取花红,唤吹手,就叫两人在丹墀下拜堂,迎了回去。后来蒋瑜、何氏夫妻恩爱异常。不多时宗师科考,知府就将蒋瑜荐为案首,以儒士应试,乡会联捷。后来由知县也升到四品黄堂,何氏受了五花封诰,俱享年七十而终。
却说知府自从审屈了这桩词讼,反躬罪己,申文上司,自求罚俸。后来审事,再不敢轻用夹棍。起先做官,百姓不怕他不清,只怕他太执;后来一味虚衷,凡事以前车为戒,百姓家家尸祝,以为召父再生。后来直做到侍郎才住。只因他生性极直,不会藏匿隐情,常对人说及此事,人都道:“不信川老鼠这等利害,媳妇的鞋子都会拖到公公房里来。”后来就传为口号,至今叫四川人为川老鼠。又说传道四川人娶媳妇,公公先要扒灰,如老鼠打洞一般,尤为可笑。四川也是道德之乡,何尝有此恶俗?我这回小说,一来劝做官的,非人命强盗,不可轻动夹足之刑,常把这桩奸情做个殷鉴;二来教人不可像赵玉吾轻嘴薄舌,谈人闺阃之事,后来终有报应;三来又为四川人暴白老鼠之名,一举而三善备焉,莫道野史无益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