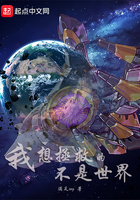霍根婉拒了郭宇和吴贝安相送的请求,他独自到地铁站,坐车回家。
下了地铁,到达光明小区,已经是晚七点半。万家灯火都明亮着,只有霍根的世界是黑色的。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身心俱疲。
上到楼顶,霍根照例掏出钥匙。
还没等他把钥匙插进孔里,门已开了。
一个披着头发,穿睡衣的女孩站在门后,有些害羞。
她至多二十一,二十二的岁数。齐腰的长发,小巧的瓜子脸。女孩水汪汪的眼睛,迷途小鹿一样剔透纯净,她细细的眉毛微微蹙着,看起来怯生生。配上她娇小的身躯,更显得楚楚动人,也更能激起男人灵魂深处的保护欲。
不过,霍根看不见,他从没见过这个叫鹿耳瓶的护工。
“霍大哥,你回来拉?”女孩倚着门。
“嗯。”
霍根应了一声。晚归,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在家等着你,这种感觉足以让人暖彻全身。
进了屋,鹿耳瓶扶着霍根,坐到沙发上。她倒了一杯开水,将药递过去。问道:“你今天还头疼没有?”
“我出门带了药。”霍根推开女孩递来的药丸,又问:“小鹿,你给我买瑞士糖了吗?”
他回来前口袋里的糖就已经没了,才几个小时没吃,实在记挂着。
“喏,二十四块钱。”鹿耳瓶取来一大包瑞士糖,摊开手。
“钱包在我衣兜里,你自己拿。”
霍根迫不及待地接过糖,撕开包装袋。将手伸进去,抓起一把糖,又松开。感受着一颗颗瑞士糖,从手指缝隙溜走,让他身心愉悦。
鹿耳瓶接过钱包,数出三张十块的,又从自己衣兜里拿出六元放了进去。这才放心地将三张十元人民币,放进自己小小的精致的荷包里。
小姑娘对待钱的态度实在认真,每一块钱在她那里都像是有生命的。
“别找了,那六块当给你的跑腿费。”霍根听见了动静。
“不行,该我的一分不能少,不是我的一分不能要。”鹿耳瓶极认真地说。
也许是糖份起了作用,霍根鼻子又灵了。他嗅了嗅,说道:“我不在家,你也不用泡面吃啊。你大胆买菜,我给你报账。”
“霍大哥,我就爱吃泡面,你晚上吃了没?”
“吃过了。”霍根又撒谎了,他傍晚实在没有任何食欲。
鹿耳瓶这才放下心,重新抱着抱枕,坐在他的身边,继续看着电视里的搞笑综艺。
整整一集节目,女孩时而傻笑,时而更傻的笑。
霍根又剥了块瑞士糖,丢进嘴里。任由那糖味,在味蕾翻滚化开。耳边女孩的笑声掺杂在综艺里,出奇的和谐协调。
他的思绪随之飞到了九天之外,许是飞得太远,霍根的头颅承受不住,开始疼的厉害。残存的神志像一片偶然飘进万里苦海的枯叶,波涛汹涌中,随风起,伴浪落,摇摆不定……
意识越来越模糊,身体越来越软,像一片羽毛飘着飘着……
一双神奇的手,给黑白的世界描添上了彩色。
墙上的港台明星,八仙桌边的脚踩缝纫机。伸出天线的收音机,床脚的痰盂,木摇椅,破蒲扇。一台只知道摇头的落地扇。
昏昏的灯下,母亲踩着缝纫机,在补一件旧衬衣。父亲拿着心爱的紫砂壶,靠在沙发上,半睡半醒。妹妹正坐在自己膝盖上,写语文作业。电视机开着。
霍根瞥见桌上的台历,台历最上面的一页写着: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廿四;己卯年;兔。
“霍根,去买瓶醋来,一会儿吃饺子了。”
“妈,等我看完这集还珠格格就去。”
“这孩子,怎么越大越懒了。也不知道随谁。”
“那还不是给你惯的,小兔崽子,快滚去买醋。”
“爸,再等五分钟,就五分钟。”
“爸爸妈妈明天就去上海了,你这个样子,我们怎么放心让你留下,照顾妹妹?”
“妈妈别说了,我就去。别关我电视啊,也别让妹妹调台。”
“好勒,你快走吧。”
火!红色的火!到处都是!门倒了……大衣橱倒了……
木质的通红坍塌,铁质的弯曲变形。红的黑的,热气逼人。眼前全是可怕的红色,火舌吞吐,肆虐,张狂。
睁不开眼,身体像是要化了。
有人在说话,耳边全是哭声喊声,惨叫声。自己好似在火里煎熬,又好像在门外焦急。
使劲推着门,门被从外面锁上,怎么也推不开。
太热了,太热了,要化掉了,爸爸的脸,妈妈的脸,妹妹的脸,自己的脸,全都被可怕红色吞噬,要融化了,全都要融化了,他们的脸逐渐模糊。
“爸爸!妈妈!妹妹……”
……
他睁开眼,什么也看不见。摸了摸头底下,什么也没有。
那些颜色一下就归于虚无了,巨大的失落感,包裹着霍根。
“是我啊,我是鹿耳瓶。霍大哥,你怎么出这么多汗?”
“我……我没事,只是做了个噩梦。”
霍根揉了揉脸,那个自信乐观永远打不倒的他,总是在早上醒来后,被披上穿好。
“你一般都在枕头底下放什么?”鹿耳瓶好奇地问。
霍根并未回答,反而转移话题:“现在几点了,你在这等了多久?”
阳光从屋外投射进来,屋内气温很高。他知道时间应该到中午了,鹿耳瓶的耐心倒也是好,竟忍着没有叫自己起床。
“十二点多拉,我把午饭做好了,你洗洗脸就吃吧。”
鹿耳瓶乖巧地回答。
“哦。”霍根应了一声,没有起身,只是掏出手机。
他的手机设置了盲人模式,一查,十来个未接电话,全是吴贝安在两个多小时前打来的。
霍根拨打了回去,电话很快通了。
“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
“一个好消息,昨天我们连夜走遍了全市的租车行。对比监控录像,再加上查调租车人的身份信息。今早终于锁定了嫌疑人。”
“是谁?”
“市立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罗咏好。”
吴贝安的声音很激动:“他在家中有两辆汽车的情况下,租借了一辆传祺SUV,至今仍未归还。尸块被发现的早晨,他天没亮就驾驶着那辆租来的车,到过炮台山。”
“那多半是这个人了,坏消息呢?”霍根揉着鼻子。
“你怎么知道有坏消息?”女孩有些惊讶。
“因为找到犯罪嫌疑人,你一点都不开心。快说吧!”
“坏消息就坏透了,这家伙死了!”吴贝安确实很沮丧。
“就死了?不能够吧!”
霍根嗅到了事情有一丝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