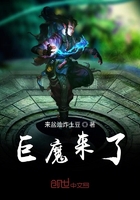田蚡回到相府,正待沐浴更衣,宾客告之,淮南国的中郎伍被刚刚来府上拜谒过,说是淮南王刘安的车队,已经过了函谷关,午后便可抵达长安。田蚡心头一喜,大声吩咐道:“马上备车,去灞上接王爷。”
田蚡五短身材,鼻高耳阔,双目微凸,看上去有些暴睛。一张四方大脸上,放松时和蔼可掬,板起时则有股豪横的霸气。其貌虽不扬,可母亲曾请义姁为他相过面,义姁说他这种身材与面相,在相法上是贵格,日后必会大发达。果然,不到四十岁的年纪,他便封侯拜相,成为朝廷中炙手可热的显贵,对此,他颇为自负。他边更衣,边端详着铜镜中那张因酒色过度而略显臃肿了的脸,吩咐候在一旁的府丞道:“若是宫里头有事情找我,就说我去了长乐宫,出迎淮南王的事,莫声张。”
刘安是老淮南王刘长的长子。刘长是高祖与赵美人所生,是刘邦的幼子,极受宠爱。刘邦打下天下不久,为保刘氏的天下长治久安,开始有意剪除因功被封为王的异姓诸侯。高祖十一年,刘邦伐灭淮南王英布,将他的地盘转封给了刘长。
刘长的母亲赵美人,原是赵王张敖的宫人。高祖八年,征伐韩信,途经赵国时,张敖献赵美人侍寝,竟而受孕,赵王将其安置在离宫奉养。贯高等人谋反事发后,赵美人连同赵王张敖等一干人犯,被押解至河内郡听鞫。赵美人请求狱吏转告高祖,自己已有幸怀了身孕,是皇帝的骨血。刘邦当时正全力以赴在案子上,无心理会这件事情。于是,赵美人再托人,走辟阳侯的路子。辟阳侯名審食其,被吕后倚为腹心,他若尽力,不难借吕后之力救出赵美人。不想吕后得知此事后,心存妒忌,不仅不为她说情,反而将事情压住不报,而審食其亦没有为之力争。赵美人绝望,生下刘长后,怨而自杀。狱吏抱着婴儿请示刘邦,刘邦悔恨不已,将孩子交与吕后抚养,赵美人则被葬于家县真定。
刘长自幼失母,寄人篱下,常遭吕后及其男宠審食其的取笑侮辱,他隐忍不发,脸上一副憨态,心里却渐渐由怨愤而扭曲变态。长大后,刘长勇武过人,力能扛鼎,性格亦骄蹇刚直。孝文皇帝即位后,由于是仅存的亲兄弟,对他格外优容,每每宽宥其骄恣不法的行为。孝文皇帝三年,刘长进京奉朝请,亲赴辟阳侯府求见,酬酢间,突然以藏于怀中的金锤击杀審食其,并命令从人将其碎尸泄愤。之后刘长驰诣阙下,肉袒谢罪道:臣母无罪,辟阳侯能救而不争,致臣母冤沉海底,其罪一;吕后杀赵隐王如意母子,幽死赵幽王刘友,辟阳侯不争,其罪二;吕后封诸吕为王,欲以危刘氏宗亲,辟阳侯非但不争,反而阿附吕氏,其罪三。臣杀郦食其,为母复仇,为赵隐王母子与赵幽王[15]复仇,为天子诛贼臣,一时愤激擅杀,伏阙请罪。孝文皇帝悯其志在为母复仇,特谕赦免,没有治他的罪。
刘长是近支亲王,自恃尊贵,对文帝直呼“大兄”,又兼性格刚烈,好勇斗狠,往往一言不合,即怒目相向,自薄太后、太子至诸大臣皆对之敬惮有加。归国后,刘长益发骄恣不逊。不仅僭制逾礼,不奉汉法,甚至数次上书,口吻极不驯顺。文帝曾亲自作书切责,刘长不仅全无悔改之心,反而勾结朝臣、闽越与匈奴,试图谋反。事发后,文帝尽诛与谋者,将刘长全家发配到蜀郡严道县的邮亭服役。囚车就道后,刘长不堪其辱,于途中绝食自杀,留下了四个年幼的孤儿。
刘长死后,文帝悯其早死,将这四个孤儿都封作了侯。八年后,有好事者将兄弟之争编排成了民谣,曰: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言下似责难文帝待兄弟苛刻。文帝听到后笑笑说:“难道百姓以为朕贪图淮南的土地么!”于是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加封刘长已成人的三个儿子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衡山和庐江三国的国王。身为长子的刘安,与乃父作风迥然不同,自幼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长大后尤其好名誉,暗中以德行拊循百姓,树立名声。孝景皇帝前元三年,刘安二十五岁,七国构乱,他原打算响应,但为其国相所阻,刘安竟因此免祸。
刘彻即位后,刘安得知皇帝好儒术艺文,于是招致四方宾客术士数千人,其中出名者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和晋昌八人,及儒者大山、小山之徒。刘安与宾客,整日议论学问,著书立说,天文地理、仁义道德、古今存亡治乱之道与世间诡异飘渺之事,无所不论。撰述为内外百余篇,又有中篇八卷,专论神仙黄白之术,总名之曰《淮南鸿烈》。刘安将此书进献,大得皇帝的好感。刘彻曾试使之为《离骚》作传,刘安日出受诏,食时即撰写完毕,所费不过一个时辰。他还进献过《颂德》及《长安都国颂》,尽极歌功颂德之能事。由于摸准了皇帝的嗜好,刘安不露痕迹,总能逢迎得恰到好处,每次宴见,坐而论道,探讨政治得失和赋颂、方技,君臣侄叔两个都兴会淋漓,直到日暮掌灯时分,方才依依惜别。
刘安身材高大,眉目疏朗,留着一口美髯。进退行止间,既有从小锦衣玉食,长大南面为王养成的那份尊贵,又有由学问中浸淫出来的儒雅。从辈分论他是刘彻的叔父,不仅辈分高,且学问渊博、才思敏捷而又善于文辞,颇为皇帝所敬重。凡下达给淮南国的诏敕、信件,刘彻每每召司马相如等视草润色后方才发出,对刘安的景慕,可想而知。
田蚡得与刘安结识,是在淮南王上次进京奉朝请时。田蚡因得罪窦太后,被罢职家居,刘安以长辈的亲王,折节下交,在京期间,两人往来游宴无虚日。探知田蚡虚荣好货,刘安每每厚赠之,分别时,两人竟成了忘年之交。数年后,田蚡被拜为丞相,朝廷中有了这样一位有权势的朋友,刘安窃喜自己的钱用对了地方。田蚡则与之互通声气,朝廷中的机密大事,刘安知道得一清二楚。汉代的诸侯王,大致五年进京朝觐一次。刘安上次朝觐是在建元二年,转眼四年过去,这次再入长安,他已经是四十六岁的人了。
淮南国的车队到达枳道亭时,已经时近日中了。看到田蚡等在那里,刘安心里一喜,下车见礼道:“迎送诸侯乃太常[16]的职掌,怎敢劳动丞相的大驾!”
田蚡长揖道:“殿下乃高祖皇帝的嫡亲孙儿,连皇帝尚且拿殿下作长辈对待,能伺候王爷,是我们这些作臣子的荣幸,甚劳动?谈不上,谈不上,王爷客气了!”说罢,两人相对揖手,大笑起来。
刘安向坐在后面车子上的一位女子招了招手道:“陵儿,还不下车见过你田叔叔。”
田蚡觉得眼前一亮。那女子从车上一跃而下,身手甚为矫健。年纪也轻,不过十四五岁的样子。肤色白皙润泽,两只黑亮的眼睛深若潭水,波光潋滟,一头黑瀑似的长发松松地绾在脑后,瓒珥不施的她,却艳光逼人,不可方物。
“父王姓刘,哪里来的姓田的叔叔?”刘陵打量着田蚡,莞尔一笑。
刘安喝道:“陵儿不可放肆!当朝的丞相,天子的母舅,你田叔身份贵重。丞相与寡人情好无间,有如兄弟,当然称得上叔叔。快些与你田叔叔见礼。”说罢又对田蚡介绍道:“这是小女刘陵。此番进京,非缠着要跟来不可。寡人无奈,带了来。小女顽皮,打算在长安住一阵子,还要承望君侯日后多加看顾喽。”
“噢。田叔叔大安。陵儿初来乍到,不懂得京师的规矩,请田叔叔指教。”刘陵直视田蚡,笑语莺声,长揖着请安。
“哪里,哪里。都是自己人,用不着客气。”刘陵容色夺人,目光中有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在她的审视下,田蚡竟有了种说不清的感觉,既有些自惭形秽,又有些心旌摇动。真看不出,刘安竟会有如此出色的女儿。
刘安邀田蚡同乘一车。车驭是侍候他十几年的心腹,御术极为老到。四马并鞯,一溜小跑,宽敞的车身伴着嘚嘚的蹄声,款款而行,几乎觉不出颠簸。刘安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身旁的田蚡,田蚡仍是色迷迷的,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刘安心里生出一丝鄙夷,他咳了一声,堆出满脸的笑容。
“君侯,皇太后安好?”
“哦……还好,太后近来心思全在外孙女的婚事上。吾上封信中提起的事情,不知殿下以为如何?”修成君金俗,是太后王娡的长女,论起来也是田蚡的外甥女,她的女儿金娥年已及笄,到了出嫁的年纪。太后对这个女儿一直心怀愧疚,所以对外孙女的婚事看得格外重,一心要为她寻一门好人家,要田蚡在诸侯王中加紧物色。淮南国的太子刘迁年将弱冠,年龄相当,身份也贵重,田蚡早早就向刘安打过招呼,一心要成就这门婚事。
在这件事上,刘安心里很矛盾。金俗出身微贱,乃太后入宫前与平民所生,并非皇家血胤,根本配不上自家的门第。娶金蛾作太子妃,其他诸侯王背地的非议和耻笑,一定不会少。可与权势相比,门第又算得了什么!太后自觉亏欠女儿太多,对修成君母子格外看顾,结下这头亲事,与太后乃至皇帝的关系就更进了一步,金娥毕竟是刘彻的外甥女。想到这里,他有了决断。
“能与太后攀亲,幸何如之!待犬子行了冠礼,寡人即托君侯议亲。”
这下可以给太后一个喜讯了。田蚡极为满意,笑道:“都是皇室宗亲,这下亲上加亲了。今晚吾做东,为殿下洗尘接风。”
“君侯太客气了!还是寡人做东。天子这一向可好?”
“这要看这好指甚了。”
“怎么说?”听出田蚡话里有话,刘安诧异地问道。
“自打太皇太后崩逝后,再没人管得住上边了。这回闽越内乱,不战而胜,上边的心气更高了。眼下又盯住了西南夷和南粤,在边事上,仗着国家府库充实,上边的雄心大着呢。”
“是呀,寡人知道君侯的主张,也曾上书谏伐闽越,不想全无作用。今上身边有个名庄助的中大夫吧?”
“有。怎么?”
“今上派他出使南粤,回来路过淮南时,竟专程来王府,说是传达皇帝的谕意,实则申斥老夫。人倒是精明强干,不晓得他是怎么个背景,如此得天子之宠?”
“这个人,说起来倒是有些家学渊源。他父亲庄忌,善辞赋,与枚乘齐名。都在梁孝王那里作门客。建元元年举贤良文学,这小子对策当意,被今上擢为第一。此人巧舌如簧,皇帝每每令他和其他郎官与大臣廷辩。在征伐闽越这件事上,非但王爷,就是我这个丞相,也曾被他窘辱过呢。”
皇帝重用小臣,折辱大臣,显然已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日后的祸乱,搞不好就会伏机于此,倒是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刘安笑笑道:“皇上这个年纪,少年气盛,好大喜功。既存了经营四夷之心,也只好随他去了。谏阻无用,徒然招怨,寡人是不会再触这个霉头了。君侯放心,早晚碰了壁,皇帝方会知道国事艰难,不是想甚就能做甚的。”
田蚡心有灵犀似的笑笑,决定试探一下刘安。他近来失意于天子,除亲近太后以固宠外,也有外结诸侯巩固权位的心思。自梁王薨逝后,诸侯王中,淮南最盛。世事无常,这淮南王日后或许会大贵,倒是值得费心结交的呢。更何况,他还有这么一位妙龄好女。
“国事上顺,可在家事上,上边焦心得很呐。”
“怎么?”
“王爷难道想不到?上边与陈皇后结缡七八年,竟无一子半女,尤其不可解的是,后宫其他嫔妃也全无子息,殿下想想,这正常么?”田蚡话中有话,他看定刘安,双目灼灼,说出了一番令刘安既紧张又振奋的话来。
“王爷试想,这病若是在天子身上,就难得有子嗣,宫车一日晏驾,谁接位的可能最大?王爷是高皇帝的嫡亲孙儿,正值壮年,学识渊博,平日广行仁义,口碑遍传天下。够格承继皇室大位的,除去王爷,还能有谁!”田蚡侧过身子,躬身长揖,很有几分输诚的样子了。
刘安内心狂喜,可脸上却是惶惑不安的样子。他扶住田蚡,正色道:“天子富于春秋,哪里谈得上绝嗣?君侯莫妄测未来,况且此事非吾等为人臣者所宜言。我们先谈眼前的事,晚间还是寡人做东,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两家的亲事。这件事,若能蒙太后允准,寡人欲觐见长乐宫,太后那里,还请君侯为寡人先容。”
“这绝无问题。论起来,那女子还是我外甥孙女,这个亲家,我们算是做定了。”田蚡捋髯笑道。稍顿,他回首向后车瞟了一眼,凑到刘安的耳边,很恳切地说道:“还有件事情,不知王爷可能帮忙?”
“君侯莫客气,尽管说,尽管说!”
“内子故去已好二年了,中馈乏人。这继室,找,就要找个门第、模样都好的。我想要在刘氏宗亲中物色,物色到了,还要请王爷助成田某这件大事。”说罢,田蚡紧紧盯着刘安的反应,只等他开口应允,自己马上就可以毛遂自荐,做淮南国的女婿。
田蚡的心思,从他对女儿的频频顾盼之中,刘安已了然于胸。这个人,权势财色,无一不贪,人品卑下,自己是决不可能将爱女许给他的。可他位高权重,是皇帝、太后的近亲,又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况且,朝廷上的机密大事,离不开田蚡为他通气,若如他所言,日后自己果真有龙飞九五的机会,朝廷中还真不能没有他的合作,这个面子,还真就不能驳他。一念至此,他故作思索地沉吟了一会,一拍额头道:“有了!君侯这件事情,就落在寡人身上。可真是不能再巧了,君侯还记得燕王么?”
“燕王?刘定国?”
“正是。他有个妹妹,极美,已寡居数年。上次朝觐,他就托我在京师为之寻一户好人家。君侯大贵大富,运势正旺,这兄妹两个必定会满意的。燕王位在诸侯,妹子也是个翁主[17],门第足够,陪送也不会少。丞相若有意,孤愿作这个大媒。”
真是个老狐狸!田蚡心有不餍,却又不好回绝,于是颔首漫应之:“那么,便有劳殿下作伐了。”
两人一时无话,车入长安,田蚡要去长乐宫,换车告辞。看着他怏怏不乐的样子,刘安向随侍的家臣使了个眼色,笑道:“寡人备了礼物,一车劳君侯敬献给太后,还有一车就直送君侯的府上。都是些淮南的特产,不成敬意,请笑纳。”
望着侍从押解过来的两车方物,田蚡的脸上又有了笑意。“王爷太客气了。既是在京师,当然由我做东,尽地主之谊。晚间吾邀些大臣,就在舍下摆酒,为大王洗尘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