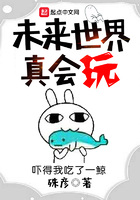行至桃花庄便是酉时,夏季日头极长。
进庄子的时候金乌堪堪停在海岸线上,待桌椅摆好,众人入座,这时早已点上的明灯才有了作用。
男堂女眷找好位置坐下,我这才细看。
除蕴哥儿,铮哥儿外的男堂便就是陪嫁来的“百合”所出的三姐儿赵楼和四哥儿赵寅。
两个人都算是乖巧可人儿的。姨娘上不了桌,这样算来便是九人,厅里便布了10人桌。
母亲同淑姨妈坐最上首,月姐儿蕴哥儿下排。
在其次便是我同囡囡,然后接着是争哥儿、寅哥儿、茵姐儿和楼姐儿。
淑姨妈是个极热情的人,每道菜都会细数是为谁准备的。
她做的很周全,在别人看来像是个风风火火,粗心大意的人。但是她却是很细致的,她会照顾到所有人,嫡庶不论。
“这是你极喜欢的麻糍。”她为母亲布菜,是母亲极喜爱的糖心麻糍。
母亲敛眉,将糖心麻糍放在碗底:“这个腻人涨肚,我吃一个就够了。其实我更喜欢京都的菜,有家里的味道。”
淑姨妈面上僵了一下,接着便更为热情的招待其他。
我大概明白母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子,但我听说幼时的母亲是很欢乐的,生于国府顶着郡主的头衔,顶尊贵的人物。
我回神看的时候,碗里已然多出了些许蟹黄和炒的金黄的年糕。
蕴哥儿坐在我边上,刚放下手中绢帕包着的蟹壳。
我顿了片刻,侧头笑:“蕴哥哥真了解我。”
我细细的将蟹黄,年糕吃完。给囡囡剥上些对虾,又挑了些蟹黄给她。并叮嘱:“蟹黄少吃些,若是贪凉了那可不好受。”
“囡囡知晓,都听姐姐的。”
食毕,我可以看得出来母亲吃的还是很欣喜的,她没有应小辈也无堵淑姨妈。
算是解铃还需细铃人。
天色渐晚,淑姨妈留母亲及几个哥儿姐儿在桃花庄歇下。母亲本是想回的,蕴哥儿却在中间劝阻,她便没再说什么了。
淑姨妈带诸各去安置住所的时候,络麽麽往后头来叮嘱我明朝回了庄子里午时一过回去,拜会居在扬州的外婆。
我应了是,络麽麽叹了口气:“老身知小姐是明事理的人儿不会同夫人计较,但还是辛苦小姐了。夫人的心结难解,是郁久成顽疾还得苦您几时。”
“麽麽言重了。”我细细听完她的话,忙道,“我只盼母亲能够心足意满,其他什么的也只是想多见她一面罢了。”
“小姐聪慧,可怜了这聪慧是从小受着苦得来的。”络麽麽有些悸然,偏身擦了擦泪,福了福身子往前头去了。
囡囡不懂,转头问我:“麽麽怎么总说姐姐苦?麽麽才苦,没有亲人的。”
我仰了仰头,眼泪只泛了点出来润了眼睛,然后才说:“姐姐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姐姐小时候总生病吧。”
囡囡皱眉,担忧的问:“姐姐现在长大了就不会生病了吧。”
我轻声“应不会了。”
夜里采儿将我头上的首饰一个个摘下,逞着采儿出去倒污水,我这才细细去看那玉簪子。这才发现那簪子是极好的白玉,中间的蔓延的四周清清爽爽,那颗络朱混圆剔透。
“小姐今儿个怎么不想收这簪子。”采儿出声我吓了一跳,才知道她就站在我身后。
“怎么突然在我后头。”我拍拍胸口回神。
采儿扶上我的肩膀给我按摩,叹了口气无奈:“小姐呐,我站在您身后许久了。走进来时有步子落地声的。您分神了才没发现我。”
也是,是我分神了。
“小姐…”
“廷哥儿来了!廷哥儿来了!”
采儿话刚出口,外头妈子从外堂往里头来边跑边喊。
我把簪子放在妆台上转头正好同采儿对视:“廷哥哥来了?”
采儿点了点头。
我疑惑呢喃:“怎么这么晚了也要过来?”
“小姐去瞧瞧不?”
“都洗漱完了,唉。可这灯是亮着的,如今熄了叫外人如何说我。”我心是不想去的,夜色华浓已是困的不行了,还要别好簪子穿了衣裳去寒暄。
“那姐儿去否?”采儿挽着我的发拿起不是放下不是。
我左右看了看镜子,叹了口气。想躲的怎么也是躲不过的,“给我挽起来吧。随意些,我套件衣裳就去。”
采儿应了是,她手很巧,没一会儿就做好了。我起身去拿衣裳,转头看她衣衫齐整:“倒是你随了缘分,妆面也没下衣裳也没脱。”
“那姐儿要上妆么?”采儿端着脂粉。
我思索着,上妆面要时候也忒长了,都是自家人,便摇了头。
出了门去,母亲和茵儿在院中央同淑月大姨、月姐儿一同,见我出来了月姐儿便道:“蕴哥儿说稍稍就来。”
我点头,再抬了头去看月儿,已经弯了角。朦朦胧胧的照在院子里,凉风习习,有些舒爽。没见铮儿、囡囡几个小辈,大概都睡下了。几个姨太庶孩子都是在别的院住的,由着大概不知道。
蕴哥儿不多时便来了,披了件厚些的外衫。他坐在轮椅上被十四推了过来,含着笑:“久等了久等了。我本是将歇下的,一听着衍廷来了就兴了头。”
淑月大姨引着往前头去,穿了窄门,从后堂进了大厅。
静默等着,不一会儿有人敲了大门来,看门小厮拔了门闩,厚重的门开了来。几个火把亮了整个大堂,一丛人里出来一挺拔俊朗的男子,火光辉映下的脸隐隐灭灭,到一行人站在大厅前同廊上的长明灯辉映才算清了五官,来人朗眉星目,头戴金玉冠,脂红卷金涛浪袍,脚蹬黑布牛底靴。正是———赵衍廷。
淑姨妈见了他忙迎上前去,“可算是来了。”
廷哥儿行礼,起身道“母亲。”
淑姨妈拍拍他的手背问:“路上可有缺着少着累着的。”
廷哥儿笑应:“未有缺的少的。”
淑姨妈又叹了口气:““你爹总说苦养儿,咱家不缺这些的,苦个什么劲儿。马车都不消的你坐,生生骑了半月的马。”
“这几日骑马倒是身子舒爽不少。总是在朝上束手束脚的,倒是如此自在。”廷哥儿安抚着。
月姐儿捂了嘴笑,“你母亲这两日没见你就可劲念着,虽嘴上不说,但我也瞧得出来。”
“来,衍廷。”淑姨妈拉了廷哥儿到母亲跟前来,“这是你络姨妈。”
廷哥儿行礼后带着笑道:“络姨妈好,总听母亲说道您,是个极雅致的。”
“虚夸了。数年没见哥儿了,又挺拔了些。”母亲淡淡着应了。(因为母亲常年在祠堂里所以是数年没见)
廷哥儿也没觉着尴尬又行上一礼表示离开。
蕴哥儿由十四推上前来,“丘杨(廷哥儿的表字)”
廷哥儿见到蕴哥儿满目欣喜,“长庚!(蕴哥儿的表字)”
“有两三年没见了吧。”蕴哥儿仰头看着廷哥儿,廷哥儿顺势蹲了下来。
“是啊,你如此才情倒被这身子骨白白拖累了。”廷哥儿叹气,“可好些了?”
月姐儿上前来嗔怪,“衍廷何苦这急急的来了,我叫人去府上听你说把我那新得的白貂皮子拿来给蕴哥儿的。”
“无妨,到时我遣人送去。”廷哥儿起身,转了头去看廷哥儿,“我晓得你,若你不收退了回来,我便三顾茅庐亲自给你送去。”
廷哥儿无奈,只叹了口气:“我知晓了,你这何苦呢。我那处用的吃的都不少的。”
“这皮子不同,是难得的珍贵物件。”月姐儿上前急解释。
他们说罢了,再到我面前来,“许久不见了乐妹妹。”
因着未上妆,我忙拿了扇子遮面,露了个眼来瞧他,没应话。我心里还是有些恼的,哥儿这晚还要来,叫女儿家睡不得妆也无时上的。
“怎么不说话,还躲在扇子后头。”
廷哥儿侧身来看我,我就又拿扇子挡“廷哥哥可别瞧了,妹妹今儿没来及上妆。”
“妹妹天仙似的人,没上妆也是好瞧的。”廷哥儿没再探身,站直了身子笑。
我见他笑的好看,侧了侧眼睛。
“今儿个也晚了。”淑姨妈抬头去看了看夜色,“阿木。”
廷哥儿的随身叫阿木,是个侗族人,肤色较黑,常扎着辫子再束冠。他从后堂过来行了一礼:“都准备好了,公子劳累先歇下吧。”
廷哥儿便同长辈行了礼,领着阿木跟淑姨妈去了。我们这厢才好各自散了去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