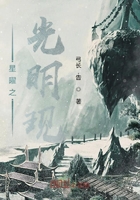“我是问,爷爷还活着吗?”
我妈手指从烟灰缸边夹起了烟卷,抽了一口,然后整个人放松地往沙发上靠下:“他声音有点怪,我有十几年没听到他的的声音了。”
“怎么个奇怪?”
“老了许多。”她从容地吐了一个烟圈。
我想起我十岁时,经常见到我爸跟爷爷吵架。这两人总是像看不惯对方似的。也许我爸跟爷爷的不和,就像我跟他一样。小时候,我从来没去过爷爷家,听说他很孤僻,脾气有点怪,后来他搬到了码头一带,他没给我们留地址,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隔年,我爸跟我说他已经去世了,我当时是信以为真的。
印象中,爷爷的模样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以前每次我问我妈关于爷爷的事,她都不愿意告诉我太多事,包括我爷爷是做什么的。她唯一提到的就是他的脾气比较古怪,与其他人难相处。
“他打电话来都说了些什么?”
“他想搬回住宅区生活。还说想见见你。”
“什么时候?”
“我记下了地址,你有时间可以去找找他。”她指着桌子上的电话,我走了过去,看见电话旁有张便条纸,上面有一行地址。
我妈又倒了一杯酒,我见状立即夺走了瓶子里剩下的白兰地。
“今晚早点休息。”我说。
她没看着我,而是专注地喝着杯子里倒出来的部份。我将瓶子盖紧,带回到了二楼卧室,放在我的桌子上。
夜里我好像听见我妈在楼下哭泣和呕吐的声音。我试着用毯子盖住自己耳朵,但心里却无法坦然,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家正徜徉在分裂的边缘。我的胸口又泛起了一阵刺痛。
我妈是一个能坚忍一切的女人,但是她的耐性并不是毫无止尽的。从最近开始,我就发现家里多了些空酒瓶,她正在以酗酒的方式来缓解自己。我真希望她的痛苦能够早点结束,如果一直藕断丝连着,终有一天她会病倒。
之后连续几天,我爸始终没回家。而我妈也跟没事发生一样,把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都扛了下来。吃晚饭时,她递碗给我,我碰到了她的手,那一下我感觉到她的手变得粗糙了不少。我记得我上次摸到她的手时,皮肤还是光滑紧致的。
至于红丝带,这些天上下班的日子里,仍旧频繁遇到他们出没,但是没有再发生像上次那样严重的事故了。我后来了解到红丝带是对议会一些政策不满,到处宣扬某些议员的阴谋论。正因为红丝带对社会造成了滋扰,久而久之,民众对他们产生了厌恶,所以才上演了上次那场冲突──民众与红丝带的对抗。
在电视新闻里,有议员在访谈中直指红丝带与地下组织勾结,企图破坏社会安宁。但是这个所谓的地下组织的言论,很多民众都是头一次听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灾后重建的社会里冒出了各种危险的组织了?
暂且不说红丝带的事。这几天大头都没来上班,听强人说他打电话到人事部请了一星期病假。周四下班我去他家找他,没等我开口,他妈反问我是否知道大头最近在干什么,我当时愣了。她说大头最近常常早出晚归,白天打电话找他却总是关机状态。我知道大头妈很担心他,所以编了个谎,告诉她大头最近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多,忙完了就会回来的。
大头这种反常的行为,我以前从来没遇见过,一时也不知道该去哪找他。我觉得可能他自己迟早会出现,与其费神在他身上,不如找点别的事情做,比方说继续调查一下当年搜索队的事情。上周末在疗养院调查老鬼的事情,还有那奇怪的梦里所见到的情景──藏在墙后面的数字,使我暗自认定了30年前搜索队的事情有蹊跷。我头一次对一件事如此的执着,而对真相的求知欲有时就像蚂蚁在啃咬我全身般疼痒难耐,所以我下定了决心要继续调查下去。
我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我该从哪儿开始调查。搜索队的事情发生在30年前,其中第一支搜索队迄今为止已有40年了。南岸岛上点年纪的人都应该对当年的事情有些印象,也许可以先从谁那里询问询问。
不过我平时认识的人不多,究竟该请教谁呢?一时半会我还没头绪,目光无意间落在客厅里的书架上,那儿摆放了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是我外公外婆抱着我时拍的,我顿时想到了自己从来没跟爷爷拍过照,我家也没有爷爷的照片。上次我妈说爷爷打电话来,想跟我见见,我为何不试着去拜访一下他,顺便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些什么。
想到这里心中有点小兴奋,但很快又觉得不妥。
我跟他近二十年没见,一见面就问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会不会太奇怪了?但是除了他,我确实想不到其他合适人选。
隔天下班我就照着便条纸上的地址找到了码头区一座古老的建筑物。那是间破仓库,看上去至少有50年历史,老远就能看到仓库屋顶掀开了一大片,只有一小部份被新旧不一的铁皮重新盖上了。
爷爷多年来都独居在这儿吗?
我有些踌躇不安地来到掉漆的铁门前,我又想起周一晚我妈说爷爷打电话来,他说他想见见我。他为什么会单单想见我?待会见面后,我又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冷不猝防,仓库的门开了。一个满头白发,弓着背的老人独自步了出来,他被站在门口的我吓了一跳,幸好及时扶住了墙才没摔倒,可他手上拿着的几本书却散落地上。
我忙道歉,并曲身帮他拾著书。我注意到这些书十分晦***名竟是&;lt;&;lt;人类灭亡史&;gt;&;gt;、&;lt;&;lt;宗教与种族战争&;gt;&;gt;、&;lt;&;lt;法西斯危机&;gt;&;gt;,我虽然对历史很感兴趣,却没去到这种偏门的钻研程度。
“雷子?”我听到老人有点惊讶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刚好把所有的书捡了起来,挺直了身子看向他。面前的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个子不高,脸上都是岁月磨砺的沧桑皱纹。他的声音听起来雄浑而陌生,但却充满了对我的熟悉感。他见我没反应过来,上前抬起一只手摸了摸我前额的头发,因为他比我矮,所以做起这个动作来有点吃力。但是这动作我很熟悉,感觉小时候的确有人这样摸我,这下我几乎可以断定他的身份了。
“爷爷?”
“嗯,差点没认出你。”他退后了半步,打量着我说。
说真的,我没想过重逢的场面是如此突兀,我刚才还在想该怎么打招呼。
“你现在就像你老爸年轻时一样强壮了。”他又说。
“我没觉得自己跟他很像。”
“我很久没见到你了,那时你大概只有那么高。”他把手掌平放在他的胸前,我觉得他并不是在怀念以前的我,听起来更像是普通的陈述。
“我也以为你……”
“以为我进坟墓了?”
“嗯。”
“哼,你那固执的老爸巴不得我早点两腿一伸。”我注意到他眉宇之间掠过了一丝不悦,语气也变得尖锐了不少。
“别提他了。其实我这次来看望你,是想顺便请教些事情。”
“你跟你老爸一样。”
“什么?”
“你跟他一样,目的性太强。”他的态度明显变得不是太友善起来。
“不,我只是想请教──”
“一样,你并不是存心来看望老头子我的,是不是?”
我开始明白为何我妈说爷爷脾气很怪,确实,我感觉他有些乖张,这点跟我爸很不一样。就算是重遇了十几年没见到的孙子,也并不像非常欣喜的样子。
“说,想问什么事。”他粗声粗气道。
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谈话氛围有点走偏了,我是否应该下次见面再问他比较好呢?但是我既然已经来了,没理由白跑一趟。或许我应该先问问,看看他是还记得当年搜索队的事。
“我最近在打听几十年前搜索队的事情。”我说。
他听完后眼睛为之一亮,干瘪的嘴唇紧闭。我知道这代表了什么,他确实知道些事。
“你们这些年轻人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历史了?”
“单纯兴趣而已。爷爷,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当年的那些故事?”我有点受不住他讥讽的腔调,但不便发难。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我现在有些事要忙,没太多时间闲聊。”他不屑道,然后从我手上不客气地接过了那些书,”等我搬回住宅区后你再来找我。如果我那时还没死,你还想听我老头子讲故事的话,就来找我。”
“那,爷爷你保重身体。”
“我身体很好。回去告诉你爸妈,老头子我还打算多活十年。”
这次重逢谈话并不顺利,我觉得总爷爷是个非一般的老头,他让我想起了中学时代一名老师,他博学多闻,比大部分老师有学问,所以平时心高志傲,有点难沟通。
我坐着班车回到了住宅区。一路无事,下了车已是八点,正往回家的方向走。此时路上行人稀少,路灯已亮了起来。家家户户正在用餐,肉香味飘到了街上,我顿时感到了饥肠辘辘,于是我加走了脚步,却听见跟在我后面的脚步声也加快了。
我试着又加快了脚,后面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我立即停下来,那脚步声也戛然而止。我继续前进,脚步声也紧随前进。似乎这脚步声在跟我保持着一致步调。
我越想越感到不妙,猛然扭头往背后看,街道上空无一人,脚步声再次悄然停止。我敢肯定有人躲在暗角注视着我,但却说不出是在什么位置。
我想起从疗养院回来的翌日早晨,那时我走到街上,也有类似的感觉。然而这几天来我都是一下班就回家了,可能是因为那个时段街上行人很多,所以我没才察觉有没有人在跟踪我。
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跟踪我?
我感觉心脏像悬在半空一样,绷得紧紧的。但是自从疗养院的经历之后,我学会了一点自控能力了,我发现只要不断对自己说必须冷静,必须冷静,真的可以令自己冷静下来。我思量着会是什么人跟踪我,马上,我就想到了疗养院拘留室里那个脸上有刀疤的银发男。他知道我跟大头当时在撒谎,他不止没拆穿我们,还放走了我们,直觉告诉我他是另有所图,没有人比那家伙更可疑。
但是他为什么要跟踪我呢?难道是因为我们去过了老鬼的房间?
银发男是不是担心我在那诡异的房间里发现了什么?
我忽然想到了另一个人选。那个在老鬼房间里袭击我们的人,也有相同理由跟踪我。
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是跟老鬼房间息息相关。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人会跟踪我了。考虑到这点,我开始确信老鬼房间里真的暗藏着什么重要的秘密。我可能从这周开始,一直都被人跟踪着。跟踪我的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却没有采取其他行动,那么应该是监视才对。不晓得大头是不是也被人跟踪监视了,他这几天反常的行径,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我心中暗暗自忖不能慌张,要先装作没有发现自己被监视。今后暂时保持低调,监视我的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寻常事,迟早会放弃的。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而,我的想法终究还是太天真了。当我继续往前走时,背后的步伐声突然急遽接近过来。看来这人不是监视我,明显是冲着我来的!我实时慌了,开始拔腿就跑。畏惧和恐慌给了我想像不到的动力,让我不顾一切地狂奔起来。
刚开始我确实看见有个人影跟在后面,可一转眼那人就隐入暗角中,就像一只躲在暗处的野兽。我感觉那人不怀好意,甚至是个危险的家伙,所以我不敢停下来,脑里只剩下必须甩掉后面那人的念头。
我沿着街道一会转弯一会直跑,可总感觉那人在后面紧追不放。我心叫不妙,于是转弯往海边方向跑去,跑进了石堤下的隧道,又从另一端跑了出来,沿着石堤旁直奔。最后,几乎绕了个大圈才返回住宅区。
现在是夏天晚上,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
我好久没有这么拼命奔跑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感觉血脉沸腾,汗流浃背,全身散发着蒸气。有个声音彷彿对我说安全了,另一个声音则不断告诫我别停下来。我下意识里往后方望去,因为有些累,我好像看见了一些物体在移动。安全起见,我咬着牙根,又跑了两条街,看到前面不远处就是家了。
此时我已感到小腿都快站不直了,大口大口地吸着灼热的氧气,胸口像被一团火包围着。我实在没力气跑了,于是停了下来,转身望向后方,没有发现可疑的动静。
我想我应该是成功摆脱了那个黑影。
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条件反射想要逃开,却被硬生生地拉进了黑暗处。我握紧了拳头,打算跟这个人拼了,可黑暗中我看不清楚他,只感觉对方很健壮。
“雷子。”他叫了我一声,听着声音非常耳熟。
“谁?”我摆出攻击的姿势。
“我。”他上前一步,借着微弱月光,我看到了他乱得像杂草一样的头发,还有脏兮兮的脸。
靠!居然是大头!
“大头?你想吓死我啊!”我减了一半力气,往这家伙胸口捶了一拳。
“嘘……小声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我立马意识到事态不对,但还是忍不住小声嘀咕:”你这几天死哪去了?去你家都找不到你。”
“唉,别说我了。”他有点焦虑,又有点沮丧。
“你这表情八成没好事。”
他又叹了口气,一副惶恐的样子:”雷子,我告诉你一件事。KELLY失踪了。”
“什么?失踪了?”我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他严肃地点点头,这表情告诉我,他没有跟我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