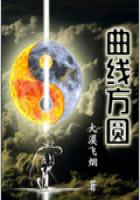“宁小岑,我会让你做到!”我的手拉开房门的瞬间听到凌舜晖的声音,幽冷而决然,仿佛浮冰下汹涌奔流的深海:“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别想再回到他身边!我一定会让你,完完全全属于我。”
我只觉得四肢百骸被撕扯着快要散架,胸口像坠了个千斤重的称砣,已经把心脏碾成了齑粉,只剩下一片让我喘不过气来的沉重与冷硬。
“只怕你现在做到了,以后会后悔一辈子!”
我没有回头地说,用两只手使劲拉开了厚重的大门,突然觉得一阵刺眼。
楼梯口一侧是扇硕大的窗户,仲夏早晨大把大把明晃晃的阳光斜射进来,无遮无拦肆无忌惮地正好射在我眼睛上,一瞬我眼前像闪电划过什么也看不见。
我本来就头晕眼花,这一下更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胀痛,索性半眯着眼睛快速跑下楼梯。
“宁小岑,”我听到骤然加快的脚步声和焦急到近乎惊恐的声音:“小心!”
我下意识收住脚步,还没站稳又听到一声失控的闷哼,愕然地急忙回头,就看见一个身影在楼梯上踩空,仿佛从那团阳光中跌落了下来,猝不及防中他好像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是不能着力的脚让他身子摇晃着又向前倾了过来。
我什么也没想就拼命冲了上去,伸开手阻挡在他的前方,在他触到我的一瞬紧紧抱住了他。
他好像在被我抱住的一刹那抓住了楼梯栏杆,另一只手想尽力地揽住我的背,虽然有了点缓冲,但是巨大的冲击力还是让我不可控制地直挺挺向后倒去,后脑壳正好弹落在一块硬物突起的棱角上。
那一瞬我还清醒,觉得后脑勺像是被一块烙铁狠狠地烫了一下,开始脑袋只是发麻发重,很快火烧火燎的疼越来越清晰而且不断地扩散,眼前是黑的,可又像有无数条小火苗在惊慌地乱窜,耳朵里仿佛还听到皮焦肉烂的吱吱声。
我痛得都哭不出来,心里还在埋怨自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顶在我脑后的碎片正是昨天花瓶碎片的余孽,估计程耀太过匆忙没来得及全部收拾干净,刚刚凌舜晖就是要提醒我别踩上去,可我却没头没脑只顾闭着眼睛横冲直撞……
想到凌舜晖,第一反映就是如果不是我这么不小心他根本不会摔下来,我一下子着急地不行,顾不得痛就往怀里乱抓:“凌舜晖,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我很好,不要动。”
可是他的声音听上去一点也不好,我在像广播嚣叫一样的耳鸣里都能听出他声音里的颤抖:“后脑有出血,目前意识还是清醒的……我没有搬动过她……对了,她怀孕了,……快,请你们务必快一点……”
我的神经全部被脑后锋利的疼痛牵扯着,一听到他说“怀孕”才感觉下腹也不对劲。一阵一阵的绞痛越来越紧,好像有一个尖尖的锥子在里面打着旋儿疯狂地钻凿,忽然一下尖锐的抽痛,哪一个地方好像被凿穿了,热的液体哗啦一下涌了出来,汩汩的像是奔流的小股喷泉,我的大腿都已漫开一片温温的湿热。
我在流血,大片大片的血。
我妈就是这样死去的,我在梦里无数次看见她泡在自己身体流出的血里,血慢慢地浸没了她的腿,她的身体,她的脸……
濒死的无力蔓延到全身,身下的血好像在慢慢蜿蜒成一条河,我在上面浮浮沉沉得魂灵都要游离出身体。
奇怪的是我似乎没有太大的恐惧,恍恍惚惚还觉得如果就这样魂归离恨天,倒也一了百了六根清净。
只是疼痛依然揪扯着我不放,倒让我实在替自己忿忿不平。老天真是不长眼,我这么年纪轻轻如花似玉就要死了,好歹也给我个痛快的,怎么还编排出这么大的苦楚来折磨我!
“痛……怎么这么痛……痛死了……为什么不让我痛快点死啊……”我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边心有不甘地很恨喃喃着,声音越来越轻连自己都快听不清楚。
“你不会死,宁小岑,我不会让你死!绝对不会!”说到最后几个字,凌舜晖几乎是在吼了。
我总是不听他的话,以前他也总是这么吼我,可是现在他的声音听上去比任何一次都生气,气得好像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
但我已经没有力气和他斗嘴了,我的脑子越来越糊涂,连疼痛的感觉似乎也在渐渐麻木。
恐惧突然攫住我的神经,只怕现在是我留在世界上最后一丝清醒的意识了!
“凌舜晖,你听我说,”我一下子觉得有很多要交代,身边只有他,我胡乱地挥着手要抓住他。
他的手立刻紧紧攥紧我的手掌,还是昨天那样冰凉黏腻的一手汗。
能想起来的全是些鸡零狗碎的事,我顾不得那么多语无伦次:“我有一张存折,在枕头下面的席子下面,密码是……”
开户的时候与教授情意正浓,密码是我们的生日合在一起,分手后也没有去改。
迟疑了一下我还是说了,反正我就快死了,什么旧爱情仇的都是浮云。
他的手好像颤了一下,我争分夺秒地径自往下说:
“那棵幸福树帮我还给周蕊蕊他们,祝他们一生幸福平安,不要像我这样……”
“我还欠叶琳娜两百块钱,上次交团费我正好忘带钱……”
“还有……”
“你会没事,不许再说!”凌舜晖突然俯身下来用唇封住我的嘴巴,只是轻轻地贴上来极温浅的啜吸,却反复流连黏住了一样久久不放,像是要一直黏到我死似的。
清冽深邃的气息让我瞬间清明许多,我终于想到最重要的事。
“还有……”反正最后一次了,我大胆的把手抚在了他的脸上,指尖在他脸上轻轻摩挲。
“宁小岑,怎么样?你到底怎么样……”他抬起头任我在他脸上任意妄为,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惊慌失措。
我留恋地把手指划到他嘴角的边上,那里,有时候如果运气好,会让我看到一个小而浅的漩涡。
初见时只道是寻常,只是一旦失足坠了进去才知道,原来那里是深不可测有去无回。
直到现在我才敢承认自己的沦陷,我对他挤出或许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微笑:“凌舜晖,我想和你说……我比我妈幸运多了,因为我死的时候,我爱的男人,在我的身边……”
感到解脱的同时一阵再也无法抵挡的疲倦,我却不愿放开掌心里他脸颊的那一抹微凉。
“凌舜晖,我想,我早就爱上你了。”
似乎有冰冷的液体滴落在我的脸上,然后,所有的一切好像都离我远去,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迷迷糊糊醒过来时我寻思着会不会碰上时下大热的穿越或者重生什么的,结果一睁开眼睛看到外婆欣喜若狂的老脸。
“哦哟哦哟,醒了醒了,你个死小囡,吓死外婆了!”
原来,还是在这一世,我却已感觉恍如隔世,而沉睡前对他最后说的一句话,还依然那样清晰地记得。
外婆急急地按铃通知医生,我费力地环视一下房间,还是上次那间医院豪华的单人病房,可是他却不在。
心里掩藏不住的失望弥散开来,我闭上眼睛皱皱眉头。
“不要再睡了,好囡囡啊!”外婆的惊喜转而又变作紧张:“你都睡了两天两夜了,再睡下去,你外婆的老命都要被你吓掉了!”
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蓦地睁大眼睛:“什么,我睡了那么久?”
明明应该是诧异的惊呼,从我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却是气若游丝。
“醒来就没事啦,醒来就好了。”外婆已经眼泪鼻涕一大把,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我赶紧通知凌先生,他一直守着你,刚刚才有急事回公司。”
“不要!”我没来由的一阵心慌。
一直以来我在他面前都裹着一个坚硬而光滑的蚌壳,可是现在壳被撬开,我柔软虚弱的内心完全赤|裸地坦陈在他面前,还嵌着他看不到却永远无法容忍的过往的尘砂。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怎么啦?”外婆奇怪地我摸摸的额头:“不发烧啊!你昏迷的时候可是抓着人家的手都不肯放,害得凌先生两天两夜都寸步不离的,现在怎么又不让我叫他来?”
我吞吞吐吐:“不要,不要打扰人家的公事,反正我也没事了。”
外婆这才宽心一笑:“嗯,傻小囡,学会心疼人了,不愧是外婆教出来的。”
医生来给我做检查时外婆问东问西几乎把人问得崩溃,我从他们的对话中大概知道了我受伤后的情况,我脑后的伤虽然流了点血,但只是小面积的挫伤并无大碍,真正伤元气的是流产造成的大出血,当时血库正好O型血告急,如果不是有位好心人及时捐献我可能真的就一命呜呼了。手术以后我身体虚弱一直昏迷,直到今天中午情况稳定,凌舜晖才通知了我外婆。
至于凌舜晖陪了我两天两夜,是外婆从几个小护士的闲聊里听出来的。
“这种事情是在是太吃苦头了,你个傻囡囡怎么就不知道当心点……你要再和你妈一样让我情何以堪啊!”外婆在我耳边特文艺的絮叨,“不过好在苍天有眼,让你碰到凌先生那样对你情深意笃的人,你掉了他的孩子他还这样不离不弃,我老太婆也可以安下心来了。这种男人啊是可遇而不可求,看看时机差不多就早点和他把婚期敲定吧,你的婚事定下来外婆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颐养天年了……”
我还是困倦,越听越觉得觉得遥不可及,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
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觉得肚子咕咕乱叫,我半梦半醒之间低低嘟哝:“外婆,我饿,我要吃东西。”
一根吸管塞进我嘴里,我吸了一口,淡而无味的温水,顿时不满又委屈:“我饿,我要吃鸡汤小馄饨……”
柔软的纸巾在我嘴边擦拭了一下,依稀一句无奈的叹息:“唉,宁小岑,你总是那么饿。”
天哪!淩舜晖!我可不可以装成暂时性痴呆或者永久性失忆?我全身见了鬼一样的震悚,眼睛闭得紧紧地把被子蒙在头上。
说话也结结巴巴瓮声瓮气:“淩总,您这样我我我实在担待不起,能不能叫我外婆过来啊……”
“宁小岑,不用再躲了,”他没有掀开我的防护,声音从被子外面传进来,闷闷沉沉仿佛隔着遥远的时空:“你可以当成从没有见过我,以前的宁小岑,我也会当成从来没有认识过,从现在开始,我要正式追求你,直到,你放下一切接受我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