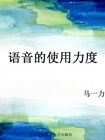陈起一只手提了提裤子,看着想要挣扎爬起来的神机客。
匪气十足,不见贼气,真真算个汉子。
“二当家,你喝光了贫道的酒,此间事了,可是要记得付酒钱。二当家就在此地,稍候贫道吧。”
言罢,铁棍一磕,强盗入户,一脚踹门。
哐当,木门塌了一般,生光术护体,全然不惧幽门之内氤氲而出得墨绿色烟雾,一个箭步而入。
那赤膊背影,活脱一个蛮不讲理的市井无赖,赶着去约架一般。
“先劈了你的棺材板”
门内满眼绿烟,满鼻浓雾,枯辣腐朽之气直窜脑门,满脚都是没入脚踝的粘稠泥浆,感觉已不是踩在人间之地。
心生不甘,不甘不得,生愁怨,与恨,所隔不足一步。
人生美好十钱,入得我门,可否借我一钱,让我也看看人间美好。
陈起不觉之中,满心凄凄,前尘种种,竟惹来凉泪,四眉丛生,原是那眉上再生愁眉。
五脏先天,肺主悲。
团聚在肺脉的那一道金光,许是觉得该是付点租金的时候了,散出丝丝迷离金光入脉,很快消解了这股不知何故涌来的悲愁,护住了肺脉。
烟雾之中,雾聚成影,影中有画,画中缭绕尽是不堪,虿盆、炮烙、木驴、凌迟……
道道酷刑,时时耳语,此间内无时无刻不告诉你,这是个什么光景的世道。
这前五关所涉邪祟,竟然皆有过往。
原本负责行刑的那个牢头,孰料生前却是因为贪墨,被判处凌迟三日,受三千六百鱼鳞刀,那个套在身上的渔网,远来就是用来行凌迟之刑,框定肉块大小的工具……
到那墙中老鬼,痴迷文卷诗词,为独占侄子的妙得诗篇,一包砒霜要了侄子全家性命……
贪?痴?
烟雾与雾影,向着深处被无限拉长,再缓缓收缩而回,再被拉长,往复不停。
哞……
陈起左腹纹身隐隐发烫,此刻彻底甩下了文雅吃客的遮羞布,这个灼意催促着陈起,吃食就在前方。
泥浆中趟行未久,前方雾影往复尤为强烈,依稀是两个巨大的孔洞,悠长地呼吸。
再临近一看,这些墨绿色的烟雾竟然是一只鬼物呼吸所散,两盏青光蒙蒙,在烟雾中亮起。
烟雾骤然左右晃动,四下散开,一个畜牲正在抖身甩水。
明亮耀眼的双眸,四只蹄子均深陷于泥浆之中,一只苍青色的大牛,身体反复扭动,蹄子却不出泥浆,位置一动不动。
哞……哞……
愁……愁……
这牛鬼显出身形之后,原来这先前听闻的类似哞叫的声音,竟是一个个愁字的声音。
一时间人畜无害。
牛眼中有暗红色的影子在流动,刹那间穿梭如电,红影左突又窜,陈起左腹的纹身已经发烫到有些难忍。
牛鬼开口。
愁啊……
登时泥浆翻腾,原本还算平整的的路,有如抖动一匹长布,波纹起伏,险些站立不稳。
水里有东西。
一只纤纤玉手,十指葱葱,从背后环过陈起脖颈,从脸颊掠过,向胸膛滑去。
“冤家,让奴家等地……”
“小冤家,你和贫道的纹身比来,你觉得哪个更吓人啊?”
“宵天朗朗,天光九重,灵心垂悯,护身诛邪,敕。”
光莲绽放,孔窍生光,花开涤荡,光焰升腾,笼罩方圆的烟雾被光力撕开,连脚下泥浆都有些消减。
至于刚刚那位尚未蒙面的不知名奴家,直接被万光穿身,原本封闭空间的层层烟雾,上方隐隐天光散入。
“贫道这24K纯金奥斯卡小金人的味道还不错吧。”
愁啊……
随着再一声喊叫,被生光术冲散的烟雾,内鼓烟团,下沉浊地,纷纷钻入泥浆。
泥浆成土,竟有绿草拔节,空间扭转,脚下的地面却悬立于陈起身后,宛若息壤汇合。
此刻再看,左右斧劈峭壁,两山之间内,却是那平整的土地,青草连片,陈起平躺着被土壤埋身,只有半个头露在外面。
这细草弯身摇曳,弥漫着那枯辣悲愁之气,土壤中透着透骨寒意,不仅禁锢着陈起,而且层层腐蚀着陈起的生光术。
陈起调动着八万四千孔窍中的光种,便要再绽光莲,突破这诡异的土壤。
陡然生变。
半空中的烟雾汇拢具现,一只滴着血珠的硕大牛蹄轰然踩下,生光护住全身,陈起双肩角力,青筋暴露,硬是硬从土壤阻塞中生生拔出一只手。
握拳护头,弯臂肘击,俨然八极顶心肘的招式,奔着牛蹄磕去,直接砸到了牛蹄之上的几道血痕。
许是有些吃痛,前牛蹄一个趔趄,竟然未做纠缠,一步迈过,呼吸之间,又是另一只牛蹄踏地而来,直奔面门。
陈起顶过连续三蹄,幸亏这三蹄之上皆有伤口,已经从土中拔出上半身,并拔出了原本插入土中两根黑铁混。
双棍交叉,第四蹄踏地而来,这一蹄的力道明显数倍于前,墨绿色烟雾缭绕,一蹄压住双棍,力道再加重一丝,便能将陈起重新踩回土中。
千钧一发之际,这牛蹄之上,一把钢刀破空寒来,在牛蹄之上霹雳三打,堪堪留下三道血痕,血珠迸发。
哪有时间感叹和好奇,陈起顺势抽棍在血痕之上补刀,牛蹄吃痛,竟也未做纠缠,一步踏过。
这一步踏过之后,寒光乍来,眦目而入,进而冷光闪闪一个镜面,从两山之中直来。
那是一把巨大的三角形犁铧,犁铧之上便是那与破开两山、齐顶平高的手扶木架,以及那不知几何多少,带着嘶吼被捻入那拉犁麻绳之内的扭曲鬼物。
以鬼搓绳。
鬼绳拉犁。
在前面踏步而过的牛鬼拉扯之下,明晃的犁铧从两山之间犁来,陈起身体所陷的土垄,便是犁铧锋芒所指。
民俗中便有惊蛰之后,春耕犁锄太岁之口口相传,封神演义中更有太岁神殷蛟所遭犁锄之厄的传奇。
电光火石之间,陈起收腹压惊气,舌顶上牙膛,两把铁棍插地,生光术催发至极致,扯开双腿与土壤那有如互生肉芽般地纠缠,双手反握铁棍,弓身而起。
犁铧锄到,虽然还未接触,但身体便已升起撕裂之感,仿佛这躯壳原本就是两半粘合而成,这会儿就是要把它重新犁开。
鬼绳向下一顿,犁铧入土又深一分,撕扯之力更为加重,陈起上自眉心,下至两胯之间,左右对称,上下一线。
一道血线,便要被犁锄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