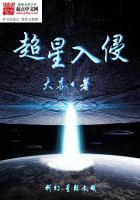“吧唧吧唧,吸溜。”
短匕挑起肉块,张嘴便是一阵汁水飞溅;端碗仰头一口肉汤入腹。
“美甚,啪嗒。”
满足叹息一声,放下碗匕抹把胡须,汉使抬头望向上首的右贤王,推开坐垫,缓缓站起,拱手躬身,称呼不知不觉改回了原本匈奴时:
“蹬,使命在身,不待与大王欢宴。还请大王予我一言,战死者尸身,是还,还是不还?”
按理说吃人嘴短,这汉使吃了右贤王的肉汤应该不好意思当面提出,起码要磨蹭半个小时辰,等这顿饭吃完。
但一来,这早食算不得高规格燕享,“寻常人家”所食罢了;二来,在任务完成的情况下,时间肯定是越短越好,也就容不得他拖延。
三嘛,便是要考虑到一会带着尸体回去的时候,会不会有随行匈奴兵卒在李司马问他,“为什么这么晚?”后当场跳出,指责他因私废公。
“啪,怎么可能!”
一名希冀献媚于王前的百长闻言大怒,拍桌而起,指着汉使,便是一阵唾沫星子飞溅:
“就算大王答应了你的要求,那被派去归还尸身的必然是最忠心不贰的。
“你说,他们为了戳穿你而降汉,哈哈,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听到过的最可笑的事情。”
“你,你怎么能听到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心中的阴私被人朗声道破,汉使身子一晃,差点原地摔倒。
“蠢物,你心里想什么,那张纠结到奶奶家的脸已经摆明了。”
再度喷了一脸唾沫后,百长犹不甘心,他直接大步走出几案来到帐中心的空地上,对着端坐上首看着下方热闹,胖脸渐渐严肃的右贤王下拜道:
“大王,我怀疑,这厮是在虚言恫吓我们,好打消大王您派人随行的念头,方便一一人行事。”
“哦,是这样啊,多亏龙套卿直言,本王知晓了。”
完全看不出的短脖子上下晃了晃,姑且算作颔首,严肃胖脸转向汉使,原本温柔的话语加了几分郑重:
“兰氏族人,你是如龙套卿所说的那样打算的吗?”
“蹬蹬。”
从几案后走出来到空地上,看了眼身旁下拜的龙套百长,他便下意识地要跟着他一起跪下。
“不好,跪拜大王事小,可我奉司马令来此,以汉使的身份跪拜,这事就大了。”
看着在视野中不断扩大的地面,心头突兀祸起,转瞬间想到了自己跪拜的后果。
“不然,大王还请听我啪,蹬蹬。”
脸色大变的他顾不得什么容貌威仪,单手猛地往地上一按,下拜之势被阻,整个人向后踉跄几步后站稳。
“呼,真是危险,差一点就要不得不跳反回匈奴了。”
擦了擦额头冒出的冷汗,捶了捶差点满负荷的老腰,汉使以微微躬身的姿态对着上首的右贤王说道:
“使命在身,恕不能对大王跪拜。”
“大胆。”
“无礼。”
紧随着汉使这一系列“杂技”响起的是一声声呵斥,是一张张拍桌而起的愤怒面庞。
不单是希冀拍马的百长,就连不太在乎,甚至幸灾乐祸于右贤王出丑的贵人、将校也不得不挺身而出,或是戟指怒斥,或是“良言”相劝:
“来人,将这厮拖下去斩了,再呈首送上。”
“此时速速下拜,看在兰氏的面子上,你还可以无事。”
“哗啦,蹬蹬。”
帘帐被掀开,一队持铤兵卒走入,直指空地上站立的汉使。
“嘭嘭,事急矣,要快拿主意,快让大王不杀我。”
用力捶了捶大腿,压住就地一滚,冲上前挟持人质、临死拉个垫背的冲动,汉使双拳紧攥,不去看周遭投来的恶意视线,拼力转动大脑:
“下拜能解决问题吗?能;那我现在能拜吗?能。”
先是第一个问题,能不能拜,拜了后能不能保住狗命;
“不过,现在下拜很容易,解除危机也很容易,但问题在后面,现在拜了,回去怎么向汉人交代?发怒的司马大人也同样可怖?
“就算有个万一,自己幸运地挨过了下拜的惩戒,经此落实背主之贼、膝盖很软的名号后,谁还会用我?”
“蹬蹬,呼哧呼哧。”
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隐隐能感受到重甲之下的粗重喘气声,乃至兵刃拖在地面上的摩擦声(脑补)
持铤兵卒:拖拽?在青铜铤面前,不管是珍惜动物皮毛的毛毯,还是铺满玉石、香木的地面都脆弱不堪。
我们究竟是来抓人,还是来搞破坏的?
没有功夫红着脸驳斥兵卒的“胡言乱语”,汉使继续疯转头脑:
“保命在下拜吗?不在;那在于什么?平息不下拜导致的大王怒火。”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不拜又要怎么才能抱住狗命;
“保命不在于下拜与否,而在于下拜惹得大王生气,只要让他不生气就行了,下拜是最简单,也是最迅速的办法。”
灵光一闪,汉使抓住了问题关键,并抬头看了眼面色温怒的右贤王。
“总之,不拜或许会死,但拜了后一定会生不如死。
“当然,不拜归不拜,也要注意言语举止,不能真惹急了大王,他急了眼可是不会问为什么,直接杀人的。”
成功总结好结论,抓人的持铤兵卒却也到了身旁,一声怒喝,挥舞着铤杆,便要搭在腿弯:
“贼子,还不快跪!”
“嘭。”
青铜铤毫无疑问地落空,铤尖在地上这张不知品种皮毛铺就的毯子上留下了一个大破口。
“*,他真的要杀我!”
心有余悸地看了眼距离脚后半尺的青铜铤,汉使心头大恐,却也无路可走,只得强逼着自己站在原地,用力震了下刚穿上不久,还有些别扭的衣袖。
“刷。”
借着青铜铤挥出后,众龙套闭嘴的环境,衣袖发出的响声虽小,但也压下寥寥几声嘈杂,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倒也是助我一臂之力,若非如此,我说不定还得大喝一声。”
思绪一刻不停,汉使不敢将其停止,他恐怕一停自己就再也无力,要顺从本能逃跑。
“大王,还请听我一言。”
一改往日的墙头草,随风倒的降胡面目,在数十人的恶意目光注视下,他板起脸,直起腰,朗声道:
“若平日遇大王,定三叩九拜以表敬意,可某为汉使,代表的是司马,是天子,如何能向胡王下拜?还请大王恕罪。”
说罢,汉使深深弯腰,对着脸色泛青的右贤王一个九十度躬身。
起身后,他看也不看周围咬牙切齿的龙套,和青铜铤即将落下的兵卒一眼,眼中只有右贤王,胖脸愠色稍缓。
“不好。”
看到这幕,那些悄悄关注右贤王,余光一刻不移的众龙套心中顿时一凉,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咬牙道:
“这厮究竟是耍的什么诡计,竟让大王动容?”
一群拍马的日夜努力,却不及一个降汉的三言两语,这确实够打击人的。
“不,还有办法。只要能赶在大王开口之前动手杀了这厮,那就行了。
“快,动手啊!”
一些嫉妒得发狂,抱着“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的龙套对着再度举起青铜铤,二度落下的兵卒狂使眼色。
“刷,啪嗒。”
青铜铤落了,只是落的位置不是他们希望的汉使后脑勺,而是持铤兵卒的手里。
“咚,大王?”
铤杆轻震地面,持铤兵卒受铤立在一旁,对上首的右贤王投以请示目光,一副指东打东,让撵鸡绝不撵狗的忠实走狗模样。
“咯吱咯吱,走狗!”
又是一声咬牙切齿的怒骂,众龙套对临时收手的兵卒恨得牙痒痒,却也只能在原地磨牙,怒目相视,做不得半分威胁言语。
“嘿,我几个既担风险又担责任,只为了给你们排斥掉一个拍马竞争?
“你看我,像傻子吗?”
持铤兵卒瞪眼冷笑以对。
“你……”
拍马龙套无言以对,只是暗暗磨牙,继续和持铤兵卒玩瞪大眼,谁闭谁输的游戏。
“哼,一群蠢物。”
唯有帐外,通过帘帐目睹全程的龙套二号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得极为透彻,没有被迷惑:
“这岂是甚么拍马,他从一开始便是降汉的贼子,是被汉狗派来试探态度,甚至送来给大王泄火的,这点你们难道都忘了吗?”
他在心中斥骂猪队友之余,也不免深感失望,坚定了先前浮现的小心思:
“有王如此,有将如此,有卒如此,这贤王军迟早要完,我得为了自己找些出路了。”
“我该走了,你们替我向统领大人交代一声。”
主意打定后,龙套二号不再看帐内的一人,也不再听帐内一语,他一边招呼了同样看戏的亲卫一声说要离去,一边心中细细思量:
“既要降汉,那等这汉使一会出来后,要向他卖好吗?”
只是这念头刚刚浮现,就被龙套二号摇头否决:
“不,降汉降汉,这降的是汉人,可不是给汉人当狗的胡人。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看好他,虽然有些身陷绝境的急智,但他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好运。”
龙套二号: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家伙能活过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