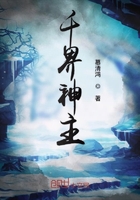柯嬷嬷点了点头,“长公主已经六年没见过皇上了。头几年请见时,皇上还使人来责骂殿下不会教养儿子……原本大爷起复,殿下特意进宫谢旨,皇上虽没象从前那样拒见,却也是说政事繁忙,只让殿下给皇后娘娘磕了个头作罢。”
郁心兰真是震惊了,原以为连城的起复了,皇上应当是不再猜忌他了,却没想到皇上竟连长公主都不见,说是政事繁忙,可磕头谢恩能要几个弹指?就算是在御书房,让外臣回避一下便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顿了顿柯嬷嬷又继续道:“殿下的生母玉才人份位不高,跳得一曲《何蛮子》被皇上宠幸的,可惜没熬出头便香消玉损了。殿下连个可以依仗的娘亲都没有,若不是皇后娘娘帮衬一下,殿下真是一点风光都无。”
柯嬷嬷话里的意思,玉才人竟是个舞姬?虽然贵族女子会在一些宴会上抚琴吹箫,展示才艺,但决不会跳舞!若是舞姬,那长公主还真是没有外祖家可以依仗。
郁心兰理了理思绪,方道:“我承认今日我是莽撞了些,可于礼法都合,父亲当不会怪罪母亲的。”
柯嬷嬷犹豫了一下方道:“侯爷的奶娘跟老婆子是拐着弯的亲戚。听她说,侯爷不是长子,又生得极俊,自幼家将的孩子们便很少与侯爷玩耍,只有甘夫人同侯爷玩,又不象旁的女娃子那么娇气,翻墙爬树什么都敢,侯爷自小便极喜欢甘夫人。殿下嫁来一整年,侯爷只在洞房那日到过公主府,后来殿下坚持搬到宜静居,才慢慢同侯爷恩爱起来。再后来生下了大爷,侯爷喜欢得不得了,有段日子,真可以说是蜜里调油。只是皇上登基后,皇后娘娘……多次责骂甘夫人,原是想帮殿下,却逼得侯爷更偏向甘夫人了。”说罢长叹。
郁心兰也跟着叹气,皇上以为施加压力,侯爷就会休了甘夫人,将长公主扶正,却不料侯爷是个硬脾气,不但不休,还变着法子顶着干,弄得婆婆现在左右为难。况且说难听一点,当初是皇上死乞白咧地要将皇妹嫁给侯爷,一登基就这般作态,实是有过河拆桥之嫌。
“一切的根源还在皇上!”郁心兰思索片刻,胸有成竹地道:“我想父亲只是不喜欢连家事都被皇上左右,才会越加偏颇甘夫人,若皇上不插手,父亲应当还是公正的。”记得新婚第二日进茶时,二爷嘲弄相公,侯爷便是帮着相公的,想来侯爷不是个糊涂人。
柯嬷嬷嘴角直抽,“皇上已经几年不插手侯府的家事了,可侯爷……”郁心兰浑不在意,“那不过是习惯。青梅竹马的情份,甘夫人在父亲心中的形象是根深蒂固的,便是有点什么事儿,甘夫人解释一下,或是道个歉陪个礼,侯爷便会信了。这厢先不管,目前最重要的,是让皇上与母亲恢复以往的兄妹情份。生母早亡,皇上和母亲幼时生活不易吧?”
柯嬷嬷有些难过的点头,“先皇有百来位妃子,五十余名皇子、皇女,皇上和殿下,又无生母照顾,个中艰辛,真是一言难尽。”
柯嬷嬷是长公主的奶娘,因而对皇上与长公主年幼时的事记忆犹新,又含着泪说了几桩心酸的往事。
郁心兰听后,顿时有了主意:“玉才人的忌辰就是秋分节?不如这般这般……”附耳低语。
柯嬷嬷有丝犹豫,“能行么?”郁心兰胸有成竹得笑,“必定行!只要皇上与母亲重归于好,还怕甘夫人翻花样?”见柯嬷嬷仍在犹豫,郁心兰又加重语气,坚定盟友意志:“只要母亲好好说,皇上必不会再插手侯府的家事,侯爷也必不会怪母亲。嬷嬷,您想想,就算今日我不逼甘夫人下跪,她就会善待大爷么?会敬重母亲么?只要她想为二爷、三爷谋这爵位,这就是不可能的!”
郁心兰说完,回身到床头的小暗格里拿张药单,递给柯嬷嬷,“这是我无意中发觉每日的例汤有些古怪,让大爷查出来的汤中加的药材。”
柯嬷嬷扫了一眼,脸色大变,急切地追问:“大奶奶,要不要请太医来为您诊诊脉?”
郁心兰虚拭了两下眼角,显得哀怨无奈,“暂时不必,例汤我早没喝了。”
柯嬷嬷立时站了起来,坚定地道:“大奶奶放心,老婆子我一定劝服长公主殿下。”
郁心兰露出感激的笑容,亲手包了两个三两重的小金鱼塞到柯嬷嬷手中,“有劳嬷嬷了。”她知道长公主派柯嬷嬷来,是要劝她低调柔顺点,却没想到会被她反劝回去。不过只要是母亲,看到那张药单,都会想去争一争,为儿子支起一片天地。
柯嬷嬷贴身收好药单,正想告退,外间便传来吵闹声。细耳一听,是程夫人那大嗓门在大叫着,“把你们奶奶请出来,我倒要问问,我们老爷每月都将俸禄上交到了公中,凭什么饭也不让我们吃顿好的!”
郁心兰撇了撇嘴,向柯嬷嬷道:“一会还请柯嬷嬷陪我演折戏。”然后扬声道:“是大伯母吗?快请进!”
程夫人冲锦儿冷笑一下,“没规矩的东西,本夫人的路都敢拦,给我掌嘴!”程夫人的几个大丫头就要上前,紫菱冷喝一声“住手!”而后向程夫人福了福,“还请大夫人见谅,锦儿若有不是之处,我们奶奶必定会责罚!”
程夫人是西府的主母,伸手管东府侄媳妇的丫头本就不对,只是她认为郁心兰不敢反抗,所以说得理直气壮,没曾想到被个丫头给驳了。
程夫人觉得没脸,还想发作,可天色又不早了,还是大事要紧,于是丢下一两句重话挽回颜面,冲进了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