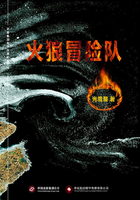我出生在濑户内海上的一个小岛,对我来说,令人怀念的故 乡风景既不是大海,也不是橘子园。
而是窗外的一片烟草田。
我在东京生活已经十五年,当我这么说时,没有一个人脑海中能够浮现和我脑中相同的画面。即使我告诉大家,烟草在变成 茶色的碎片之前,是柔软的黄绿色大叶子,茎的前端会绽放出楚 楚动人的粉红色小花,也没人能想象。有人问,那是怎样的花? 我回答说,和茄子的花很像,对方居然莫名其妙地反问,茄子是 蔬菜,也会开花吗?
对大部分人来说,烟草就是包在香烟纸里的茶色叶子,茄子 就是细长形的紫色蔬菜。虽然有人闻到烟味就皱眉头,但我很喜 欢烟味,只不过我说的烟味不是会冒出黄烟的香烟味道,而是刚采下的黄绿色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茶色时散发出的香 味。
我家那栋屋龄超过五十年的两层木造房子后方,有一片差不 多八十坪大的农田,除了茄子以外,一年四季都种植时令蔬菜, 周围还种了会开花、结果的树木。住在老家的时候,每到傍晚, 我就会拎着篮子,好像去菜市场一样,去农田里采收。
农田的后方是一大片烟草田。烟草田周围是五公里没有铺柏 油的产业道路,周围的居民经常在那里散步。
如今,已经看不到烟草田了。 可能是因为香烟不仅会影响吸烟者的健康,还会影响周围的人,因此,香烟逐渐遭到社会的排斥。从十年前开始,烟草田渐 渐改种其他蔬菜,从五年前开始,有一部分经过整地后作为建筑 用地。
这次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回老家。 我并没有和家人闹不愉快。如果我有儿女的话,父母应该会叫我每年都回家,但对于三十多岁的单身女儿,只要偶尔打打电 话,确认我还活着就够了。而且,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处 境也和我相同的妹妹。
二楼两间三坪大的儿童房原本用纸拉门隔开,如今纸拉门被 拆掉,成为成年以后终于享受到独生女待遇的妹妹的城堡。我搞 不懂她为什么花钱搜集一大堆只要去仓库翻找,要多少有多少的 昭和初期的旧家具和旧摆设。房间变了样,连窗外的风景也都变 了样。
窗外是一栋三年前建造的老人福利院,橘色的屋顶和白色的围墙很像是欧式公寓,乍看之下,不像是老人福利院,但看到已 经晚上九点多了,各个房间几乎都没有亮灯,就会觉得果然是老 人福利院。
白色围墙绕在房子周围,围墙内种了开红花的树木。是大花 四照花吗?通常都是开白色的花,红色的栽培不易,可见得到了 悉心的照顾。在建造这所老人福利院的同时,也修整了周围的产 业道路,如今,可以绕着铺了欧式石板的五公里产业道路一周, 欣赏四季的花草树木。
这所老人福利院由政府出资建造,不了解内情的人看了或许 会皱眉头,觉得浪费了国民的纳税钱,但是,这所老人福利院的 戒备森严不光是为了入住者,更是为了周围的居民着想。如果觉 得羡慕,可以在调查清楚这到底是怎样的老人福利院之后,请政 府也去自己住的地方建造相同的设施。
即使是无法想象烟草田的人,当他们听到我说窗外就可以看 到老人福利院时,能够想象出那个画面吗?虽然我家的人已经习 以为常,但对大部分人说,仍然是一件很奇特的事。
我再度仰头从一楼到六楼细细打量。
纸拉门打开了,妹妹单手拿着托盘走了进来。 “你介意灿烂院吗?” 妹妹问站在窗边的我。这家老人福利院叫“灿烂院”。 “虽然房子很漂亮,但治安没问题吗?”
“完全没有问题。基本上,住在里面的人不会外出,所以 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我们担心的事,事情没想象的那么糟啦。”
妹妹把那个圆形漆器托盘放在那张电视连续剧中顽固老爹翻 桌镜头中常出现的圆形矮桌上,用茶壶泡茶。我拉起窗帘,背对 窗户坐在矮桌前。
三年前回家的那次,家里召开了一个小型家庭会议。与会者 是父母、我和妹妹,会议主题为是否同意老人福利院建造在我家 后方。虽然不是建在我家的土地上,但福利院特地派人来征求我 家的同意,原本以为他们很有良心,但听了详细的说明,又看了 资料,终于了解了其中的理由。如果他们事先不打一声招呼就擅 自建造那家老人福利院,恐怕真的会被告上法院。
听负责和我家交涉的联络人说,之前他们找了多块预定地, 但和预定地相邻的住户团结一致,大力反对,至今为止的交涉全 都遭到了拒绝。幸好目前这块预定地只和我家相邻,只要我家同 意,他们就可以在这里兴建了。
父母担心的是阳光的问题。老人福利院是岛上独一无二的六 层楼钢筋建筑,一旦会对屋后的农作物产生不良影响,就无法同 意他们兴建。我和妹妹都很受不了父母,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 担心吧?我家平时大门和檐廊的门都敞开着,如果神志不清的老 人擅自闯进我们家怎么办?等到遭受危害之后,再后悔早知道就 不该同意就来不及了。即使那些老人不会外出,搞不好三更半夜 会发出怪叫声,或是有些老人会动粗,所以,该担心的不是农作 物,而是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想到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
─这种事要发生了之后才知道,杞人忧天也没用。
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
─如果家里有可爱的孙子,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这就叫作躺着也中枪。我每年最多只回来一次,说起来有 点事不关己,所以很快就闭了嘴,但住在家里的妹妹不肯轻易让 步。
─你们都上了年纪,即使发生什么也无所谓,你们也该为 我想想,未出嫁的女儿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
─既然这样,那你就赶快找个人嫁了吧。
─不用担心,反正老人福利院也不是三两天就能造好的, 就当作是比赛吧。
我妈并不是在讽刺妹妹,而是真心希望我们两姐妹中,至少 有一个赶快结婚。我发现原本打算与之结婚的前男友超级恋母, 才刚分手不久,根本不考虑结婚的事,所以立刻和父母站在同一 战线,同意建造老人福利院。于是,三比一,少数只能服从多 数。
联系人拿着根据日照率计算出来的资料,向父母说明并不会 对屋后的农作物造成任何影响后,立刻在同意书上盖了章。虽然 不是造自家的房子,联系人却跪坐在我们面前深深鞠躬,几乎把 头磕到膝盖了。
─你们是全日本心胸最开阔的一家人。
“茶泡好了。” 古董集市买的有田烧茶壶内飘出绿茶的清香,高雅的香味让
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用力呼吸。难道是乡下的空气衬托了茶的香 味?和我带回来的“松月堂”最中饼应该绝配,但必须把最中饼放在佛坛前供一晚上,而且,这毕竟是知名的和果子店一天只卖 三十盒的限量商品,我不想比父母先吃。
我家向来和奢侈的东西无缘。我妈经常说,大家一起吃便宜 货,比一个人吃高级货幸福多了,从来没有想到其实可以大家一 起吃高级货。所以,要等一家四口到齐后,才能吃最中饼。
“你在减肥吗?”妹妹问。 “如果在减肥,怎么可能回来?” 我的体质偏瘦,再加上每次回来,眼睛下方就挂了两个黑眼袋,让我妈看得心生怜悯。我每次回家,她在吃饭时就不停往我 的碗里夹菜。今天晚上,我也十二万分享受了一家四口久违三年 的鸡肉丸火锅。
父母胼手胝足地供我读完大学,我身为长女,没有回老家 尽儿女之责,在都市自由自在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至少 在回家探亲时要好好孝敬父母,但可惜我也手头拮据,尤其这一 次,买一盒五千元的最中饼已经是我的能力极限了。看到我三年 前买给父母的防风夹克袖子已经磨破了,他们仍然穿在身上,内 心忍不住隐隐作痛。而且,我妈胸前还别了一个好像小孩子公主 玩具组合中的大胸针。
那到底是什么?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但因为别在防风夹克上 面实在太不搭了,我无法开口发问。
“这个给你吃。” 妹妹从银色的仙贝盒子空罐里拿出一个熟悉的小盒子。那是“松月堂”金盒包装的和三盆糖。
“喂!家里怎么会有这个?”
“别人送的。姐姐,我记得你很爱吃和三盆糖?这种糖虽然 好吃,但没办法一口气吃很多,所以怎么吃都吃不完。妈还说, 干脆泡咖啡的时候当砂糖用。”
“开什么玩笑?这是梦幻糖果耶。只有京都总店的老主顾才 能买到,而且一盒就要三万元。”
“三万?所以像砂糖这么小的一块就要一千元?不可能!你 是不是把三千元记成三万元了?”
妹妹说完,打开盒子,把一颗做成菊花图案的和三盆糖丢 进嘴里,我差点“啊”的一声叫起来。不光是盒子,我也见过那 个菊花形状。我们公司出版的杂志上曾经介绍过,国民天后演员 在庆祝古稀之年时,曾经送和三盆糖给自己的亲友。在报道中还 附加了一句,该店不接受任何电话、电子邮件的预订。没想到这 种梦幻糖果竟然就这样随意丢在我家的矮桌上。我诚惶诚恐地伸 出手,拿起一颗菊花,轻轻放在舌尖。柔和的甜味立刻在嘴里扩 散,随即消失了。
“味道怎么样?”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但说不清楚,只吃到砂糖的味 道。”
“对吧?是不是吃不出有什么特别?喂喂爷还真舍得砸钱 啊,不,我猜想是有人送给喂喂爷,他不知道是这么贵的糖果, 所以才送给我们家。如果妈知道这么一小颗就可以在‘雪绒花’ 买四块草莓蛋糕,一定会昏倒。”
“雪绒花”是搭乘前往对岸本岛的渡船站附近的蛋糕店,现 在觉得一块草莓蛋糕两百五十圆的价格很合理,但小时候觉得是高级蛋糕,一年只有四次,家里有人生日的时候才会去买。岛上 的超市卖的草莓蛋糕一盒有两块,也只要两百元。
“喂喂爷?” 我问了令我纳闷的问题。 “就是住在灿烂院顶楼的爷爷。”
“你还叫得真亲热,他是叫隈川之类的吗?”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种事不是不方便问吗?他每天都打开窗户叫喂、喂,所以我就提议叫他喂爷爷,结果妈妈说喂 喂爷更有亲切感,所以大家都这么叫了。”
“没问题吗?” “反正是隔着六楼的窗户,话说回来,第一次向他挥手的妈
妈真的很有勇气。” 然后,妹妹说了我妈和“喂喂爷”之间交流的来龙去脉。
老人福利院通常根据机构的特征,分为特别养护老人院、老 人照护保健院、安养院,会在广告牌上连同机构的名字一起写清 楚,但“灿烂院”的广告牌上并没有写。不知道是因为属于实验 性质的老人福利院,无法按照一般的方式分类,还是故意不写。
两年前的五月落成的“灿烂院”在房子建好之前,就已经选 好了入住者。房子刚造好,入住者就搭渡轮来到岛上,当天就住 满了每个房间。虽然不知道那些入住者从哪里来,但应该没有岛 上的居民。“灿烂院”的门前有可以停二十辆小客车的停车场, 平时只有送货的人把车子停在那里,从来不曾有过访客。
院方禁止入住者自由外出,虽然可以在院内散步,但因为围墙很高,所以外面的人不会和入住者打照面。因此,对我家来 说,除了后方建了一栋大房子以外,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父母 和妹妹三个人的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我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准备早餐、洗衣服。我爸退休之 前,每天六点叫他起床,七点送他出门上班后,在农田里工作一 个小时,然后带着便当去山上的橘子园。傍晚五点之前,独自在 橘子园工作。回家之后,在屋后的农田里采收蔬菜,准备晚餐。 我爸七点回来后,一家三口围在桌前吃饭,他们夫妻十点上床睡 觉。每天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娱乐。我妈的兴趣是下厨和编织, 简直就是家事的延伸。
六月,“灿烂院”开张后一个月,梅雨季中难得太阳露脸的 早晨,我妈像往常一样,在屋后的农田浇水,头顶上传来男人的 叫声:“喂——喂——”我妈没想到是在叫她,继续忙着农活, 但那个声音一直叫不停。“喂,喂,小姐。”我妈心想该不会是 叫她吧,于是停下了手。声音是从“灿烂院”的方向传来的。回 头一看,一个老人在顶楼房间的窗户前向她挥手。
“喂,喂,小姐。你真的很勤快,每天真辛苦啊。” “一点都不辛苦,我精心栽培的花和蔬菜为我带来活力,你那里可以看到花吗?” “我视力很好,看得很清楚,你的脸也看得很清楚。如果你不介意,小姐,可以为我摘下你脚边的白花吗?” “哎哟,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从这里看就够了,我这老头子不会妨碍到你吧?”
“请便,请便,请你欣赏我种的农作物。” 他们聊了一会儿。那之后,只要天气放晴,我妈去屋后的农田时,喂喂爷就会打开六楼的窗户,大叫着:“喂——喂——” 挥着手向我妈打招呼,心情愉快地鼓励我妈,一直看着我妈在农 田里干活。
我把和三盆糖放进嘴里。我必须在脑袋里整理一下这件事。 “听到别人叫小姐,居然会觉得在叫自己,你不觉得很有妈妈的风格吗?” 妹妹为自己的茶杯里倒茶时说。
“小姐哦……即使身穿旧衣服,但还是有一颗少女心啊。 不,她是天使,我从来没有看过像妈妈这么心胸开阔的人。虽然 是自己的妈妈,我真的觉得她很了不起。”
无论问岛上任何人,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妈是“好 人”,也许有人口不择言地说她是“伪善者”,通常都是和我妈 年纪相仿的同性才会说这种话。但是,那种人觉得我妈是“伪善 者”,是因为她再怎么努力想要当“伪善者”,也无法待人亲 切,但即使面对这种口出恶言的人,我妈仍然能够一视同仁,用 和别人相同的方式对待她。
我妈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不属于任何公益团体,只是因 为自己想做而做,就这么简单。
无论对方得了传染病,或是负债累累,或是曾经多次离婚, 或是别人说他脑筋有问题,对我妈来说,大家都是“邻居”。只 要听说有人生病了,就会制作容易消化的菜肴上门探视;只要谁家有喜事,就会带上她擅长的寿司和屋后种的鲜花上门道贺。 我妈令我望尘莫及。虽然我身上有一半是她的血─不,我爸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的这些行为,休假的时候,甚至和我妈同 行。我是他们两个人的女儿,却完全无意向他们学习,也不想继 承他们的意志。
相反,我甚至希望他们节制一点。
即使有人在相同的情况下和我打招呼,即使叫我“漂亮的 小姐”,我应该也会当作没听见。我相信眼前的妹妹应该和我一 样。
“你在说从早到晚工作的父母时,难道没有一点罪恶感 吗?”
“我也有做事啊。” 妹妹鼓起了脸。三十多岁的人还会做这种表情,可能来自我妈的遗传。真是该继承的优点不继承,只继承无关紧要的部分。 “你只是从早上十点到傍晚四点,坐在完全没有客人造访的乡土资料馆柜台而已,而且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计时职员。 既然工作那么轻松,难道你没想过自己煮晚餐吗?我猜你的薪水 一分钱都没交给家里吧?”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虽说你是东京出版社的正式员工,但 那家小出版社连名字都没听过,你也没有寄钱回来给爸妈啊。你 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我至少比你孝顺爸妈。妈妈说想看刊登你写 的无聊文章的《波动》,我还帮她上网订了呢……对了,我记得 好像有刊登通知说下个月开始停刊了?”
“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