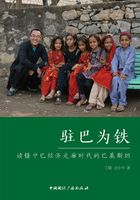闻一多(1899—1946)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现代诗人、学者,新月派的成员。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等,字益善,号友三、友山。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22年留学美国,学习美术和文学。1925年归国后,曾任国立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1928年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愤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最终于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被国民党枪杀。
《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生前拟定的唐诗研究的写作计划,因其突然离世而未能完成。1949年朱自清等人编辑《闻一多全集》时,首次以《唐诗杂论》为题收入了有关唐诗的九篇文字,我们根据当今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选择了其中六篇。朱自清曾评论说:“他的《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可见其作品的价值与特点。
《律诗底研究》写于1922年3月,历来被人们被称为《诗歌节奏的研究》一文姊妹篇,是作者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古代诗歌可以作为新诗创作的借鉴而写作的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全文七章二十一节,现存手稿五十九页,内容主要于分析和总结中国古代律诗的特点和规律,如律诗的定义、溯源、组织、音节、作用、辨质、排律等。文中虽然没有涉及新诗,但作者的动机却是为了阐明古代律诗中存在着包括形式在内的大量养料,等待着新诗人们去汲取。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本书是作者表述新诗观的著作,却因系统介绍了古代律诗的知识而成为认识和学习古代律诗的一部精彩作品。
唐诗杂论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麓”,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麓,类书家也是书麓,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麓”,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徐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甚至
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隋遗录》所载炀帝诸诗皆明秀可诵,然系唐人伪托。《铁围山丛谈》引佚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亦伪。
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枫落吴江冷”比起前面那两只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这不是说笑话。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么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品质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归真地讲,崔信明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比,不简直是“事”与“意”的比照吗?我们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占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做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徵,来维持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领下的人们为诗干得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学术。关于修辞立诚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若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
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则深而雅,其义则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因为他崇拜的陆机,是“文藻宏丽”,与夫“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的陆机,所以太宗于他的群臣中就最钦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学士赞》中,是这样赞虞世南的:
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家,并包六艺。
两《唐书·虞世南传》都说,他与兄世基同入长安,时人比作晋之二陆,新传又品评这两弟兄说:
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赡博不及也。
这样的虞世南,难怪太宗要认为是“与我犹一体”,并且在世南死后,还有“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之叹,这虞世南,我们要记住,便是《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著者。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不啻明白的告诉我们,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五十二期
宫体诗的自赎
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的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其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没有第一流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但这时期却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就因为他们制造了些有如下面这样的宫体诗。